慢性阻塞性肺病合并細菌感染患者CD4+CD25+T調節細胞及相關細胞因子表達水平及意義
邢貞泉, 趙光強
(海南省三亞市人民醫院/四川大學華西三亞醫院呼吸內科, 海南 三亞 572000)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可防、可治的慢性氣道炎癥疾病,不完全可逆的氣流受限為其主要特征,COPD急性加重是導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有數據顯示,COPD患者每年約出現0.5~3.5次急性加重[1]。細菌感染是誘導COPD急性加重的重要因素,文獻報道40%~60%急性加重期COPD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培養結果可發現病原菌感染,因此及時并準確判斷有無細菌感染對COPD患者臨床治療和改善預后具有重要參考價值[2]。既往研究表明感染引起的機體免疫改變是導致COPD病情變化的重要原因,其中以T淋巴細胞介導的細胞免疫為主[3]。CD4+CD25+調節性T細胞(regulatory T cell,Treg)是具有特異表型和功能的T細胞亞群,可通過分泌抑制性細胞因子誘導和維持免疫耐受,在自身免疫病、腫瘤免疫、感染等疾病防治中具有重要意義。觀察CD4+CD25+Treg細胞及相關細胞因子表達可能對COPD臨床診治具有指導意義[4]。本文主要探討CD4+CD25+Treg細胞及相關細胞因子在COPD患者外周血中的表達水平,同時分析其與COPD合并感染的關系以及在預后評估中的應用價值,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納入2020年8月至2022年8月108例COPD患者為研究對象,根據是否合并細菌感染分為感染組(n=53)和對照組(n=55)。納入標準:①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診治指南(2021年修訂版)》[1]中COPD相關診斷者,即存在COPD危險因素暴露史,有慢性咳嗽、咳痰、呼吸困難等癥狀,吸入支氣管舒張劑后肺功能檢查提示第一秒用力呼氣容積/用力肺活量<0.7,并排除其他引起持續氣流受限及類似癥狀的疾病;②感染組均經臨床表現(發熱、痰量增加、膿性痰、呼吸困難加重等)、實驗室指標(C反應蛋白、白細胞、降鈣素原等升高)、細菌學培養(痰培養病原菌陽性)等明確診斷;③年齡40~85歲;④入組前1月內無抗生素、激素類藥物、免疫調節劑應用;⑤患者以及家屬均知情同意。排除標準:①合并其他系統急慢性感染者;②伴哮喘、肺結核、間質性肺病等其他呼吸系統疾病者;③合并惡性腫瘤、自身免疫病等其他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疾病;④精神病史。
1.2研究方法及指標:所有對象入組后次日清晨,采集空腹肘靜脈血標本,一份樣本制備單細胞懸液,采用CytoFLEX型流式細胞儀(美國貝克曼庫爾特公司)檢測CD4+、CD4+CD25+水平;另一份樣本分離上清液備用,采用ELISA法測定白介素-4(interleukin-4,IL-4)、白介素-12(interleukin-12,IL-12)和干擾素-γ(interferon γ,IFN-γ)水平,試劑均購自上海晶抗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比較兩組研究對象外周血CD4+CD25+Treg細胞及其相關細胞因子IL-4、IL-12和IFN-γ表達水平,分析各指標與COPD是否合并細菌感染及預后關系。所有患者均按照指南[1]進行規范治療,包括危險因素管理(戒煙、避免暴露于潛在刺激物中)、氧療、應用支氣管擴張劑(結合患者實際情況合理使用β2受體激動劑、抗膽堿能藥物、茶堿類藥物)、糖皮質激素(伴外周血嗜酸性粒細胞計數升高者)、改善痰液黏稠度(痰液粘稠者)、抗感染(合并細菌感染者)等治療;并隨訪預后(住院患者追蹤轉科情況,出院患者28d內每日電話隨訪1次,了解疾病情況),統計患者28d內病死率。

2 結 果
2.1感染組與對照組COPD患者基本資料比較:感染組年齡和長期激素用藥史比例明顯高于對照組(P<0.05),兩組性別、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煙酒史、長期臥床、病程及合并癥等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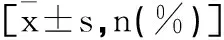
表1 感染組與對照組基本資料比較
2.2感染組與對照組COPD患者Treg細胞及相關因子比較:感染組COPD患者血清IL-4和IL-12水平高于對照組,IFN-γ/IL-4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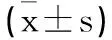
表2 感染組與對照組COPD患者Treg細胞及相關因子比較
2.3不同預后COPD患者Treg細胞及相關因子比較:隨訪結果顯示28d內死亡15例,病死率13.89%。死亡組COPD患者血清IL-4水平高于對照組,CD4+CD25+、IL-12、IFN-γ和IFN-γ/IL-4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2.4COPD合并細菌感染的logistic回歸分析:將性別和年齡作為校正因素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血清IL-4和IL-12水平均與COPD合并細菌感染存在關聯(P<0.05),見表4。

表4 COPD合并細菌感染者的logistics回歸分析
2.5COPD患者預后的logistics回歸分析:將性別、年齡和細菌感染作為校正因素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CD4+CD25+、IL-12和IFN-γ/IL-4均與COPD患者預后存在關聯(P<0.05),見表5。

表5 COPD患者預后的logistics回歸分析
2.6Treg細胞及相關因子對COPD患者預后的診斷價值分析:以患者預后未狀態變量(死亡=1,存活=0),以logistics回歸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指標為預測指標,ROC曲線顯示CD4+CD25+、IL-12以及IFN-γ/IL-4對COPD患者預后判斷具有良好參考價值;三項指標構建logistic回歸模型,以其預測概率繪制的ROC曲線顯示,三項指標聯合預測患者預后的AUC較單項指標進一步提升,見表6,圖1。

圖1 CD4+CD25+、IL-12以及IFN-γ/IL-4評估COPD患者預后的ROC曲線

表6 Treg細胞及相關因子對COPD患者預后的診斷價值分析
3 討 論
免疫平衡紊亂是導致COPD病情持續進展的重要病理基礎,其中感染是加重免疫失衡的最常見原因,感染通過激活免疫應答并誘導炎癥反應加重,促進炎癥細胞向肺血管床和氣道壁遷移和聚集,不僅可引起微循環障礙,導致氣道壁反應性增加和肺功能減退,同時還可加重氧化應激反應并造成肺組織損傷[5]。故探究COPD及COPD合并感染者免疫狀態變化對患者病情分析及診療方案制定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CD4+CD25+Treg細胞是起源于胸腺的免疫調節性T細胞,可抑制CD4+、CD8+T細胞活化、增殖,參與機體免疫應答的負調控,其作用機制可通過細胞與細胞間直接接觸,或分泌抑制性細胞因子來完成,這對維持機體免疫穩態十分重要[6]。細胞因子在免疫調節和炎癥反應發揮重要作用,其中IFN-γ主要由Th1細胞產生,IL-4則以Th2細胞分泌為主[7]。文獻指出,COPD合并肺部感染者可出現Th1/Th2平衡紊亂,主要表現出Th1相關細胞因子明顯下調,而Th2相關細胞因子明顯升高,這對抑制體內炎癥反應有積極作用[8]。本文結果顯示,感染組IL-4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IFN-γ/IL-4明顯低于對照組,表明感染可引起免疫應答并促進抗炎因子IL-4表達,同時因免疫調節功能下降,IFN-γ升高幅度不明顯,導致IFN-γ/IL-4降低,這與感染組COPD患者CD4+CD25+Treg細胞降低的趨勢保持一致,提示患者存在免疫失衡傾向。IL-12主要由固有免疫系統中樹突狀細胞釋放,為促進Th0細胞向Th1細胞分化的重要因子,在機體免疫功能調節中發揮重要作用[9]。本研究結果顯示感染組COPD患者血清IL-12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表明病原菌可通過激活樹突狀細胞而誘導IL-12表達,進而促進Th1細胞活化并分泌IFN-γ等細胞因子,參與調節細胞免疫。本研究logistics回歸分析也進一步證實血清IL-4和IL-12水平與COPD合并細菌感染存在關聯,提示二者檢測可能有助于早期預測COPD合并細菌感染發生,這與侯聰霞等[10]報道有相似之處。
COPD合并細菌感染無疑會加重患者病情、增加其治療難度,對患者預后造成不利影響。本研究結果顯示,本次納入的COPD患者經積極治療后28d內病死率為13.89%,這主要因為細菌感染直接導致患者病情加重,繼而引發呼吸衰竭、多器官功能障礙等嚴重并發癥,使得患者預后不良。比較發現,死亡組血清IL-4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CD4+CD25+、IL-12、IFN-γ以及IFN-γ/IL-4均明顯低于對照組,可見COPD患者死亡與免疫調節功能減退和炎癥反應加重有關,與宋署光等[11]報道結果相近。logistics回歸分析顯示CD4+CD25+、IL-12和IFN-γ/IL-4均與COPD患者預后存在關聯,隨著病程進展,COPD患者血清IL-4等抑制性細胞因子水平明顯升高,同時抑制Th1細胞活化和IFN-γ釋放,導致Th1/Th2漂移,患者炎癥反應和肺組織損傷持續加重,最終導致患者病死率增加,可見調節免疫功能,促進T淋巴細胞亞群分布恢復平衡對COPD治療具有重要意義,且檢測CD4+CD25+、IL-12和IFN-γ/IL-4可為評估預后提供參考信息。本研究作ROC曲線進行分析顯示CD4+CD25+、IL-12和IFN-γ/IL-4用于評估COPD患者預后的AUC分別為0.747、0.827和0.709,均具有良好敏感度,但單獨檢測時特異度相對偏低,將三者聯合進行評估顯示AUC達0.924,敏感度為93.33%,表現出良好診斷效能。
綜上所述,CD4+CD25+Treg及相關細胞因子與COPD感染發生和預后有關,檢測CD4+CD25+Treg分布以及IL-4、IL-12和IFN-γ可為COPD患者細菌感染診斷和預后評估提供參考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