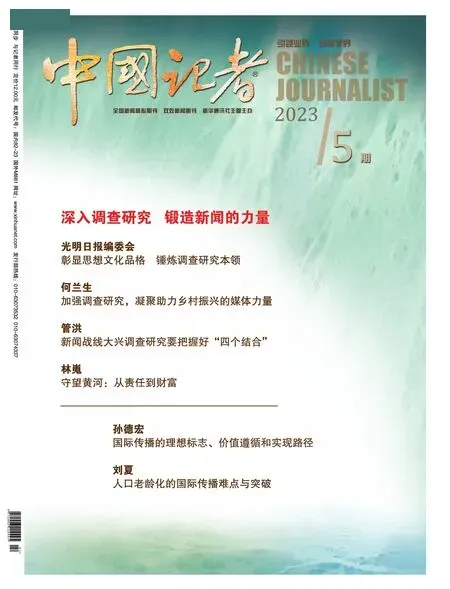國際傳播的理想標志、價值遵循和實現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對推進我國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十分重視,多次強調要搞好國際傳播:“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認識一個立體多彩的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當下,在思想認識上重視國際傳播已成普遍共識,但在具體實踐中如何做好國際傳播工作還是一個十分迫切的現實難題——“傳而不通”“各說各話”“自話自說”“自娛自樂”,乃至“自產自銷”“自生自滅”之類的情況,還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些傳播效果不佳的難題該如何解決?
國際傳播的傳播效果如何,關鍵取決于“價值認同”。價值認同問題是國際傳播中最重要的問題。成功的國際傳播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傳播者與接受者擁有接近乃至相同的價值取向。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明確提出了“全人類共同價值”的重大理念,為我們搞好國際傳播,提供了堅定而明確的價值觀和方法論依據。
因此,在實踐中如何切實地做好我國的國際傳播工作,我們必須深入思考這樣幾個問題:成功的國際傳播的理想標志是什么?它的價值遵循是什么?它的實現路徑是什么?
一、理想標志:在文明互鑒中融合成為異域文化的一部分
什么樣的國際傳播才是成功的?或者說,成功的國際傳播的理想標志是什么?很多已經取得較好傳播效果的國際傳播案例證明:成功的國際傳播其文本所蘊含的價值最終在文明互鑒中融合成為接受方文化乃至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認為,這就是成功的國際傳播的“理想標志”。
從文化的國際傳播看,我國的《紅樓夢》《好一朵茉莉花》,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作品或理念的國際傳播受到了廣泛的認同和接受,還有域外的德國古典哲學、俄羅斯文學在我國傳播過程中的接受效果等,都具有這樣的特征。作為文化產品一部分的新聞的國際傳播同樣也具有這樣的特征,比如不久前的“云南大象北上”的報道等……可以肯定,這些案例都是比較成功的國際傳播,它們都程度不同地融合成為了接受方文化的一部分,乃至人類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常說的“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不同價值觀的交匯與認同”,以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等……其根本目的和追求目標都在于此。
我們在上述討論“理想標志”過程中,特別地強調了“文明互鑒”問題。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成功的國際傳播本身一定是不同文明的“互鑒”與“融合”的結果;另一方面,對這一結果之所以如此的研究要求我們,揚棄在已有國際傳播研究中已經習慣的“比較”“交流”的研究范式,努力形成平等的“互鑒”研究范式,并以這一研究范式的原則、方法進行相關研究,為上述成功的國際傳播“理想標志”的確立和“價值認同”的實現,為解決數百年來文化國際傳播中所面臨的異質性沖突等等難題,提供學理依據和破解工具。
二、價值遵循:全人類共同價值
成功的國際傳播的“理想標志”確立之后,我們就應該而且可以討論國際傳播中最關鍵的問題——“價值認同”問題:我們應該有怎樣的“價值遵循”才能達到這個“理想標志”?
數百年來,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中之所以面臨異質性的沖突、有效性的檢驗、原創性的焦慮等難題,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價值認同的“闡釋立場”難得共識——也正因此,“全人類共同價值”理念的提出,為解決這些難題提供了可能,并為互鑒式的國際傳播及其研究開辟了廣闊的空間。
我們知道,無論如何強調傳播學的真實、客觀、公正等規則,我們都必須承認,傳播的闡釋立場是客觀存在的。進一步說,在任何精神產品及其傳播過程中,傳播主體與接受主體的闡釋立場都是客觀存在的,而這個“闡釋立場”也正是“價值認同”的基本指向。一味地強調只有自己“闡釋立場”的“正確”,是文化霸權的表現,是對“共同價值”的拋棄。成功的國際傳播其關鍵就在于,尋找并遵循傳受雙方價值的共同之處,并以此來確認自己的闡釋立場。這樣才能為平等、交流、共享的“文明互鑒”提供可能。
國際傳播中的“傳播”當然很重要,但這并不是傳播的目的,傳播的目的在于“接受”——“接受”的關鍵在于“價值認同”,沒有基本價值認同的國際傳播是不可能成功的。
哲學上的“價值”,是指特定客體屬性對主體需要的意義,它所彰顯的是客體是否滿足主體的需要。就國際傳播而言,本文討論的“價值”是指傳播文本的思想價值、藝術價值或新聞價值。這里的“價值認同”是指傳播文本的內容屬性對異域受眾的意義——正是從這樣的角度看,著眼于人類普遍幸福的“全人類共同價值”這個重要理念,因其充分詮釋和體現了全人類共同的利益關切和價值追求,所以才可能易于被異域受眾認同和接受。
豐富多彩的文化是全人類的共同資源,以文化殖民為目的的西方“普世價值”漠視了不同文化間的平等交流與互鑒融合,而“全人類共同價值”正是以平等交流與互鑒融合為基本前提和導向的。在全球化境遇下,探尋并確認具有普遍“共同價值”的路徑是人類通往美好未來的必由之路……這些也正是成功的國際傳播與接受的最重要價值基礎,它為成功的國際傳播提供了學理依據,也提供了現實可能。
首先,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國際傳播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為解決數百年來文化國際傳播中所面臨的異質性沖突等難題提供了破解工具。一般認為,中華文化具有重視人倫道德、倡導忠君愛國、追求中庸和諧等特點;西方文化具有人本意識、理性思維、超驗追求等特征……從“價值認同”的角度看,欲使一種文化最終融合成為域外接受方文化乃至人類文化的一部分,難度很大。但是,因為“全人類共同價值”超越了國家、民族和意識形態的界限,蘊含了全人類共生共在的倫理金律和理性思考,恰切處理了人類文明多樣性與統一性的關系,所以成為了不同國家、民族利益訴求的最大公約數。它從最廣泛的人民利益出發,代表著超越國家、階級、團體和個人私利的公意,兼收并蓄不同文明價值觀的精髓,傳承和發揚“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主張。因此,它既為全世界攜手構建持久和平、文明互鑒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實現的可能。
其次,全人類共同價值為互鑒式的國際傳播開辟了廣闊的學術空間。它因文明互鑒而誕生,也因文明互鑒而續存。在這樣的過程中,因為各個不同主體間的自主與平等,而達成相互尊重、相互溝通、相互影響的互鑒融合關系。主體在承認“他者”存在的基礎上,尊重不同主體視域的差異性,立足于對方視角而理解“他者”,置身于歷史視野容納過去與當下,從而實現不同視域的融合。這正所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就國際傳播而言,其“客體”——傳播文本(原作、譯作、新聞報道),“主體”——傳受雙方(作者、譯者、記者和異域受眾),也因其“視域融合”而促進了“價值認同”。此處需要強調的是:我們這里所說的“主體”,既包括國際傳播中的“傳播主體”,也包括國際傳播中的“接受主體”。而且,在國際傳播的過程中,還經常會出現傳受兩大主體相互“換位”與“互證”的情況,即成功的國際傳播最終是通過兩大主體(傳播主體與接受主體)的互相作用、互相認同而實現。也正因此,我們才說成功的國際傳播是在平等交流、相互比較基礎之上的“互鑒”與“融合”,是異域文化成為自身文化一部分的一個必然過程。在國際傳播這個互鑒與融合的過程中,我們需要高度重視這樣兩個問題:
第一,反對居高臨下的“文明優越論”,堅持文明的平等性、尊重文明的多樣性。每一種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都凝聚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獨特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著自身存在的必然合理性。文明從來就沒有高低優劣之分,所以必須反對文化霸權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以平等的態度尊重不同文明,從而更好地展望和把握全人類共同價值的今天和未來。
第二,堅持文明的和合共生、互鑒互學,“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融合,因融合而發展。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正是不同文明的支流源源不斷地匯集到一起,才形成了全人類共同價值的主流。在不同文明的交流、比較、互鑒中,各個不同文化傳統的主體會自覺地互相吸取有價值的元素并為自身所用,同時也在不同文明的“他者之鏡”的映照中,各個主體通過反思自身不足,取長補短,從而實現了自身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基于上述認識,搞好我國文化(新聞)的國際傳播,需要做出這樣一些努力:一是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理念為價值認同的闡釋立場,將“全人類共同價值”作為我們做好國際傳播工作的價值遵循。同時,把這種理念切實融入我們的傳播話語和敘事體系之中,充分體現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共同性”,努力擺脫敘述與闡釋的局限性。既要自主自信地向世界表明自己的觀點,又要平等而理性地按國際傳播規律辦事,尊重接受者的主體地位,努力實現傳受雙方的相互尊重。二是在不同文明交匯處挖掘、講述中國故事。從中華文化、中國與世界的交往,以及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尋找優質資源;從共性、共情的角度優化國家敘事、媒體敘事、民間敘事機制及其話語體系,進而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
三、實現路徑:審美的傳播
成功的國際傳播的“理想標志”與“價值遵循”確立和明確之后,需討論“實現路徑”問題。“融合為接受方文化乃至人類文化的一部分”這個“理想標志”,在決定了傳播者價值取向和闡釋立場的同時,也決定了成功的國際傳播的實現路徑,即“審美的傳播”。
“美”是全人類的共同追求。在美學的經典定義中,康德的“美”,是“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形式”;黑格爾的“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兩者意思很有相似之處,只是黑格爾把康德的“合規律性”的實現方式進一步闡釋為“感性”地“顯現”。什么是“感性顯現”?就文化(包括新聞)的國際傳播而言,“講故事”就是最好的“感性顯現”——所有的故事都是不同的,都是感性的——“講好故事”的傳播,就是“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傳播,也就是審美的傳播。
成功的國際傳播一定是“審美的傳播”,是因為它既強調傳播文本理念的“合目的性”,也強調傳播文本形式的“合規律性”。這里所謂理念的“合目的性”,就是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這個重大理念,在“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這些方面實現傳受雙方的價值認同;所謂“合規律性”,就是按國際傳播規律辦事,尊重傳播過程中傳受雙方的主體地位,“感性地顯現理念”——“講好中國故事”,實現傳受雙方的情感共振,使異域接受者易于接受、樂于接受。
應該看到,在目前的傳播學理論及其實務中,關于傳播“技術”的研究是比較充分的,而對其作為精神產品所應具有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共同目的的重視和研究是相對薄弱的。這種情況導致了當下的國際傳播理論較多局限在具體傳播原理、傳播方式等相對側重技術規律和手段層面。技術手段的改進和完善當然可以解決很多表層難題,但難以解決根本問題……就此,我們必須重新確認這樣兩點共識:
一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傳播學、新聞學研究的根本目的,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一樣,都是要促進社會的文明進步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現實中諸學科界限之所以涇渭分明,原因是各自實現這個根本目的的邏輯路徑和技術手段的不同,而導致了今天各個學科的不同分類而已。但是,這并不意味我們就可以只重視手段而忘了目的,所有的“手段”都是為“目的”服務的。如果我們的學術研究較大程度地陷入各自“學科專業”的技術層面的研究,而忽視了對“根本目的”的追求,那就本末倒置了。
二是從傳播實務的角度看,那些廣受贊譽的經典、名篇,無一不是深刻關注社會的文明進步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個“根本目的”的,它們都是深刻地關注人的幸福和快樂的——也正因此,它們才受到各方的認同和接受——成功的國際傳播尤其如此。說來道理也并不復雜:盡管不同國家、民族、文化傳統的受眾各自有著千差萬別的“接受偏好”,但作為“人”,大家對幸福與快樂這個“共同價值”的追求卻是相同的。
這兩點共識決定了“成功的國際傳播一定是審美的傳播”的邏輯思路和最終結論:就傳播的“合目的性”而言,人文關切就是審美關切,審美關切就是人文關切,所以成功的國際傳播就必須從“人”出發,從全人類共同價值出發,關注人,關注人的共同性;就傳播的“合規律性”而言,成功的國際傳播就是要以平等、交流、共享的互鑒方式“講好故事”,實現“理念的感性顯現”。所以,成功的國際傳播必須實現“審美的傳播”。
具體講,“審美的傳播”包括兩方面含義:

第一,傳播文本內容及其價值取向的最高境界,必須是對“人”的幸福、解放、超越,或痛苦、艱難、困境等人類普遍性問題的深刻而真實的探究與表達。即,它們一定是“關注人”的,既關注人的物質需求,更關注人的精神需求。而且,國際傳播中這個“關注人”的價值取向,既不能僅是傳播者的,也不能僅是接受者的,而應該是傳播者和接受者所共同認可的。所以,以“人文關切”為基本特征的“審美關切”的最高價值遵循,就是“全人類共同價值”這個具有“人類共性”的價值追求,這也正是不同國家、民族、文化傳統的接受主體千差萬別的“接受偏好”的“最大公約數”,即傳播文本中所蘊含的超越了地域和種族限制的“人類性”的共同價值。
第二,傳播文本形式及其想象意蘊的最高境界,必須是盡可能最大限度地體現人類審美的獨特性、共通性,遵循傳播的規律性。所有文化產品的經典文本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它們都是“獨特”的,獨一無二的。傳播文本所包含的獨特民族文化與本土經驗、異域特色的多少等,是它們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的重要指標,也是國際傳播規律的必然要求。同時,它又因為體現了審美的“共通性”而自然地使域外受眾易于接受、樂于接受。“獨異”因其獨特的本土氣質而散發出迷人的異域特色,吸引著接受者的閱讀興趣;“共通”因其理念相通并符合傳播規律而使得接受者易于接受、樂于接受,甚至產生巨大的情感共鳴……我們之所以一再強調要高度重視傳播文本對人類共同價值的挖掘和獨特想象意蘊的體現,其學理依據也正在于此。

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國際傳播要實現審美傳播,傳播者和接受者具有同樣的主體地位——“接受主體正在全面崛起”,這對我們比較習慣的“我說你聽”“我傳你受”,是個具有顛覆性的挑戰。同時,又因為傳播技術、手段的日新月異,甚至勢如破竹,“技術為王”“流量為王”“算法為王”等認識和做法也頗為流行……但是,媒介的再大進步也不能改變精神產品傳播的根本目的和科學規律——成功的國際傳播還是必須堅持“內容為王”,而且一定是關注“人的共同性”和按傳播規律辦事的“審美的傳播”。所以,國際傳播中的傳播主體應該把“全人類共同價值”上升到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堅定地以人文關懷作為自己的闡釋立場,在承認接受主體(異域受眾)千差萬別的“接受偏好”的基礎上,努力尋找并遵循傳受雙方的“價值認同”——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把握“全人類共同價值”及其實現方式的“獨特與共通”對成功的國際傳播的意義和啟示。
四、未結束的討論
對“成功的國際傳播一定是審美的傳播”而言,我們上述討論還只是綱要式的討論,其中提及的諸多學術理論和實踐應用問題,尚需做更深入細致的研究。比如,在互聯網時代的當下,傳播實踐中已經明顯呈現出來的“接受主體正在強勢崛起”以及由此帶來的傳播主體與接受主體的“主體間性”問題,比如“國家傳播”“媒體傳播”“民間傳播”的關系問題、“自主傳播”與“他者傳播”的關系問題……還有,本文尚未談及的“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間的“傳播規律”問題、“傳播”與“宣傳”的關系問題、翻譯語言轉換中的“異化”與“歸化”問題,以及傳播主體如何對待國際代理機構及其“營銷策略與手段”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既是如何搞好國際傳播的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是無法回避的實踐問題。所以,更進一步深入討論這些問題,將對我們科學地總結國際傳播與接受的客觀規律,進而為搞好國際傳播工作實事求是地提供更有價值的對策和建議,都有著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