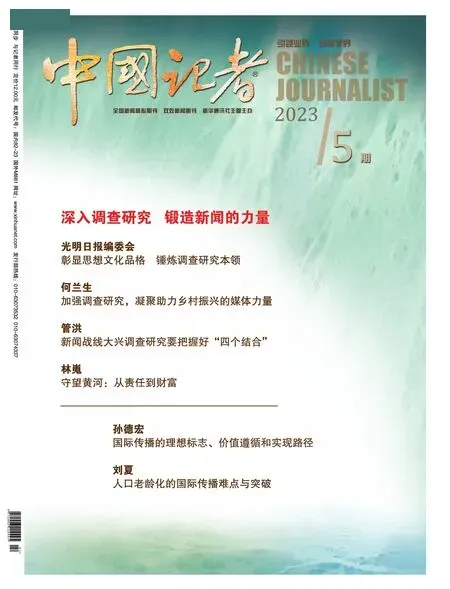深融背景下短視頻敘事能力重構
□ 黃義偉 秦亞洲
當前,智能傳播技術邏輯主導的主流媒體小屏端豎屏成為新的媒介視聽傳播空間載體,媒介話語邏輯建構也因之產生新的勢能與裂變。融合新聞生產的邊界不斷突破與突圍,手機端豎屏的信息呈現、敘事能力與輿論引導能力成為衡量新型主流媒體有效傳播效果的主要指標之一。進入Web3.0階段,習慣于社交媒介的“Z世代”審美品味、情感與消費偏向均發生重要變化,碎片化、輕量化的閱讀習慣使得主流媒體的敘事場景出現了“大屏—小屏—橫屏-豎屏”的轉向。
一、視聽傳播轉向豎屏精準化、聚焦化的特征表現與敘事模式
(一)豎屏視聽傳播前臺后臺空間區隔變小,單屏新聞容量更為緊湊
目前,短視頻新聞主流呈現方式以豎屏為標配,除了一些電視臺將電視新聞畫面仍以橫屏剪輯發布在B站、小紅書等平臺外,在抖音、快手等平臺則很難再見到主流媒體以橫屏形式發布短新聞。與橫屏形式相比,豎屏視聽傳播敘事傳播前臺后臺空間區隔變小,單屏新聞載體容量更為緊湊,“在敘事語態上,短視頻新聞的場景敘事呈現出生活化、臨場感與社交化的鮮明特征”。[1]這種方式更適合作為社會網絡中樞的個體用戶快速刷看視頻。
融媒體建設的推進以及用戶使用手機收看新聞習慣的改變,加速使“橫屏”展示的主流狀態轉向“豎屏”,即使日常新聞資訊無影像也要編發成動態文字影像進行推送。豎屏視頻9:16顯示畫幅,新聞信息要在3分鐘以內通過分屏形式敘述完畢,并實現傳播效果的二次、三次轉發效應。從手機界面物理空間對照來看,與紙媒圖文版面空間、電視圖像視覺相比,豎屏均以壓縮呈現,首頁顯示的屏面信息成為導讀引流的關鍵。
戈夫曼在其著作《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中闡釋擬劇理論時引入戲劇表演中的“舞臺”一詞,將舞臺劃分為前臺和后臺,“前臺”能夠實現選擇性呈現,不符合觀眾期待的行為隱藏在“后臺”。進入網絡社會,“前臺”更適合通過文本和視聽方式在大眾面前呈現出“框定”后的舞臺形象,而“后臺”則是相對自然的自我狀態。移動互聯時代信息傳播更為暢達,后臺區域又逐漸成為前臺表演的新空間,而從大屏到小屏、橫屏到豎屏,傳播者與觀看者的空間關系發生顛覆性變化,手機界面也從動態屏幕轉為實時屏幕,豎屏視聽傳播前臺后臺空間區隔變小,越來越多的日常生活場景進入到短視頻表達與呈現中,成為用戶關注的信息。
豎屏畫幅的呈現與播放方式更易讓用戶進入到移動化沉浸式觀看模式。為牢牢抓住用戶,基于算法推送機制下的流量考慮,同時遵從新聞價值因素、輿論引導與傳播效果,主流媒體短視頻所呈現的新聞或信息首先需要在時效上快速反應,迅速播發,不再等“塵埃落定”的節點式新聞增多。因此,能夠納入傳播者視聽視野的內容則更為分散,屏幕空間高度濃縮,單屏新聞容量更為緊湊,甚至對于信息量密集分屏過多的短視頻提供“倍速播放”,促成用戶短時駐留快速獲取信息。
(二)豎屏視聽故事空間和話語空間視角增多,屏內新聞要素更為繁冗
在敘事研究中,敘事空間包括“故事空間”和“話語空間”。其中,“故事空間”指事件發生的場所或地點,“話語空間”則是敘述行為發生的場所或環境。[2]敘述觀察的視角既有觀察者處于故事之外的“外視角”,如全知視角、第一人稱主人公敘述中的回顧性視角、第一人稱敘述中見證人的旁觀視角等;又有觀察者處于故事之內的“內視角”,如第一人稱敘述中的體驗視角。在由橫屏到豎屏的轉換過程中,原來大屏模式中的新聞主播、出鏡采訪記者、新聞當事人和新聞現場見證人、旁觀者的視角在短視頻的敘事空間中不再聚集式出現,紛紛淡出或者有選擇地出現甚至變為同期聲,新聞數目較以往呈現量產化特征。與此同時,當某一類重要新聞發生時,最先出現在現場的短視頻用戶及跟進者“隨手一拍”的記錄、上傳與傳播,也是敘述視角各異,豐富充實新聞信息增量的同時,使得屏內信息過載。
在融合新聞傳播中,除了文字、聲音、圖形、圖像之外,動畫、游戲、VR、AR、MR等元素均可以附著在小屏界面進行意義的生成,智能傳播技術的不斷升級更迭又增加了傳播主體的駕馭難度,尤其是利用人工智能自動生成的突發事件、體育、財經等資訊類新聞的廣泛出現,使得視聽數字媒介敘事空間變大,有利的一面是信息獲取的便捷觸達,更能為用戶提供有效的個性化、定制化資訊服務,增強用戶的黏性并固化使用習慣;不利的一面則體現為與原來的大屏相比,屏內有限空間內的新聞要素更為繁冗,用戶獲取信息的視覺舒適度降低。
泛媒化驅動信息傳播更為復雜和多元呈現,主流媒體視聽傳播對敘述視角增多的回應也更注重互動性。一方面,媒介短視頻化的新聞呈現,使得新聞的可消費性增強,用戶打開視頻留言區互動概率較以往增強;另一方面,除重要新聞之外,任何時段媒介都可以安排更多的信息作好服務對接,而不再受限于以往固定的出版頻率、周期,以及對應的新聞欄目來安排生產、播報。融合新聞智能發布、傳播,新聞用戶24小時在線在場接收場景無限擴大,可隨時隨地刷取新聞,新聞采編、發布的數量與更新頻率形成強關系,碎片化、移動化與時新性、功能性交織混融。
(三)豎屏視聽新聞主題精確、敘述立體,屏間場景缺勾連、易撕裂
以大屏為主體的視覺傳播能夠充分地運用推拉搖移等視覺展示手段,借助蒙太奇等方法傳達更精確的新聞主題,而豎屏視聽傳播敘事使用的表現手段則只適合特寫、小場景等類型報道,聚焦主體多元、采訪因素過多的內容則無法在一個短片中充分表達,需要生成多個短視頻而后整合才能完整傳達主題,但在傳播、分發過程中會因屏間場景缺少勾連產生斷裂、撕裂效果,“通過對碎片化新聞事件的觀看,受眾僅能捕捉事件的單一或少量要素,受眾對事件本身的感知度、記憶度等均較低”[3]。

在傳統媒介發展階段,由于受眾群體龐大,媒體平臺單一,新聞報道中的媒介話語更善于在宏大敘述與微觀體驗中尋找平衡點,以滿足在固定節點固定版面(節目)中的傳播覆蓋促成媒介傳播輿論的共情共識效應。而進入媒介融合的今天,新聞信息通過短視頻的表達與傳達切換到用戶手機小屏微觀體驗界面,則更注重接收者的“面對面”屏幕溝通的交流思考和深度連接。
消息、通訊題材的報道,甚至是深度報道類的內容轉化到小屏端需要二次加工與生成。人物專訪、新聞專題的畫面變為短視頻的即時信息流,需要滿足用戶視聽需求跨屏編播編導,或者基于移動收看新場景在編播前就要編輯記者介入前端生產,整個編采制播流程需要兼顧分發場景、適配狀態必須始終保持前置化,媒介編輯部人力資源配置成本大大增加。
二、視聽傳播敘事策略與敘事能力創新路徑
媒介深度融合與技術賦能加持,促使融合新聞新形態不斷有了多端兼容,“一次采集+多次生產+多平臺分發”也具備了“元敘述視角”生成的可能性。新型主流媒介視聽傳播豎屏內容生產能力、敘事能力創新,需要從敘述表達主題與新聞視角、產品可視性與敘述美感、敘事語態書寫與用戶深度參與三方面進行強關系梳理、表征,形塑新的主流媒體“屏媒”媒介話語,并重新聚合媒體生產和分發邏輯。
(一)新聞選題切口小,故事講述視角更聚焦
主流媒體融合新聞小屏端豎屏媒介敘事能力重構,不是媒體內容生產的傳統媒介端的“源產品”進行瘦身后“搬運”至第三方平臺官方賬號,否則,在媒介空間話語表達中,傳統媒體便容易被邊緣化。因為,今天的用戶所擁有的屏端選擇權具有高度自主性,媒體的編排手段、表達方式不具網感,就會被迅速劃掉、刷掉,在算法機制的支配下,就會難以再度讓新聞或信息與用戶相遇。因此,融合新聞的生產在媒介端的敘事能力需要通過視聽語言構建新的媒介圖景,采用新語態表述呈現,敘事動力集中于策、采、編、審、播、評、饋等環節精細化、精深化呈現編排,敘事文本關聯小屏界面將新聞選題切口變小,新媒體敘述視角切碎,挖掘好“隱喻”要素,充分在手機“屏媒”界面闡釋、傳遞與生發新的符號意義。
主流媒體媒介敘事能力提升除了在信息層面進行深度開掘,還要在“新聞+政務+服務”方面進行延伸拓展,實現小屏與大屏協同共頻,界面前與界面后響應共鳴。比如,津云新媒體在其客戶端、北方網等平臺推出的短視頻作品《臊子書記》,沿用傳統紀錄片拍攝方式但增加了用3D做“扶貧日志”、MG動畫展示“扶貧創意”,讓微視頻更具微綜藝化,可看性與趣味性充分兼顧。片中運用的多處“隱喻”,重在表現出大寨村美好的明天,小屏端豎屏展示新聞主人公宋鵬“大頭照”,夫妻對話與網友互動等情景旨在通過小切口反映精準扶貧大主題,信息傳播與輿論引導效果并重。
(二)關注“公共敘事”:數字知識產品可視化,傳播美感質感

數字傳播生態下,媒介工作者的工作中心與職能有了新的賦能,在整個采編流程中可以充分將數字知識產品理念融入主流媒體的全鏈條策劃、生產、加工與宣發中。
媒介融合推進至縱深階段,H5、VR等新聞形態可以更好地為小屏端豎屏營造沉浸體驗,實現視聽故事空間和話語空間中的敘述視角的多模態,打通閱讀時空界限,增強高價值濃浸潤性的閱讀收視體驗。比如,人民日報社新媒體中心出品的手繪長圖H5《復興大道70號》在手機端共用了55屏,其中涉及500多個歷史事件和場景,并且還能在淘寶平臺通過搜索關鍵詞自動彈出長圖,北京、廣州、成都等多地推出“復興大道70號”地鐵主題專列、地鐵主題長廊、主題店等,打造“網紅打卡地”,快閃、直播等多種形式使知識產品可視化為“當代版清明上河圖”,網上網下的社會傳播效應協同一致。

知識產品可視化通過為新聞提供背景新聞或新聞劇目展映、新聞游戲開發,實現敘述視角與話語空間的深度關聯,個體體驗感增強的同時又為主流媒體的品牌傳播力實現美學意義上的關聯。“我的Daily”“我的Vlog”“我的觀察”等一系列依托社交媒介話語表述生態空間打造的可視化產品也是贏得年輕用戶的關鍵話語場域,從而真正在媒介敘述的語境中實現用戶的深度代入。聚焦年輕新農人的新聞微紀實“普利橋種糧記”系列短視頻,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焦點訪談”欄目、湖南廣播電視臺新聞中心、永州廣播電視臺聯合攝制,在進行新媒體豎屏敘事方面的深度嘗試過程中也將“屏媒”傳播的美感、質感輸出,實現傳播效果的最大化。2022年9月上線的《普利橋種糧記·夏管篇》每集時長全部縮短到3分鐘以內,而且還充分運用數據畫像精準定位,除表情包、加花字、網感配音配樂等貼近年輕用戶的敘述方式外,故事講述采用真人秀、網綜等表達方式,呈現內容的可視化,傳播效果更立體。
(三)關照“個體體驗”:書寫向善向美敘事語態,吸引深度參與
主流媒體在傳遞社會核心價值,協同開展數字化治理過程中,融合新聞小屏端豎屏具有直接的“面對面”優勢,立足于這種關系邏輯基礎上的媒介報道,實現了新聞主題和敘事主體的雙向兼顧,注重延續社交媒介的核心基因,關照手拿小屏的個體體驗嫁接,適應互動表述、關系邏輯關照下的故事空間場景。與此同時,“吸納和‘打撈’網絡空間中形成的海量話題反哺自身”[4],增強網絡關系節點上的新聞生產,書寫向善、向美的敘事語態,吸引年輕用戶深度參與。抖音、快手端的小屏系列短視頻“主播說聯播”與電視大屏上的“新聞聯播”形成了協同效應,“主播說聯播”話題設置,與短視頻評論區共同開創了新時代現代媒介話語表述、溝通與形成輿論場的綜合效應,主流媒體的“屏媒”界面傳播能力得到全面呈現,主播的口語式表達、網絡語言與網感的背景音樂共同提升了年輕一代用戶的“屏媒”信息體驗,甚至還帶動了主流媒體多個端口的節目聯動效應。
媒介訊息的深度化呈現需要從“屏媒”敘事空間構建上進行“路標”引領,短視頻碎片化的特點雖然滿足了即時推送與獲取,但吸引用戶到主流媒體新媒介賬號進行長時間查看、觀看,滿足深度信息需求時更需要入口索引,目前這一點在多家媒體號呈現粗線條、分散化。例如,主流媒體在抖音、快手、西瓜等賬號主頁處設置專題頁、專題標題,還可以做出相關鏈接,類似的像短視頻“首頁合圖”形成專題熱點導引視覺沖擊力,能夠幫助用戶駐留翻屏“瞬時”第一時間找到入口,增強留駐度與黏性。
三、結語
傳統主流媒體在向新型主流媒體轉變的過程中,媒介話語傳播與敘事功能、敘事空間等能否圍繞“思想+藝術+技術”開拓、創新構建全媒體傳播體系,需要兼顧豎屏媒介敘事場景中出現的新特點與新特征不斷調試與創新:生成“公共時間”,新聞選題切小,故事講述視角更聚焦;關注“公共敘事”,數字知識產品可視化,傳播美感質感;關照“個體體驗”,書寫向善向美敘事語態,吸引深度參與。新型主流媒體視聽傳播敘事策略與敘事能力創新,有利于真正構建、塑造好主流輿論引導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