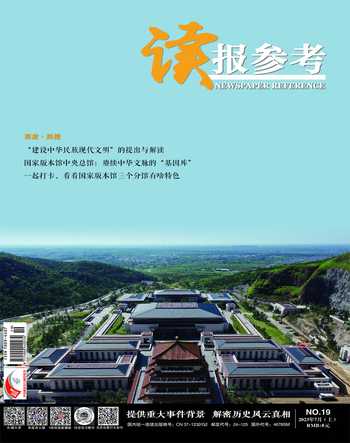中國“最窮”導演,帶全村翻拍“三國”
在牛糞和柴火燃燒的味道中,伴隨著狗叫、雞鳴和拖拉機馬達嘶鳴聲,一個紅遍全網的影視基地正在逐漸成型。他們用了一上午,才把23根木材運到田野的一處平地。這些木材并不是被清理的建筑垃圾,而是鮑小光以每根十元的價格盤下來,用來制作拍攝所需的城墻的物料。過去的兩年,他就是用這種笨拙且原始的方式,攢出了一個劇組,建成了一個初具規模的“影視基地”。
從鮑工到“鮑導”
15年前,被騙去北京做群演的鮑小光,從未想過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鮑導”。那時候的鮑小光只有17歲,忙碌于服裝廠的流水線上。他不甘于日復一日地做重復性、機械化的工作,想去做演員。網上的一條群演招聘信息,讓他第一次有了冒險的念頭。
他一個人跑去北京,交給中介500元后,被安置在影視基地旁邊的村莊,中介說“有戲了就通知你”。但直到積蓄花光,他都沒能再收到中介的消息。意識到被騙后,他開始在飯店、KTV和工地謀生。這期間,他也嘗試過寫歌,“每個月的工資都會用來去做歌,找人用電腦制作的那種伴奏,做了好多的MP3”。
2018年,鮑小光回老家了。農村的年輕人越來越少,興許會有些機會。他開了一間裝修公司,主要做硅藻泥涂料,但是村民對這種新型材料的接受度并不高。公司不到一年就倒閉了,他又從“鮑總”變為鮑工。后來,給裝修隊幫忙的期間,他開始接觸到短視頻。那已經是2021年,一個幾乎人人都是短視頻創作者的年代。
農村向來都是內容富礦,但無論是紀實或是創意,這條賽道也早已是一片紅海。前有李子柒、張同學,后有手工耿和導演張策,新晉選手起步已經越來越難。初嘗創作的鮑小光,視頻風格并不固定,時而記錄鄉間田野生活,時而制作現代搞笑短劇,但都沒什么傳播效果。直到有一天,他突發奇想,不如拍一個“說阜南話”的《三國演義》。
鮑小光自稱迷戀三國文化,但他對于《三國演義》的回憶卻是模糊的,只能隱約記得小時候有長輩提到“三國名將呂蒙是阜南人”。問及喜歡的原因,鮑小光說“因為趙子龍,他的打戲好看”。“土味三國”的雛形,也正是由一位慌張小兵和一位傀儡丞相,共同擊退“敵人”的故事組成。雖然剪輯粗糙、噱頭笑聲也十分出戲,但在評論區里,依舊可以輕易捕捉到大量被鮑小光才華所吸引的觀眾。
出圈的不只鮑小光,還有“丞相”和“盧帝”。“丞相”的扮演者是鮑小光的遠房舅舅,這位名為李華東的七旬老人,是第一批陪著鮑小光玩短視頻的人,如今也成了劇中辨識度最高的主演之一。而劇中的女將“盧帝”,本名為盧紅玲,是一位嫁到臺灣的女商人。因為疫情無法回臺,在村里大片的閑暇時刻,讓她開始嘗試來劇組做攝像師。
雖然拍攝“拍得手都疼”,但盧紅玲學得很快,逐漸成了鮑小光的固定幫手。后來在一位主演退出劇組后,盧紅玲頂了上去。“效果很好,給了我更多靈感”,鮑小光說,盧紅玲的加入激活了“三國”。盧紅玲來了后,不僅解決了主演的問題,群演也充裕起來了。他們幾乎都來自“開心俱樂部”——那是盧紅玲媽媽建立的、專供鎮上老人嘮嗑的地方,里面的“會員”大多身體健康、樂觀開朗,不排斥新鮮事物。
演員幾乎是能用就行,設備也一樣。所有拍攝都是用手機完成的,鮑小光也嘗試過單反相機,但“拍完還要從電腦里導出,太費事了”。他不喜歡用電腦剪輯,“手機剪片一周就學會了,也挺方便”。
組建劇組相當于是創業,自然免不了談錢。算上演員的日結薪資,一集《土味三國》的平均成本在400元左右,每月更新4-5集。視頻的播放收益,再加上偶爾的直播,讓劇組的收入保持在6000元以上,好的時候能過萬。“反正夠開銷”,鮑小光說。
“太專業,就會失去土味的靈魂”
對鮑小光來說,寫劇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情況下,劇本一般有200多字。鮑小光承認自己會拖延,有時兩天就能寫完,但有時也需要花費10天以上,最大的糾結是文戲與武戲的占比。實在寫不出來時,他會選擇改編《三國演義》里的劇情。“臺詞改成方言也能拍,但是這種流量不好,還是自己原創的好。”他認為,“改到自己都笑了,就是好劇本”。
他也把視頻的出圈歸功于“搞笑”。“和正版三國比起來,我們的語言比較犀利,然后用詞就是比較土;為了節約成本的道具,反而成了特色;粉絲主要是中年男性,比較搞怪比較土,他們喜歡。”
在鮑小光眼里,短視頻就是內容為王。“沒有好的劇本,再好的場景也不行。”但是,他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還是分配給了場景搭建和道具制作。記者到達時,他正在籌備搭建一座新的城樓。原本計劃白天就完成的工作,一直到凌晨1點才收工,“跟我以前干裝修差不多了”。
道具制作亦如此,演員們佩戴的帽子、戰袍和武器,都由鮑小光親手繪制。“它就是一個裝飾,你也得給它弄出來,要讓視頻盡可能接近古代戰場的真實場面。”親手繪制的帽子,耐克標志代表將軍,阿迪標志代表士兵。
拍攝當天,鮑小光的院子總會變得異常擁擠。演員們很少遲到,“叫了10個但是來了12個”是常態。在這個片場,戲服和道具都放在院子的顯眼處,裝在兩只白色的桶里任人挑選。群演們的注意力都在服裝上,人人都說“給我留件好看的”,至于接下來要拍攝的內容,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追問。他們都說,“不用問,反正都是好事”。
懵懂的不只群演,還有主演李東華。盡管出演一年之久,但他對“丞相”這一角色依舊很陌生,對于捧紅他的流量機制,更是一無所知。由于常年飲酒,他的手一直在抖,記憶力也迅速退化。記不住臺詞的時候,他會給自己施壓:“下次一步到位!”
在這間野生劇組里,主演們往往都是在開拍前才熟悉劇本。一個常見的流程是先拍群演,再拍打戲,最后補一些主演的鏡頭。因為對群演們來說,“下午接孩子”這件事的優先級高于一切。打戲是鮑小光在開拍前一天晚上唯一會擔心的環節,因為拍攝的效果并不可控。有搞武術的人提出可以來指導合作,但鮑小光擔心還要包吃喝,費用太貴,并未對邀請表現出熱情。鮑小光認為,“太專業,就會失去土味的靈魂”。
以“土味”出圈,以“土味”破局
鮑小光紅了。剛做視頻的第一年,他覺得粉絲破萬并非易事,結果年底時,粉絲達到20萬;第二年,他把目標定為30萬,結果再次高于預期,他的粉絲數突破40萬。
開始有媒體對他產生好奇,也是在那個時候。那是去年11月下旬的一個晚上,當鮑小光剛剛結束拍攝,打開視頻軟件時,他收到一條不同于以往的私信:“你的電話多少,我想采訪你一下。”鮑小光的第一反應是要錢嗎?要錢就不干。在反復確認不收費之后,鮑小光與記者開啟了一場持續半小時的問與答,“應付媒體比拍段子累多了”。
鮑小光信奉“肯吃苦”“夠搞笑”“獨一無二”是他出圈的原因,因此,他也會給出“多去嘗試,別怕失敗,劇本好了自然就火了”的建議。但偶爾,鮑小光也會回過頭,去思考“當時那個熱搜到底是咋操作的”,他承認“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有人給他炒作一下,說不定就能“掙到錢”,可惜現在已經錯過了。
盡管賬號在不少行家眼里已經很成熟,但他依舊排斥直播帶貨和廣告植入。在鮑小光看來,出名似乎比賺錢更重要,“希望今年粉絲量可以破百萬”“我拍視頻的最大動力就是成為名人,但不是什么流量都要”。
以“土味”出圈,便能以“土味”破局。這位死守領地的田野造夢家,終究還是在流量時代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位置。
(摘自《新周刊》詹世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