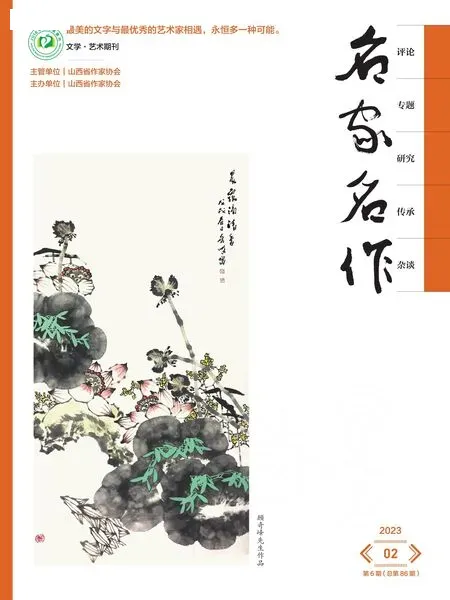論渝東北地區(qū)漢代樂舞百戲俑音樂學價值
王云龍 張 群 楊紹沖
一、渝東北地區(qū)漢代出土音樂文物的文化內(nèi)涵
渝東北地區(qū)古代音樂有著深厚的文化背景,如巫山地區(qū)出土距今約6000年的塤,為新石器時代作品,以“巫山為代表的峽江地區(qū),可能成為長江中游地區(qū)原始樂器的起源地”[1]。巴蜀地區(qū)由于地勢易守難攻,自古很少受到戰(zhàn)爭波及,兩漢時期經(jīng)濟富庶,《后漢書》有記載:“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五谷而飽。”[2]豪門階級興起,于東漢時期達到鼎盛,地主莊園經(jīng)濟發(fā)達,生活中娛樂性的歌舞百戲奢侈之風盛行,反映了巴蜀地區(qū)地主階級興盛及厚葬成風、樂舞百戲的世俗性較強。
兩漢時期關(guān)于渝東北地區(qū)文化的發(fā)展狀況,據(jù)文獻記載,萬州以東包括巫山在內(nèi)的今渝東、渝東南地區(qū),處于漁獵經(jīng)濟為主向漁獵、農(nóng)耕經(jīng)濟并重階段的發(fā)展過程中[3]。巴蜀文化與中原文化相互融合,此時期出土的樂舞俑、生活俑與武士俑后期逐步盛行起來,形成了侍俑、歌舞樂俑、生活俑、武士俑、文官俑等各具特色的人物陶俑,體現(xiàn)了地主豪紳生前享受生活的熱鬧場景[4];漢代的漢畫展示了歌舞百戲在宴飲、民間等場合大量出現(xiàn),呈現(xiàn)了宮廷雅樂與民間俗樂交融并蓄的局面,雅樂地位逐漸衰落,代之興盛的是民間俗樂,上層階級和民間百姓的審美觀念漸漸統(tǒng)一。同時,相關(guān)文獻與出土的漢畫中的樂舞百戲形象互為驗證,如張衡的《西京賦》[5]描寫了兩漢時期京城社會音樂文化典型活動場面、藝術(shù)形式及內(nèi)容再現(xiàn)京城典型的音樂文化活動場面。由此可見,出土的樂舞俑再現(xiàn)了漢代音樂文化的面貌,反映出漢代川渝地區(qū)民間音樂文化的興盛。
二、渝東北地區(qū)漢代樂舞百戲俑的音樂學研究
(一)渝東北地區(qū)東漢樂舞百戲俑的類別、組合與排列及形制等研究
渝東北地區(qū)出土的樂舞百戲俑是漢代雕塑藝術(shù)的代表,其數(shù)量之多、造型之豐富,反映了漢代樂舞百戲是中國古代表演藝術(shù)的精粹。樂舞百戲俑從種類上可分為樂俑、舞蹈俑和百戲俑;根據(jù)樂舞俑的形制,也可分為五類常見樂舞俑,分別為觀眾(撫耳)俑、舞俑、撫琴俑、擊鼓俑、吹簫俑。渝東北地區(qū)的東漢樂舞俑表現(xiàn)形式多樣,這些不同類俑的組合、排列,形成了鮮明富有特色的樂舞場面。下面論述出土的樂舞俑主要的幾類組合方式。組合1:擊鼓俑、舞俑同時出土;組合2:擊鼓俑、觀眾(聽)俑一起出土;組合3:撫琴俑、觀眾(聽)俑同時出土;組合4:吹簫俑(或吹損俑)、觀眾(聽)俑同時出土;組合5:擊鼓俑、舞俑、撫琴俑、觀眾(聽)俑同時出土;組合6:擊鼓俑、舞俑、撫琴俑、吹簫俑、觀眾(聽)俑同時出土。
從以上內(nèi)容可看出,樂舞俑常以組合形式出現(xiàn),反映了樂隊熱鬧的場面。首先,樂舞傭(有的組合)出現(xiàn)相同類別的俑有多個,如2001年奉節(jié)趙家灣東漢墓M7有擊鼓俑1個、舞俑3個、撫琴俑3個、吹簫俑4個、觀眾(聽)俑3個,該組合較為完整,反映了樂隊規(guī)模較完整、場面熱鬧,樂舞有舞蹈、撥弦和吹管樂、打擊樂器鼓作伴奏,鼓常作擊打節(jié)拍,琴和笛編制多人,編制較全,或可進行合奏等不同演奏形式,雖無音響資料證明,但據(jù)出土的文物組合可推測器樂組成的樂隊已常見于表演中。其次,觀眾(聽)俑、舞蹈俑、擊鼓俑、撫琴俑一起出土數(shù)量也較多,反映了樂舞常以樂隊形式熱鬧的場面。而觀眾俑與舞俑一起出土,似在描繪舞蹈在伴奏中翩翩起舞,反映了舞蹈與鼓的律動互為一體。再而,觀眾(聽)俑或者單獨與其他樂舞俑一起出土,如與擊鼓俑、吹簫俑、吹塤俑、撫琴俑一起出土,反映了撫耳傾聽演奏的場面,同時說明吹管樂、撥弦樂、鼓在當時或常以獨奏出現(xiàn),單個樂器或常獨立表演。《戰(zhàn)國策》記載“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6]。可見民間器樂活動的普遍及琴在這時已為重要的獨奏樂器。據(jù)文獻記載,“歌舞和歌舞藝術(shù)的發(fā)展對民族器樂的發(fā)展起到顯著作用。漢魏時期的相和歌就是用管弦樂器伴奏,歌者用節(jié)(打擊樂器)擊拍配合演唱的”[7]。我國民間歌舞藝術(shù)為詩歌、舞蹈、音樂三者緊密結(jié)合,但一般來說這是藝術(shù)發(fā)展歷史早期的形式,至我國詩歌和音樂高度發(fā)展的唐代,歌舞結(jié)合的藝術(shù)仍然為重要的民族藝術(shù)體裁,如漢魏時期相和歌到唐代相和大曲便如此,而后歌舞樂被更大綜合性的戲曲逐漸取代。盡管戲曲為更高的綜合藝術(shù)形式,但歌舞藝術(shù)仍作為獨立的藝術(shù)形式在發(fā)展。
以上出土的樂舞俑以不同排列、組合呈現(xiàn),反映了樂舞的使用場合、組合規(guī)律、編制構(gòu)建、樂器形制、樂隊規(guī)模等,再現(xiàn)了渝東北地區(qū)漢代民間歌舞樂繁盛的場面,其音樂學價值意義重大。
(二)巴蜀地區(qū)漢畫、樂舞俑呈現(xiàn)的舞蹈種類
漢代巴蜀地區(qū)經(jīng)濟文化發(fā)達,樂舞文化繁榮,這一時期漢畫像種類很多 ,其中樂舞圖像主要存于墓葬中的漢畫像石、畫像磚或者樂舞俑上。根據(jù)巴蜀漢畫舞蹈圖像,對巴蜀漢畫舞蹈按形式劃分為三大類:袖舞、鼓舞、雜物;而袖舞具體又可分為長袖舞、廣袖舞、垂胡袖舞、窄袖舞等;鼓舞又可分為建鼓舞、盤鼓舞等,雜舞又可分為巾舞、羽人舞等。下面分析袖舞與鼓舞。

男性短而寬的廣袖陶舞俑(重慶市博物館藏)

女性短而寬的廣袖陶舞俑(重慶市博物館藏)
袖舞是漢代舞蹈中的代表性舞蹈種類,長袖舞與廣袖舞為常見。傅毅《舞賦》[8]贊美長袖舞“似飛彎,袖如回雪”。巴蜀漢畫舞蹈中,長袖舞服的長袖如飄帶狀,舞者緊身、束腰、長袖或長袍拂地,舞蹈時常常有琴、瑟、鼓等樂器作伴奏,屬于專業(yè)的樂舞藝人表演,舞姿飄逸、瀟灑靈動。與長袖舞的長相較,廣袖舞注重寬度,有長而寬和短而寬,廣袖舞端莊典雅。據(jù)文獻記載,廣袖舞多應(yīng)用于漢代宮廷雅樂和宗廟祭祀活動中,前文所述,漢代巴蜀地區(qū)莊園地主階級興盛,故在宴飲等場合中也有出現(xiàn)。總之,長袖舞飄逸靈動更接近道家的自然之境,常與盤鼓舞相結(jié)合;而廣袖舞下垂厚重,更貼近儒家的方正,在百戲中也不失端莊。
鼓舞,邊鼓邊舞,同袖舞一樣,為中國傳統(tǒng)舞蹈的標志之一,以建鼓舞、盤鼓舞為常見。漢代建鼓舞使用了具有樂器屬性的道具——建鼓。據(jù)記載,漢代的建鼓舞被大量運用于宮廷禮儀、祭祀天地、戰(zhàn)爭指揮、喪葬和宴飲娛樂等場合,巴蜀漢畫中建鼓舞數(shù)量很有限。相比較少量的建鼓舞,漢畫中的盤鼓舞豐富可見。盤鼓舞,顧名思義,是在盤和鼓上面進行舞蹈的統(tǒng)稱,簡單的為盤鼓和舞者,較復雜的有樂隊伴奏,和俳優(yōu)兩到三個等,常見伴奏有管、蕭、鼓、琴、瑟、塤等。盤鼓為專屬的樂器,運用腳或其他部位擊打,或赤足或木屐,以打擊聲響節(jié)奏,因之為舞蹈伴奏,便具備樂和舞的兩種功能。舞者在盤鼓上完成復雜的動作之余,落在盤鼓上的節(jié)奏應(yīng)準確不亂,且需和樂隊相一致,可見難度很大。盤鼓舞的盤和鼓形制、質(zhì)地大小不一,盤小而鼓大(有代表星辰和日月的關(guān)系),它們相組合或各自數(shù)量沒有固定,如有一鼓的、二鼓的、多鼓的,盤有三盤、四盤、七盤的,也有一盤一鼓的、一盤二鼓的、七盤三鼓、八盤一鼓的等,盤與鼓多與象征的天體星辰有關(guān)。綜上,從建鼓到盤鼓,漢畫中的鼓舞樣式豐富,僅次于袖舞,而最為不同的是,鼓舞為真正意義上的“樂舞”——有樂有舞,其中樂的鼓點組成的樂譜為一套系統(tǒng),具有重要的音樂學研究價值。從這方面看,鼓舞的表達形式、風格特點當屬音樂學研究的重點。樂舞延續(xù)禮樂的主流傳統(tǒng) ,而俗樂也進入雅樂中,雅俗共賞,漢畫舞的分析和研究反映了巴蜀地區(qū)豐富的樂舞文化。
以上為漢畫中呈現(xiàn)的多樣化的舞蹈形式,下面根據(jù)渝東北漢代出土的樂舞俑來研究本地區(qū)的舞蹈狀況。東漢渝東北地區(qū)出土的舞蹈俑多為雜舞,即民間舞蹈。據(jù)文獻記載,民間舞蹈或由賓主或家庭成員自發(fā)抒發(fā)情緒起舞的舞蹈,而自娛性質(zhì)的舞蹈與百戲相結(jié)合,反映了雜舞在本地區(qū)的流行。這與西漢洛陽宮廷雅舞的端莊浪漫、表情嚴肅不同,雜舞顯隨意無太多嚴謹之風,也反映了世俗性。而出土的百戲俑種類較多,包括雜技、說唱、俳優(yōu)等,擊鼓說唱的俳優(yōu)說明了百戲活動的盛行,百戲題材的風俗化與數(shù)量的增加反映了民間具有雜耍的風俗與上層階級的融合。同時巴蜀地區(qū)為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也有外來西域人口聚集,這些民俗的特征也在百戲俑有所體現(xiàn)。巴蜀地區(qū)的百戲俑也融入少數(shù)民族的技藝,反映了民間藝術(shù)與宮廷藝術(shù)的融合及西南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與中原地區(qū)文化相互交流的情況。

東漢樂舞百戲俑畫像磚(四川成都楊子山出土)
綜上,渝東北地區(qū)出土了大量作為陪葬品的樂舞俑,這是比較常見的喪葬習俗,它以各種組合的方式呈現(xiàn)出不同的墓葬規(guī)模、形制,比較完整的組合有舞俑、觀眾(撫耳)俑、擊鼓俑、撫琴俑與吹簫俑,也伴隨其他人物俑形成一幅完整的畫面。一般中小階級使用較多,如中小地主、商人、中小官吏、普通平民等,反映了渝東北民間歌舞音樂文化的繁盛。
三、結(jié)語
渝東北地區(qū)出土的樂舞俑主要包括吹笛俑、吹笙俑、撫琴俑、舞蹈俑、說唱俑、擊鼓俑等,出土的樂舞俑以不同的編制而組合,多和百戲俑、人物俑同時出現(xiàn),結(jié)合此時期出土的漢畫像、漢畫石等圖像呈現(xiàn)。其中舞蹈俑常與演奏樂器的俑同時出現(xiàn),有時也有舞蹈俑與說唱俑、伴奏俑不同排列組合出現(xiàn),反映了當時民間或地主家宴、生活中的演繹場景,其中反映的不同編制樂隊奏響的音樂表現(xiàn)形式令人遐想,絲竹之樂深入百姓家。不同于前代宮廷的金石之雅樂,其民間的樂舞帶有隨興的雜舞、伴有情節(jié)的說唱,無不體現(xiàn)著民間音樂文化的興盛,這也與漢代樂府機構(gòu)對民間音樂的搜集、推廣有聯(lián)系,統(tǒng)治階級與民眾形成的“雅俗共賞”審美觀得到不斷融合,由于絲竹之樂無法保存,不同于前代宮廷鏗鏘有力的鐘石之樂,漢代民間歌舞樂的發(fā)展對中國歌舞、戲劇、小說的發(fā)展至關(guān)重要。從漢代“相和歌”發(fā)展到唐代相和大曲,文獻翔實地記載了漢代歌舞樂表現(xiàn)形式、表現(xiàn)內(nèi)容、審美特點,這與出土的樂舞俑、漢畫石、漢畫磚等音樂圖像互為驗證,這種有唱、有奏、有舞的歌舞樂表演,與百戲同臺演繹,表現(xiàn)了它的世俗性,可從相應(yīng)的排列組合中看出樂舞的表演形式。不同樂器的樂隊演奏又可以反映出多樂器重奏、齊奏等表演形式的可能,同時,漢畫呈現(xiàn)的多種器樂舞蹈合奏場景、樂器的演奏與舞蹈的配合,也體現(xiàn)了音樂與舞蹈的高度融合,反映了樂人高超的伴奏水平與舞者良好的音樂素養(yǎng)。再者,由于東漢時期巴蜀地區(qū)經(jīng)濟富足,聽俑反映了能夠欣賞樂舞的群眾音樂素養(yǎng)較好,這又客觀反映了宮廷樂舞與民間樂舞融合的世俗化表現(xiàn)。
結(jié)合前文,樂舞藝伎多為階級地位較低之人,有的是服務(wù)于莊園的歌舞藝伎,有的為失去自由的奴隸身份,有的為普通百姓,樂舞及百戲藝人多以娛人為謀生之手段,其社會身份低,如俳優(yōu)俑的侏儒丑俗形象,結(jié)合巴蜀地區(qū)的音樂文化氛圍,表演內(nèi)容多以民間歌舞為代表。不同于前代雅樂研習者有官方子弟,漢代樂舞傭體現(xiàn)的身份和樂舞本身的地位不相匹配;同時,不同的樂舞組合有相應(yīng)的祭祀之禮的要求等等,都對樂舞的表現(xiàn)形式、表演內(nèi)容產(chǎn)生遐想。我們知道,不同藝術(shù)形式的組合,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表演形式與內(nèi)容,而表演內(nèi)容也與群眾接受度、當?shù)氐奈幕尘啊肥值囊魳匪仞B(yǎng)有著很大的關(guān)系,因此漢代渝東北地區(qū)出土的樂舞俑反映的是喪葬文化背景下,宮廷歌舞與民間歌舞相互融合,渝東北地區(qū)漢代樂舞俑反映出樂舞的使用場合、排列組合規(guī)律、編制構(gòu)建、樂器形制、樂隊規(guī)模等,體現(xiàn)了樂舞不同的組合表演、豐富的音樂表演形式及地域性民間歌舞樂的興盛,對于構(gòu)建地域性音樂史料有重要的價值。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從樂手的音樂素養(yǎng)、當?shù)氐奈幕魳贩諊⒀莩龅膱龅亍⑷罕姷奈幕鹊确矫鎭碜鲆魳穼W方面的進一步分析,其音樂學研究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