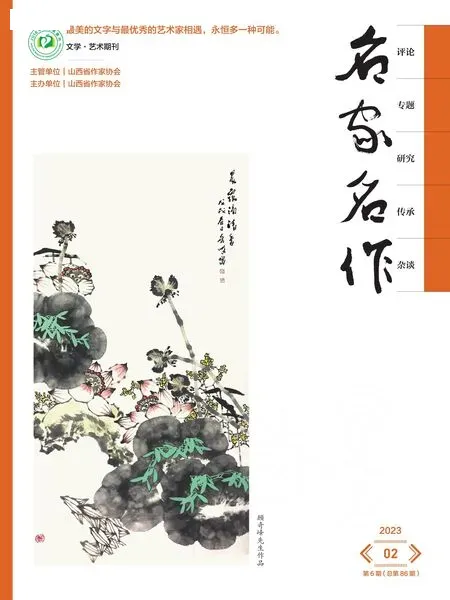“一帶一路”宣傳片《大道之行》中多模態(tài)隱喻的認(rèn)知構(gòu)建
張 瀅
一、理論基礎(chǔ)
自Lakoff & Johnson在其著作《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中提出概念隱喻理論以來,人們對(duì)隱喻的認(rèn)識(shí)由傳統(tǒng)的修辭工具擴(kuò)展到思維工具。概念隱喻體系中的隱喻被定義為一種 “跨概念域映射”的認(rèn)知過程[1],即在兩個(gè)不同的概念域中用一個(gè)概念(源域)理解另一個(gè)概念(目標(biāo)域)。認(rèn)知語言學(xué)家認(rèn)為,隱喻具有“語言、概念和交際功能”,蘊(yùn)含著隱喻使用者的價(jià)值立場(chǎng)和意識(shí)形態(tài),能夠“勸說、說服大眾”[2]。隱喻既然是一種重要的思維方式,就不應(yīng)僅限于語言這一種符號(hào)。20世紀(jì)末,在語篇研究多模態(tài)轉(zhuǎn)向的背景下,F(xiàn)orceville等人開始研究圖像、聲音、動(dòng)作等多種模態(tài)對(duì)隱喻的表征和構(gòu)建作用,提出了多模態(tài)隱喻理論。Forceville & Urios-Aparisi[3]認(rèn)為,除語言文字外, 圖像、音樂、手勢(shì)、味道等都可以參與隱喻意義的構(gòu)建,由此提出了多模態(tài)隱喻的概念,即源域與目標(biāo)域分別或主要由不同模態(tài)來呈現(xiàn)的隱喻現(xiàn)象。與語言隱喻相比, 多模態(tài)隱喻呈現(xiàn)出“動(dòng)態(tài)敘事性、鮮活性及‘具體是具體’映射”等特點(diǎn)[4]。
二、語料與分析方法
新華社于2017年5月17日發(fā)布的 “一帶一路” 宣傳片《大道之行》微視頻借由《國(guó)家相冊(cè)》中的老照片串聯(lián)起“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宗旨和成果,講述了中國(guó)的歷史亮點(diǎn)和成就。
《大道之行》總時(shí)長(zhǎng)為6分11秒(其中5分47秒至6分11秒為攝制團(tuán)隊(duì)的介紹,不在本文分析范圍),共120多個(gè)鏡頭。在結(jié)構(gòu)布局上,該片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0:00—1:40),伴隨著滴落在藍(lán)色湖面上的清脆水滴聲拉開序幕,并配合習(xí)近平總書記演講的原聲旁白和字幕,穿越回了中國(guó)古絲綢之路的場(chǎng)景;第二部分(1:41—2:21)通過一系列觸目驚心的畫面、動(dòng)態(tài)影像和旁白展現(xiàn)了當(dāng)今全球面臨的困境和危機(jī);第三部分(2:22—5:47),以父親帶著孩子尋找回家的路引發(fā)人們自然的聯(lián)想:世界怎么了?出路在哪里?進(jìn)而引出充滿中國(guó)智慧的解決方案——“一帶一路”倡議。
該視頻運(yùn)用了語言、字幕、動(dòng)態(tài)影像、圖片、音樂、手勢(shì)等多模態(tài)手法,其中動(dòng)態(tài)影像由電影拍攝和逼真場(chǎng)景混合而成,旁白收集了習(xí)近平總書記在多個(gè)國(guó)際會(huì)議上發(fā)表演講的原聲。這些多模態(tài)手法共同作為主題建構(gòu)和語篇連貫的手段,從而強(qiáng)化了受眾的認(rèn)知接受度,激發(fā)了情感共鳴。
本研究的文字模態(tài)由習(xí)近平總書記在國(guó)際會(huì)議上發(fā)表的七場(chǎng)演講的全文組成,并保存為單獨(dú)的文件,然后導(dǎo)入NVivo 12(質(zhì)性分析軟件) 中進(jìn)行進(jìn)一步的編碼和分析。視覺模態(tài)的視頻被“截圖”分割成 126 個(gè)分析單元——這是由停止和重啟相機(jī)帶來的“截圖”所構(gòu)成的“一個(gè)個(gè)連續(xù)的‘取景’”——該方法是電影研究中單位劃分的標(biāo)準(zhǔn)方式[5]。在對(duì)隱喻表達(dá)進(jìn)行編碼時(shí),演講與視頻中的隱喻表達(dá)識(shí)別方法有所不同。文字隱喻根據(jù)其含義進(jìn)行識(shí)別:如果所識(shí)別的短語/單詞的上下文含義在字典中具有更基本的含義,則將其標(biāo)記為隱喻表達(dá)[6]。視覺隱喻的識(shí)別遵循 Bounegru 和 Forceville (2011)[7]的視覺隱喻識(shí)別原則。在他們的描述中,如果一個(gè)視覺元素算作一種隱喻表達(dá),它應(yīng)該至少包含一個(gè)可以映射到目標(biāo)域的源域概念;此外,這種源域—目標(biāo)域的映射應(yīng)該是不可逆的。
三、《大道之行》中多模態(tài)隱喻的認(rèn)知構(gòu)建
在 NVivo 12的幫助下,我們確定了演講文本和視頻素材中的多模態(tài)隱喻。演講語料和視頻語料都運(yùn)用了多種源域。習(xí)總書記演講的語言文本包括248個(gè)語言隱喻表達(dá),而視頻語料包含67 個(gè)視覺隱喻(見表1)。
由此可以看出,使用人類隱喻和旅程隱喻是本研究“一帶一路”話語中更為凸顯的兩個(gè)隱喻,但演講文本和視頻文本之間存在一些細(xì)微差異。具體說來,演講文本語料更傾向于與人類相關(guān)的(105) 概念;視頻語料包含更多與旅程相關(guān)的隱喻(23),人類隱喻排在第二位。
(一)人類隱喻
在演講文本中,與人類相關(guān)的表達(dá)大都體現(xiàn)著 “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深層架構(gòu)。根據(jù)從人類到國(guó)家的概念映射,國(guó)家層面的發(fā)展計(jì)劃被解釋為個(gè)人的命運(yùn),國(guó)家間的關(guān)系通過人際活動(dòng)和人體的類比來表達(dá)。
在宣傳片中,中國(guó)工程師和非洲工程師共同研討工程方案的畫面隱喻中非的共建共享(見圖1);“中俄合作項(xiàng)目”的字幕和俄羅斯小伙打開一個(gè)個(gè)印有中國(guó)符號(hào)和中國(guó)元素的套娃畫面隱喻中國(guó)和俄羅斯睦鄰友好的國(guó)際關(guān)系(見圖2);馬來西亞小女孩在漂流瓶中看到了中遠(yuǎn)貨運(yùn)船只(見圖3);希臘小伙在中國(guó)援建的比雷埃夫斯港口垂釣(見圖4);英國(guó)男子在中歐班列上選到心儀的帽子(見圖5);斐濟(jì)人民在中國(guó)援建的納布瓦魯公路上歡歌熱舞的畫面(見圖6)和“一帶一路”的“朋友圈”正在擴(kuò)大的字幕,都是以“一帶一路”沿線國(guó)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普通民眾臉上洋溢著的滿意和幸福來隱喻中非、中俄、中馬、中希、中英、中斐等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建立起來的和諧和睦、唇齒相依的國(guó)際關(guān)系。“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是解決當(dāng)今世界危機(jī)、實(shí)現(xiàn)人類和平與發(fā)展的一劑良方,也向世界展現(xiàn)出一個(gè)有責(zé)任、有擔(dān)當(dāng)、與世界各國(guó)同呼吸共命運(yùn)的東方大國(guó)的形象。

圖1

圖2

圖3

圖4

圖5

圖6
(二)旅程隱喻
Zhang Xiaoyu[8]認(rèn)為,“一帶一路”一詞本身就是一種隱喻表達(dá)。顧名思義,“一帶一路”是連接亞洲、阿拉伯半島和南歐的古代商道范圍的地理名詞,其中“帶”指海上航線,“路”指陸路。而如今,該詞指的是在政策制定、基礎(chǔ)設(shè)施項(xiàng)目建設(shè)、自由貿(mào)易和沿線文化交流等領(lǐng)域的國(guó)家間的廣泛合作。基于“發(fā)展是旅程”這一概念隱喻,可以將“一帶一路”的內(nèi)涵理解為發(fā)展政策與物理路徑的類比,即“‘一帶一路’是旅程”。
在宣傳片《大道之行》中,旅程隱喻通過多種感官模態(tài)的表現(xiàn)形式,呈現(xiàn)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愿景和價(jià)值。首先,視頻的第一部分呈現(xiàn)了一片廣袤的沙漠和穿行其間的駱駝運(yùn)輸隊(duì)(見圖7),通過遠(yuǎn)景和中景的交替呈現(xiàn),將觀眾帶入了一個(gè)開闊的空間。同時(shí),背景音樂也采用了寬廣的樂章,呈現(xiàn)出開放、寬容、豁達(dá)的氛圍。這種多模態(tài)的表現(xiàn)形式,激發(fā)了觀眾對(duì)開放、自由、多元的向往和認(rèn)同,引發(fā)了對(duì)“大道”這個(gè)概念的探究和理解。

圖7
接下來,視頻中出現(xiàn)了“在海上航行的鄭和船隊(duì)”(見圖8)、“跋山涉水后挖掘出的古董陶器”(見圖9)等多個(gè)代表性的場(chǎng)景,這些場(chǎng)景通過視覺符號(hào)和語言符號(hào)的綜合運(yùn)用,向觀眾展示了中國(guó)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和歷史積淀。這些符號(hào)隱喻了“一帶一路”倡議的跨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的愿景,激發(fā)了觀眾對(duì)文化多樣性和歷史傳承的關(guān)注和認(rèn)同。

圖8

圖9
在《大道之行》的第三部分,視頻中還呈現(xiàn)了一幅“絲綢之路地圖”,通過動(dòng)態(tài)的線條和點(diǎn)陣呈現(xiàn),向觀眾展示了“一帶一路”的覆蓋范圍和聯(lián)通網(wǎng)絡(luò)(見圖10)。這種多模態(tài)的表現(xiàn)形式,既直觀又具有藝術(shù)性,激發(fā)了觀眾對(duì) “大道” 這個(gè)概念的想象和期待。另外,也與習(xí)近平總書記在達(dá)沃斯論壇中所說的遙相呼應(yīng)——“中國(guó)經(jīng)濟(jì)要發(fā)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場(chǎng)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遠(yuǎn)不敢到大海中去經(jīng)風(fēng)雨、見世面,總有一天會(huì)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國(guó)勇敢邁向了世界市場(chǎng)。在這個(gè)過程中,我們嗆過水,遇到過漩渦,遇到過風(fēng)浪,但我們?cè)谟斡局袑W(xué)會(huì)了游泳,這是正確的戰(zhàn)略抉擇。”在這里,旅程隱喻被具化成了一次航海旅行。對(duì)于中國(guó)來說,出海航行是一場(chǎng)生命的冒險(xiǎn),因?yàn)槿狈胶=?jīng)驗(yàn)(“漩渦”)和來自外部的致命危險(xiǎn)(“風(fēng)暴”)。盡管如此,中國(guó)還是有足夠的勇氣(“敢游”)去面對(duì)這些挑戰(zhàn),戰(zhàn)斗到底——它“學(xué)會(huì)了如何游泳”,成功地“看到了世界”。以在汪洋大海中游泳為例,發(fā)展被視為一次非常有挑戰(zhàn)甚至冒著生命危險(xiǎn)的旅行,而中國(guó)則是能夠克服這些風(fēng)險(xiǎn)的勇敢者。[8]

圖10
(三) 植物隱喻
在視頻的第一部分,湖面上的一滴小水滴由3D技術(shù)變成一朵美麗的花,接著一朵朵五顏六色的花在湖里競(jìng)相開放,最后盛開出一朵巨大的牡丹。在這段視頻中,一朵朵小花映射到“一帶一路”倡議的沿線國(guó)家這一目標(biāo)域。小花各異的顏色代表各國(guó)不同的民族與文化(見圖11)。小花是在水滴滋養(yǎng)下成長(zhǎng)起來的,水滴代表中國(guó)包容開發(fā)的態(tài)度,能與各國(guó)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中和諧共處。最終盛開的牡丹花與顏色各異的小花同在一湖面中開放(見圖12),既預(yù)示著“一帶一路”倡議會(huì)取得豐碩成果,也表明“一帶一路”倡議不是為了中國(guó)一枝獨(dú)秀,而是為了世界各國(guó)、各民族的百花齊放[9]。

圖11

圖12
四、結(jié)語
福柯( Foucault)認(rèn)為,話語即權(quán)力。因此,要想在國(guó)際上贏得 “一帶一路” 的話語權(quán)就離不開對(duì) “一帶一路” 知識(shí)的話語建構(gòu)[10]。在構(gòu)建過程中,人類社會(huì)共同理念和核心價(jià)值利益、價(jià)值定義權(quán)和解釋權(quán)都是需要高度關(guān)注的,從而得以全面提升中國(guó)的文化軟實(shí)力。“一帶一路”宣傳片《大道之行》中多模態(tài)隱喻的使用塑造了中國(guó)擔(dān)當(dāng)有為的大國(guó)形象,不失為促進(jìn)中國(guó)方案?jìng)鞑ァ②A得國(guó)際話語權(quán)的有效話語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