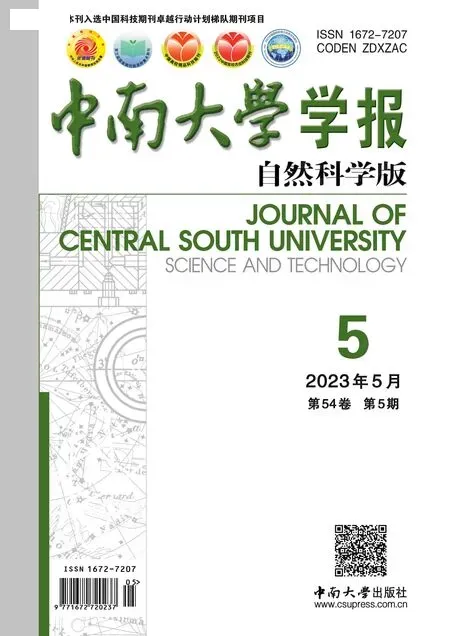三維水下黏質斜坡海床變形沖蝕特征試驗研究
竇玉喆,孫淼軍,國振,渠立標,朱佳慧,趙洪洋
(1. 浙江大學 建筑工程學院,浙江 杭州,310058;2. 中國電建集團華東勘測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311122;3. 海洋巖土工程勘察技術與裝備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311122;4. 浙江大學 海洋學院,浙江 舟山,316021)
隨著全球氣候變化,極端天氣頻發,海洋環境變得越來越惡劣。海床土體長期承受上部波浪荷載作用,在惡劣海況下容易出現過大變形,誘發海底滑坡,給海洋工程建設帶來不利影響,甚至引發重大海洋工程災害事故,例如1977 年,美國Texaco 公司的海底管道被海底滑坡破壞,造成原油泄漏,產生嚴重污染[1]。2006年,呂宋海峽發生地震,誘發了多起海底斜坡失穩,致使我國、泰國、馬來西亞、越南、韓國和新加坡的海底光纜多處斷裂,導致通訊中斷長達12 h,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2]。因此,研究波浪作用下海床土體變形失穩特性具備重要的工程價值與意義。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學者們針對波浪作用下海床動力響應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波浪誘發的孔隙水壓力響應、海床液化等。SUMER等[3]研究了粉質海床在推進波作用下的響應,例如底砂的輸送和海床液化。QI等[4]為了研究波流耦合對超孔隙壓力響應的影響,通過一系列大型水槽試驗,研究了波浪和水流共同作用下砂質海床的超孔隙水壓力響應。SASSA 等[5]通過離心試驗研究了波浪荷載作用下海床的液化機理。MIYAMOTO 等[6]結合離心試驗結果,研究了推進波作用下可液化土層的變形破壞機理。在理論與數值方面,SUMER 等[7-8]基于Biot 的孔隙彈性理論,在各種假設下建立了波浪-海床相互作用的多孔模型。HSU等[9]提出了有限深海床的Biot方程的解析解,該解析解可以收斂于YAMAMOTO 等[10]和MADSEN[11]提出的無限深海床的解。SASSA等[12]對砂質海床的波浪液化進行了數值研究,并與離心機試驗結果進行了比較[5]。同時,人們針對波浪-海床-結構相互作用也開展了許多研究,包括波浪與管線[13-14]以及波浪與樁基[15-18]的相互作用研究。但上述研究均針對砂質海床且忽略了三維特征,對黏質海床的響應特性研究較少,波浪作用下黏質海床的響應特征尚不明確。黏質海床廣泛存在于真實的海洋環境中,對其在波浪作用下的動力響應特征的研究同樣非常重要。CHEN等[19]基于循環三軸試驗,討論了杭州灣黏土中的孔隙壓力發展和耗散特征;楊彥豪等[20]通過空心圓柱扭剪試驗研究了波浪荷載作用下軟黏土的動力特性。YAMANISHI等[21]研究了試驗水槽和潮汐河流中破碎波引起的黏質沉積物沖刷過程。
目前,對于波浪作用下黏質海床的孔壓響應以及沖蝕失穩特征的研究較少,且已有的研究大多為單元試驗或基于二維條件的模型試驗,尚未見波浪作用下三維黏質海床的響應特征研究報道。實際上,近海區域水底一般都不是水平或者均勻坡度的,大多表現為“內凹”或“外凸”。而且,波浪在淺水化過程中對地形變化(包括坡度以及地形形態)較為敏感。DOU等[22]發現在相同波浪參數下,改變海床坡度會導致不同的波浪淺水化特征、破碎類型以及黏質斜坡海床破壞模式。三維海床地形具有更加復雜的波浪場特征,其動力響應特征與二維情況下的不同,從而導致海床土體失穩破壞特征不同。對二維情況下海床的研究結果無法反映真實海洋環境中波浪與三維海底地形的相互作用特征,因此,研究波浪作用下的三維水下黏質斜坡海床變形沖蝕特征具有重要意義。
相比于“外凸”地形,波浪在“內凹”地形傳播時波浪有向內凹側匯聚的趨勢,導致波浪在地形內測、坡肩位置和地形較復雜位置表現出更強的非線性。因此,本文針對“內凹”型海床地形開展試驗研究,選取舟山某海域作為研究原型,結合現場海底地形,在大型港池中開展一系列試驗,研究三維波浪場演化特征以及三維黏質斜坡在波浪作用下的孔壓響應特征和沖蝕失穩特征,研究成果可為工程設計提供重要參考及依據。
1 試驗設計
1.1 試驗設備
本試驗在浙江大學海洋學院的大型波流港池中完成,其長為70 m,寬為40 m,深為1.5 m。波流港池可實現潮流、潮位、波浪及泥沙等多因子同步耦合模擬,可采用L 型造波機制造三維波浪。港池工作水深范圍為0.2~1.0 m;波周期變化范圍為0.3~5.0 s;波高變化范圍為0.03~0.30 m。
試驗設備還包括波高儀、孔壓傳感器(PPT)和三維地形掃描儀等,其中,波高儀型號為TCS-1,數據采集采用珠江水利科學研究院研制的高速數據采集器。微型孔隙水壓力傳感器的量程為20 kPa,表壓綜合精度為0.2%。試驗前,對傳感器進行飽和、標定,確保傳感器處于正常工作狀態。地形掃描采用徠卡ScanStation P30/P40新一代超高速三維激光掃描儀。
1.2 現場條件
試驗模擬區域位于舟山某海域,呈“內凹”矩形,長約3.5 km,寬約1.6 km,整個場區內海底地形變化較大,水深在0~80 m 之間,基于現場多波束地形數據建立的等水深線圖如圖1所示。場區表層和底層的平均流速分別為1.08 m/s和0.78 m/s;表層和底層的最大流速分別為2 m/s 和1.25 m/s。舟山海域為大浪區,平均波高為0.4~1.1 m,最大波高出現在8 月,臺風所致波高最大可達11.5 m。因地形復雜,使波浪的運動受地形制約,各處的波浪分布特征不盡相同。海床底質為淤泥質黏土,土體參數見表1。

圖1 等水深線圖Fig. 1 Bathymetric contour of site

表1 土體參數Table 1 Soil properties
1.3 相似原理
物理模型水槽試驗中自由表面重力波的恢復力為重力,而以重力為主要作用力的流動試驗參數通常采用弗勞德數Fr相似準則表征。弗勞德數定義如下:
式中,v為流速,m/s;Lc為特征長度,m;g為重力加速度,m/s2。
根據現場地形、波浪資料以及實驗室設備條件,采用1∶100幾何比例設計港池試驗參數,試驗比尺詳見表2。

表2 試驗比尺設置Table 2 Experimental scale set up
1.4 三維海底地形制作
根據目標場區條件,縮尺后的三維地形的長×寬×坡頂高度為38.8 m×12.0 m×0.9 m。試驗的三維海底地形采用磚混結構。首先,沿等高線建造磚混框架,然后,在各等高線之間填充廢渣,最后,用水泥沿等高線封閉三維地形,盡量保證水體主體與地形之間不發生交換。三維地形在港池中的平面布置及具體尺寸如圖2所示。根據現場波浪條件和地形特點確定動床區域位置,如圖2中黑色陰影區(長×寬為5.5 m×5.5 m)所示。為預留動床區域,對三維地形施工時,在動床區域的2個側面以及后面預先按照地形高程設計制作擋墻,以防止土樣四處流動。同時,為減少土樣用量,在動床區域底部砌筑1個坡頂高度為0.4 m的剛性斜坡體,因此,動床區域坡頂處黏土層厚度為0.5 m。

圖2 試驗平面布置圖(陰影部分代表動床區域)Fig. 2 Test layout plan (shaded part represents live bed area)
1.5 試驗用土及試樣制備
試驗海床由人工制備的結構性淤泥質黏土制成,每次試驗需要約10.19 t土樣。在制備過程中,首先將土樣倒入真空攪拌器中,加水至土樣的含水率為液限的2 倍。然后,以30~40 r/min 的轉速在真空環境下連續攪拌3 h。為了使土樣具有一定的結構性,需要加入土顆粒質量的2%的硅酸鹽水泥(#525)[23-24]。將土樣、硅酸鹽水泥(#525)和水的混合物在真空條件下再攪拌1 h。最后,將制備好的結構性軟黏土填筑至三維地形的動床區域,在水下進行自重固結至強度約1 kPa。
1.6 試驗工況與傳感器布置
本試驗僅使用長邊造波板造波,三維海床地形試驗工況如表3所示,其中,D為坡腳處的初始水深,H為入射波波高,T為入射波周期;g為重力加速度,ζ為波陡,ζ=H/L,L為入射波波長。根據LEMéHAUTé[25]提出的“波浪理論的適用范圍”圖,本試驗入射波主要位于Stokes二階和三階波浪理論區,如圖3所示。為監測波浪場和海床孔壓響應,在港池中布置波高儀并在動床區域沿A-A和B-B斷面布置孔壓傳感器,具體布置方式如圖4所示。

表3 三維海床地形試驗工況Table 3 Test conditions of three-dimensional clayey slope seabed

圖3 波浪理論的適用范圍[25]Fig. 3 Range of suitability of various wave theories[25]

圖4 傳感器和波高儀布置示意圖Fig. 4 Layout diagrams of transducers and wave height meters
1.7 試驗步驟
本實驗采用從小波高到大波高依次造波的方式進行試驗,即首先進行H為0.069 m的波高實驗,待水面穩定后再依次進行H為0.115 m和0.240 m的試驗。在完成H=0.240 m 試驗后進行三維地形掃描。具體步驟如下:1) 根據比例尺在港池中建造三維海底地形;2) 清洗港池;3) 在指定位置安裝波高儀;4) 確定試驗波高;5) 拆除動床區域地形;6) 飽和并標定孔壓傳感器;7) 在指定位置安裝孔壓傳感器;8) 制備結構性軟黏土;9) 在動床區域內填筑人工制備的軟黏土;10) 采用三維地形掃描儀掃描波浪作用前的海床地形;11) 港池注水至完全淹沒三維地形,保證海床在水下自重固結至約1 kPa;12) 注水至目標水位,打開數據采集系統,進行造波;13) 停止造波,港池排水,進行三維地形掃描。傳感器布置示意圖見圖4。
2 試驗結果及分析
2.1 波浪場特征
圖5 所示為波浪在傳播過程中的波高沿程變化,其中,x表示波高儀到原點的距離。在A-A斷面和B-B斷面分別選取距離斜坡坡腳最近的5號和11 號波高儀的位置作為坐標原點,三維地形一側為正。由圖5可知:海底三維地形的存在會導致波浪場具有一定的三維特征,不同斷面的波浪特征并不相同。在A-A斷面,當波高較小時,波浪在爬坡過程中出現較明顯的淺水化現象,波高逐漸增大;當波高H=0.240 m 時,波浪發生明顯破碎,導致波高降低。而B-B斷面地形較復雜,波浪受地形和反射波影響較大,導致波浪爬坡過程中并未呈現出規則的淺水化特征,在13 號波高儀處波高明顯降低。

圖5 波浪波高沿程變化Fig. 5 Wave height variation of wave along the path
各階諧波的幅值隨空間變化規律如圖6 所示,其中,|An|為n階諧波振幅(n=1,2,3),Hi/2 為波幅,Hi分別取兩斷面距離造波板最近的測點(3號和9號波高儀)的波高平均值。從圖6可見:與關于水下防波堤或障礙物上波浪傳播的結果類似[26-27],高階諧波分量隨著水深的減小而增大,特別是在靠近坡頂的區域,這種現象更明顯,這說明波能從主頻向高階轉移。在波高H=0.240 m時,三維地形坡頂處的14號波高儀響應出現5階幅值,如圖7所示,由此可知波浪爬坡過程中非線性逐漸增強。

圖6 不同入射波下波高的各階諧波振幅的空間變化Fig. 6 Spatial variation of each order harmonic amplitude of wave height under different incident waves

圖7 波高H=0.240 m時的頻譜特征Fig. 7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of wave height H=0.240 m
2.2 斜坡海床孔壓響應
波浪與黏性斜坡海床的相互作用非常復雜,是沖蝕、孔壓變化以及失穩三者相互耦合直至達到穩定平衡狀態的過程。以往研究發現,在波浪荷載作用下,海床孔隙水壓力按增長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2類,即與瞬時體積應變有關的振蕩孔壓和由永久壓密趨勢引起的累積孔壓,前者由振蕩波壓力直接產生,在波浪作用過程中沒有累積;后者會引起海床土體內部有效應力逐步減小,對于砂土海床甚至會發生液化現象[28]。
對于波高H=0.069 m 和0.115 m 的情況,海床內部孔壓有一定累積,但累積并不明顯,因此,本文僅給出了波高H=0.069 m 和0.115 m 時黏質斜坡海床不同位置的振蕩孔壓幅值隨深度變化規律,如圖8所示,其中,z為孔壓傳感器埋深,h為孔壓傳感器斷面處的土層厚度。由圖8可知,由于波浪淺水化以及三維化效應,導致不同斷面處振蕩孔壓幅值沿深度變化規律不同。

圖8 振蕩孔壓幅值沿深度變化規律Fig. 8 Variation of amplitude of oscillatory pore water pressure with depth
當波高H=0.240 m時,超孔壓累積明顯,采用信號分析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提取2種孔壓信號的特征。本文選擇Daubechies小波對波浪荷載作用下黏質海床超靜孔隙水壓力響應信號[29]進行分解,進而分離累積孔壓分量和振蕩孔壓分量。圖9所示為通過傅里葉變換得到的孔壓傳感器PPT-1 的孔壓響應頻譜圖。由圖9可知:除了與波浪荷載相同的特征頻率外,其主要的能量集中在低頻區。

圖9 孔壓響應頻譜圖Fig. 9 Pore pressure response spectrum
圖10 所示為PPT-1 的孔壓響應信號通過MATLAB 得到的10 層小波變換分解圖,其中,S為原始信號,a10為分解后第10層的低頻分量,a10反映了累積孔壓分量(低頻區);dj為第j層的高頻信號,d6反映了振蕩孔壓分量(高頻區)。由圖10 可知:通過小波變換可較好地分離累積孔壓分量和振蕩孔壓分量。

圖10 孔壓傳感器PPT-1的孔壓響應信號的小波變換分解圖Fig. 10 Wavelet decomposition diagrams of pore pressure response signal of PPT-1
現對波高H=0.240 m時,A-A和B-B斷面不同位置的孔壓響應信號進行小波變換分析。
圖11 所示為波高H=0.240 m 時斜坡土體不同位置處的超孔壓累積情況。由圖11 可知,在波浪作用的整個過程中,土體表層孔隙水壓力基本沒有累積;在波浪作用初期,A-A斷面處斜坡海床內部的超靜孔隙水壓力會出現累積現象;在波浪作用過程中,3 號和4 號孔壓傳感器的響應表現為超靜孔隙水壓力呈不斷增長的趨勢,直至加載結束;而6和7號孔壓傳感器響應則不同,波浪作用初期表現為超孔壓累積,隨著波浪持續作用,黏質斜坡海床在該位置處受波浪影響較大,海床土體發生沖蝕失穩,導致超孔壓逐漸消散,因此,超孔壓總體表現為先累積后消散。從圖11(c)可見,由于海床土體的沖蝕失穩,7號孔壓傳感器原本要累積的超孔壓在t=500 s 時強制消散,并且隨著波浪的持續作用,海床超孔壓逐漸消散。

圖11 累積超孔壓時程曲線Fig. 11 Time history curves of accumulated excess pore pressure
B-B斷面處土體內部的超孔壓同樣由于波浪的循環作用產生累積,但相比于A-A斷面消散較明顯。與較深處(z=-0.30 m)相比,較淺處(z=-0.15 m)孔壓比消散得早且消散較快。斜坡海床A-A和B-B斷面的超孔壓表現出不同的響應特征,表明由于三維地形的影響,波浪場以及斜坡海床的破壞特征均具有一定的三維特征。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波浪場特征、海床內部孔壓響應特征以及海床土體沖蝕失穩特征三者相互耦合、相互影響。
2.3 三維地形破壞特征
當波高H=0.240 m時,波浪在坡頂處破碎,波壓力在破波區達到最大。在波浪不斷地對動床土體拍擊、回卷,沖蝕作用明顯。同時,斜坡土體在波浪循環荷載作用下,孔壓增大,有效應力降低,最終導致斜坡發生破壞。斜坡最終的沖蝕失穩形態如圖12(a)所示,波浪作用前后斜坡海床地形如圖12(b)和(c)所示。由圖12(a)可知:斜坡坡頂位置首先發生沖蝕,然后由坡頂向坡腳方向發生淺層破壞,在靠近坡腳處出現明顯的黏土碎屑狀堆積;破壞范圍集中在動床中間區域,由于地形和波浪的三維效應,海床并未沿著完全平行于動床兩側邊界方向破壞,而是斜向潮汐通道。

圖12 斜坡海床三維地形圖Fig. 12 Three-dimensional topography of sloping seabed
為了更清晰地觀察斜坡沖蝕失穩情況,將地形右上角定義為參考原點,分別取距參考原點水平距離1.38、2.75 和4.12 m處的二維剖面,3個剖面分別命名為剖面I-I、Ⅱ-Ⅱ和Ⅲ-Ⅲ。其中,距參考原點1.38 m 和4.12 m 處為地形布置孔壓傳感器的A-A和B-B斷面;距離參考原點2.75 m 處的剖面Ⅱ-Ⅱ為動床區域的中間剖面,如圖12(b)所示。3個斷面的二維剖面圖如圖13 所示,其中,紅色虛線表示該剖面處原始地形的形態。由圖13可知:3個斷面的破壞形態并不相同,剖面I-I和剖面Ⅱ-Ⅱ被明顯沖蝕破壞,且中間斷面Ⅱ-Ⅱ處斜坡土體變形最為顯著,距離坡頂2 m范圍內的土體由于波浪的沖蝕作用產生了明顯的凹陷,而距離坡頂2.5~3.5 m處的黏土碎屑產生了明顯的堆積。

圖13 斜坡海床二維剖面圖Fig. 13 Sloping seabed of two-dimensional profiles
2.4 三維地形與二維地形的破壞特征對比
為了研究三維地形對海床的影響,同時開展波浪海床相互作用的二維水槽試驗,水槽試驗的土體與港池試驗的相同,試驗工況如表4所示。圖14 所示為二維水槽試驗中不同坡度黏質斜坡的破壞模式。由圖14 可見,黏質岸坡與潛坡的破壞模式并不相同,海床坡度對海床的破壞模式影響較大。對于黏質岸坡,波浪在坡上破碎,海床出現沖蝕與塊體滑動相互耦合的破壞特征;對于黏質潛坡,海床發生自坡頂向坡腳的淺層破壞。

表4 二維水槽試驗工況Table 4 Flume test conditions

圖14 二維水槽試驗黏質斜坡破壞模式Fig. 14 Failure mode of clayey slope in two-dimensional flume test
通過與二維試驗結果比較可以發現,三維水下黏質斜坡的破壞形態與二維水下斜坡的破壞形態并不相同,受三維地形和三維波浪場的影響,海床破壞形態具有一定的三維特征,其沖蝕破壞方向并未在該二維剖面內,而是朝向動床區域左下方的出口(系現場地形的潮汐通道),見三維地形掃測圖(圖12(c))的箭頭方向。綜上所述,動床區域發生的破壞是由波壓力和波浪破碎的沖蝕效果共同作用導致的,而海床最終的破壞特征對水下三維地形(包括坡度和三維形態等)較為敏感。
3 結論
1) 波浪在三維斜坡地形上傳播時會表現出與二維地形類似的、較明顯的淺水化現象。但由于三維地形的存在導致波浪場具有一定的三維特征,具體表現為海床的不同斷面表現出不同的波浪特征,在坡度較大、地形較復雜處,波浪的高階分量越明顯,非線性也越強。
2) 波浪與黏性斜坡海床的相互作用非常復雜,是沖蝕、孔壓變化以及失穩三者相互耦合直至達到穩定平衡的過程。
3) 斜坡海床的孔壓響應特征與其沖蝕失穩特征密切相關,高度耦合。三維地形的存在導致海床不同斷面處的孔壓響應不同,具有較為明顯的三維特征。當波高較小時,海床的超孔壓沒有明顯的累積,大多表現為振蕩孔壓;當波高逐漸增大時,海床內部超孔壓在波浪作用初期產生明顯累積,土體有效應力降低,隨著波浪持續作用,海床土體發生破壞,海床沖蝕失穩特征和程度不同會引起超孔壓不同程度地消散。
4) 海床最終的破壞特征對水下三維地形(包括坡度和三維形態等)較為敏感。由于三維地形的存在和波浪的三維化效應,斜坡破壞具有明顯三維特征,其并未沿著完全平行于動床兩側邊界方向破壞,而是斜向潮汐通道。對于黏質水下斜坡,首先在斜坡坡頂發生沖蝕破壞,然后由坡頂向坡腳方向發生淺層破壞,在靠近坡腳處出現明顯的黏土碎屑狀堆積。海床的破壞特征與波浪條件、三維地形以及土體性質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