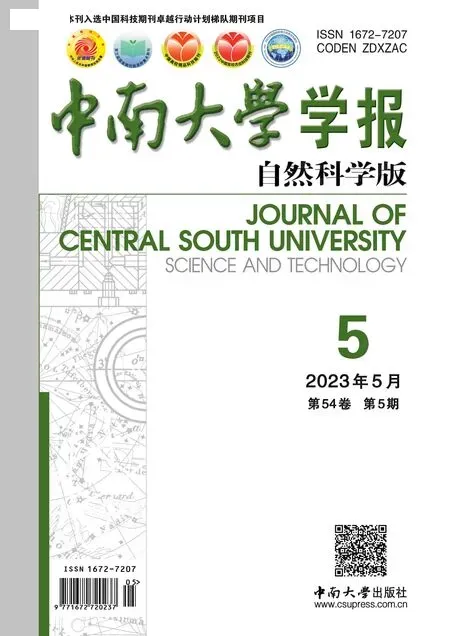既有高速鐵路提速條件下低頻晃車特征及影響因素研究
高雅,魏子龍,楊飛,吳軍,李紅艷,李威霖
(1. 中國鐵道科學研究院 基礎設施檢測研究所,北京,100081;2. 中國鐵路成都局集團有限公司 工務處,四川 成都,610033;3. 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 鐵路基礎設施檢測中心,北京,100081;4. 北京鐵科英邁技術有限公司,北京,100081)
為了更好地滿足出行需求,提高鐵路運營效率,高速鐵路不斷朝著高速化的方向發展[1-3]。部分高速鐵路列車提速運行后,在某些直線區段出現車體異常晃動現象,對列車運行的平穩性、舒適性以及運營維護的經濟性都產生影響[4-5]。
既有研究表明,車體大多在振動頻率為1~2 Hz 時出現異常晃動,這種低頻振動容易造成乘客乘坐舒適性下降,加速車輛結構部件的疲勞損傷,甚至會導致列車脫軌事故[6-8]。針對這一問題,國內外學者通過理論分析、數值仿真與試驗測試等手段開展了一系列研究。SUN等[9]結合試驗和數值仿真研究了低等效錐度導致的電力機車直線區段車體異常低頻晃動問題,并對車輛懸掛參數進行了優化。WEI 等[10]采用有限元和多體動力學耦合的方法建立了高速鐵路剛柔耦合車輛模型,研究了輪軌型面磨耗對轉向架蛇形失穩和車體異常晃動的影響。HUANG等[11]通過數值仿真研究了車輛懸掛參數和輪軌廓形對車體蛇形運動穩定性的影響,并進一步結合試驗測試分析了抗蛇形減振器對車輛運行穩定性的影響。葉一鳴等[12]研究了直線區段鋼軌交替不均勻側磨和軌道狀態不良對機車晃車的影響。歷鑫波等[13]分析了晃車時車輛振動響應的時頻特征,結合模態分析研究了轉向架蛇形失穩對晃車的影響。付政波[14]對晃車區段的輪軌匹配關系進行了分析,結合仿真分析發現鋼軌打磨后出現輪軌匹配不良,繼而導致車體低頻晃車。張志超等[15]在對直線晃車區段歷史測試數據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結合仿真分析研究了等效錐度和抗蛇形減振器對動力車晃車的影響。俞喆等[16]研究了鋼軌工作邊偏差、左右股鋼軌廓形不對稱以及車輪磨耗對動車組晃車的影響。
目前對于晃車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從輪軌匹配關系[17-18]、車輛懸掛系統參數等方面開展,隨著車輛運行速度的提高,輪軌之間的動力相互作用加劇,車輛對自身參數變化以及外部激擾會更加敏感[19-20]。因此,有必要對提速列車直線區段的晃車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以適應當前高速鐵路提速、達速的發展要求。
本文以某高速鐵路提速運營后直線區段出現的車體橫向低頻晃動現象為研究背景,對晃車問題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在對提速前、后動檢數據,輪軌接觸特性,乘坐舒適性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建立車輛-有砟軌道動力相互作用模型,綜合考慮車輛運行速度、輪軌廓形、軌道平順狀態對車輛系統動力響應的影響,以期為提速高速鐵路線路的養護維修提供參考。
1 提速列車晃車特征分析
1.1 測試數據分析
某有砟高速鐵路設計速度為250 km/h,主要運行CRH2型動車組。近期,線路運營速度由200 km/h提速至250 km/h 后,部分直線區段出現了異常晃車現象,嚴重情況下會伴隨橫向加速度超限(I級限值0.06g)。圖1(a)所示為列車提速后車體加速度增加量累計分布圖像,由圖1(a)可以看出:列車運行速度由200 km/h 提升至250 km/h 后,車體橫向加速度明顯增加,50%分位數約為0.007g,90%分位數約為0.020g,95%分位數約為0.030g,車體垂向加速度變化較小。圖1(b)和圖1(c)所示分別為當列車運行速度為200 km/h 和250 km/h 時,直線線路中未晃車區段與晃車區段的車體加速度檢測數據。由圖1(b)和圖1(c)可以看出:在線路提速后,車體橫向加速度的幅值顯著增加,且其在晃車區段出現明顯周期性波動特征。其中,提速后晃車區段中車體橫向加速度振幅達到0.06g,較提速前增加了1倍,較未晃車區段增加了2倍。晃車區段和未晃車區段的車體垂向加速度時程曲線差異較小。

圖1 實測車體加速度Fig. 1 Measured car body acceleration
圖1(d)和圖1(e)所示為車體橫向加速度頻程,由圖1(d)和圖1(e)可以看出:列車運行速度為250 km/h時的車體橫向加速度譜峰明顯比運行速度為200 km/h 時的大,同時晃車區段車體橫向加速度譜峰遠比未晃車區段的大。其中,當列車運行速度為250 km/h 時,晃車區段車體橫向加速度振動頻率為1.37 Hz,未晃車區段車體橫向加速度振動頻率為1.11 Hz,當列車運行速度為200 km/h時,晃車區段車體橫向加速度振動頻率為1.07 Hz,未晃車區段車體橫向加速度振動頻率為2.21 Hz。圖1(f)和圖1(g)所示為車體垂向加速度頻程,由圖1(f)和圖1(g)可以看出:不同運行速度下未晃車區段的車體垂向振動情況差異不明顯,晃車區段在運行速度為250 km/h 時的車體垂向加速度譜峰明顯比運行速度為200 km/h 的情況大,且振動頻率發生了變化。
1.2 乘坐舒適性分析
采用UIC513 舒適性評價方法[21]來對列車的乘坐舒適性進行評價。通過對測試加速度數據進行規范化處理,按照ISO-2631 標準中規定的計權曲線對振動信號進行加權濾波,以此來反映人體對不同振動頻率的敏感程度,從而實現對列車運行品質的量化評估。UIC513 舒適性評價方法是將5 min內的縱向(x)、橫向(y)、垂向(z)測試數據分別以5 s為一個采集時段,分成60段進行加權均方值計算,再將3 個方向上的加權值進行置信度處理,最后通過幾何相加計算得到舒適性指標Nmv為
式中:a為加速度;x,y和z為測量方向;95表示并按置信度95%進行概率處理;wb和wd為ISO-2631標準中規定的隨頻率變化的權重系數,如圖2(a)所示。由圖2(a)可以看出:在橫向振動方面,人體對2 Hz 以下的振動較為敏感,在垂向振動方面,人體對4~10 Hz的振動較為敏感。

圖2 乘坐舒適性分析Fig. 2 Ride comfort analysis
UIC513 將評價結果分為5 級,高速鐵路列車舒適性指標不應超過2[22]。圖2(b)所示為運行速度為200 km/h 和250 km/h 時晃車區段和未晃車區段的舒適性指標的計算結果,其中橫向和垂向分別代表單獨考慮橫向和垂向振動加速度時乘坐舒適性指標的計算結果。由圖2(b)可以看出:當列車運行速度為200 km/h 時,晃車區段和未晃車區段的乘坐舒適性良好,不同區段的舒適性指標相差不大。與運行速度為200 km/h 時相比,列車運行速度為250 km/h 時未晃車區段的舒適性指標明顯增加,但Nmv、橫向和垂向舒適性指標均較小,橫向和垂向舒適性指標相差較小;晃車區段乘坐舒適性明顯下降,舒適性指標接近超限,特別是橫向舒適性指標急劇增大,可達垂向舒適性指標的2倍。由此可見,列車提速后晃車區段的車體橫向周期性低頻晃動導致乘坐舒適性明顯下降。
1.3 輪軌廓形分析
對晃車區段里程K1551+670~K1551+735 的鋼軌廓形每間隔10 m進行測試,7組測試結果如圖3所示。由圖3可以看出:實測鋼軌廓形磨耗主要出現在軌頂和軌距角處,右股鋼軌廓形軌頂磨耗比左股鋼軌廓形軌頂磨耗大,左、右股鋼軌廓形不對稱。圖4 所示為鋼軌廓形測試現場圖片,由圖4可以看出:左、右股鋼軌光帶寬度不一致,一股鋼軌光帶居中,光帶寬度較窄,另一股鋼軌光帶偏向軌距角處,光帶寬度較寬。

圖3 鋼軌型面Fig. 3 Rail profiles

圖4 鋼軌測試現場照片Fig. 4 Rail measurement scene
在車輪廓形方面,隨機選取該線路CRH2A 型
運營動車組的車輪廓形進行測試,并將均值處理的測試車輪廓形作為實測車輪廓形進行后續分析,圖5 所示為均值處理后的結果。由圖5 可以看出:車輪型面磨耗主要位于輪緣處以及踏面中部,輪緣厚度明顯減小,左、右車輪廓形磨耗差異不明顯。

圖5 車輪型面Fig. 5 Wheel profiles
1.4 輪軌匹配分析
為進一步掌握晃車區段的輪軌接觸特性,對1.3 節中7 組實測輪軌廓形以及CHN60&LMA 廓形匹配時的等效錐度進行對比,結果如圖6所示。由圖6可知:與CHN60&LMA廓形相比,實測輪軌廓形在輪對橫移量為3 mm時的等效錐度較小,在輪對橫移量大于3 mm時較大,輪對橫移量大于3 mm時實測輪軌廓形等效錐度增幅要比輪對橫移量小于3 mm時的等效錐度降幅大。

圖6 等效錐度對比Fig. 6 Comparison of equivalent conicity
圖7 和圖8 所示分別為里程K1551+715 處實測輪軌廓形以及CHN60&LMA 廓形匹配時的輪軌接觸點分布圖像,其中輪對橫移量為±10 mm。由圖7 和圖8 可以看出:實測車輪廓形上的接觸點分布更加集中,尤其是在輪對橫移量小于4 mm時,實測鋼軌廓形上的接觸點偏向軌頂中心。同時實測輪軌廓形匹配時接觸點分布不均勻,且沒有出現輪緣接觸。

圖7 K1551+715處實測輪軌廓形匹配圖像Fig. 7 Images of measured wheel rail profiles matching at K1551+715

圖8 CHN60&LMA廓形匹配圖像Fig. 8 Images of CHN60&LMA profiles matching
2 車輛-有砟軌道動力相互作用模型
本文的車輛-有砟軌道動力相互作用模型由3部分組成:車輛模型、有砟軌道模型以及體現車輛和軌道模型之間動力相互作用的輪軌滾動接觸模型,如圖9(a)所示。

圖9 車輛-有砟軌道動力相互作用模型Fig. 9 Vehicle-ballasted track dynamic interaction model
2.1 車輛模型
采用多剛體動力學理論建立車輛模型,模型由1 個車體、2 個轉向架、4 個輪對組成,每個構件均考慮橫移、沉浮、側滾、點頭、搖頭自由度,整車共計35 個自由度,如圖9(b)所示。車體與轉向架之間和轉向架與輪軌之間通過懸掛彈簧和阻尼進行連接。沿車輛運行方向分別為前轉向架和后轉向架,前轉向架的前、后輪分別為一位輪對和二位輪對,后轉向架的前、后輪分別為三位輪對和四位輪對。
式中:M、K和C分別代表車輛各部件質量、剛度和阻尼矩陣;下標c、t 和w 分別代表車體、轉向架和輪對;u、u?和u分別為位移、速度和加速度向量;F為各部件受到輪軌力和自身重力的合力。
2.2 軌道模型
軌道模型包含鋼軌、軌枕和道床,如圖9(c)所示。鋼軌簡化為Euler 梁進行建模,考慮橫向、垂向和扭轉運動,運動方程見文獻[23]。軌枕簡化為剛體,考慮橫向、垂向和扭轉運動。道床簡化為等效質量塊,考慮垂向運動,相鄰質量塊之間通過剪切力相互作用[24-26]。扣件簡化為彈簧、阻尼系統,剪切力通過剪切彈簧進行表達。定義沿車輛運行方向左側為左股鋼軌,右側為右股鋼軌。單根軌枕的運動方程如下。
垂向運動:
橫向運動:
扭轉運動:
式中:Ms和Is分別為軌枕質量和轉動慣量;FyL和FzL為軌枕與左股鋼軌之間的扣件力;FyR和FzR為軌枕與右股鋼軌之間的扣件力;FzbL和FzbR分別為左、右道床塊的支承力;Zs、Ys和?s分別為軌枕垂向、橫向和扭轉運動向量。
一組道床塊的運動方程為:
式中:FzrL、FzfL、FzrR、FzfR和FzLR為左、右道床塊受到的剪切力;FzfL和FzfR分別為左、右道床塊受到的路基支承力;ZbL和ZbL分別為左、右道床塊運動向量。
2.3 輪軌滾動接觸模型
車輛與軌道是通過車輪與鋼軌之間的滾動接觸進行相互作用的,滾動接觸可以分為幾何約束和動力學約束,其中幾何約束通過輪軌接觸幾何體現,動力學約束通過輪軌力體現。其中輪軌法向力采用Hertz線性接觸理論進行求解,輪軌切向力采用Shen-Hedrick-Elkins理論進行求解。由此得到車輛-軌道耦合方程,并采用新型兩步數值積分方法對耦合方程進行求解[27]。
3 模型驗證
本文以車體加速度作為評判指標,通過與實測車體加速度對比,對仿真模型計算結果進行驗證。在仿真計算中,車輛模型采用CRH2型車參數,軌道模型參數見表1。車輛運行速度為250 km/h,軌道不平順為對應測試區段實測軌道不平順。圖10所示為車體橫向加速度時程及頻程的測試結果和仿真計算結果。由圖10 可知:仿真計算得到的車體橫向加速度在時程和頻程均與實測數據基本吻合,由此驗證了本文仿真模型計算結果的準確性。

表1 軌道模型參數Table 1 Track model parameters

圖10 車體加速度結果對比Fig. 10 Comparisons results of carbody acceleration
4 提速列車晃車影響因素分析
為了研究提速列車車體橫向低頻晃動的影響因素,采用第3節中的車軌模型參數,以運行速度為200 km/h 和250 km/h 為例,分析采用實測輪軌廓形、CHN60&LMA 廓形以及軌道不平順對車輛系統動力響應的影響。
4.1 輪軌廓形對列車晃車的影響分析
為研究輪軌廓形對列車晃車的影響,不施加軌道不平順,分析不同運行速度下采用實測輪軌廓形匹配以及CHN60 & LMA廓形匹配時的車輛系統動力響應。
圖11 所示分別為車輛運行速度為200 km/h 和250 km/h,采用實測輪軌廓形匹配和CHN60&LMA 廓形匹配時的車體橫向加速度和輪對橫向位移圖像,圖中WR&WW 表示采用實測輪軌廓形,CHN60&LMA 表示采用CHN60 與LMA 廓形,wto表示不施加軌道不平順。由圖11 可知:采用實測輪軌廓形的車體橫向加速度遠比CHN60&LMA 廓形的加速度大,同時運行速度為250 km/h 時實測輪軌廓形的車體橫向加速度與運行速度為200 km/h時相比增加了一倍。采用實測輪軌廓形的輪對產生明顯蛇形運動,輪對橫向運動向一側鋼軌偏移,其中運行速度為200 km/h 時的輪對橫移幅值絕對值為1.2 mm,蛇形運動波長為40.45 m;運行速度為250 km/h 時的輪對橫移幅值絕對值為2.0 mm,蛇形運動波長為50.57 m。

圖11 不施加軌道不平順時車輛動力響應時程Fig. 11 Vehicle dynamic response time history without track irregularity
圖12 所示分別為車輛運行速度為200 km/h 和250 km/h 時車輛橫向加速度和橫向輪軌力頻程,其中L表示左股,R表示右股。由圖12可知:實測輪軌廓形的車體橫向加速度和一、二位橫向輪軌力明顯分別比CHN60&LMA 廓形的車體橫向加速度和一、二位橫向輪軌力大,運行速度為250 km/h時的橫向輪軌力明顯比運行速度為200 km/h 的大。不施加軌道不平順時車輛系統振動頻率統計結果見表2。由表2 可以看出:采用實測輪軌廓形的車體橫向加速度振動頻率為1.37 Hz,與橫向輪軌力振動頻率以及輪對蛇形運動頻率一致,也與列車晃車時的車體橫向加速度振動頻率一致。由此可見,實測輪軌型面和列車運行速度的提高會加劇輪對的蛇形運動,直接影響車體振動頻率。

表2 不施加軌道不平順時車輛系統振動頻率統計Table 2 Vibration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vehicle system without track irregularity Hz
4.2 軌道不平順對列車晃車的影響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本文所述列車晃車現象的影響因素,施加晃車區段的實測軌道不平順作為激勵,對比采用實測輪軌廓形匹配和CHN60&LMA 廓形匹配時不同運行速度下的車輛系統動力響應。

圖12 不施加軌道不平順時車輛動力響應頻程Fig. 12 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of vehicle dynamic response without track irregularity
圖13 所示為晃車區段實測軌道不平順時程和頻程圖像。由圖13 可知:左右股的軌道不平順差異性不明顯,軌向不平順和高低不平順的振動頻率存在明顯差別,其中軌向不平順主頻為1.37 Hz,與列車晃車時的車體橫向加速度振動頻率一致,高低不平順的主頻為2.14 Hz。

圖13 晃車區段實測軌道不平順圖像Fig. 13 Images of measured track irregularity of car body swing section
圖14所示為施加軌道不平順時車輛動力響應時程。由圖14可知:當列車運行速度為250 km/h時,采用實測輪軌型面的車體橫向加速度幅值明顯增加,且輪對橫移偏向左股鋼軌。輪軌廓形和運行速度變化對脫軌系數和輪重減載率影響較小,但對乘坐舒適性影響明顯,列車運行速度提升至250 km/h 時乘坐舒適性明顯降低,同時與采用CHN60&LMA 廓形相比,采用實測輪軌廓形的乘坐舒適性進一步降低。由此可見,車體橫向低頻晃車對列車運行安全性影響較小,但會導致乘坐舒適性降低。

圖14 施加軌道不平順時車輛動力響應時程Fig. 14 Vehicle dynamic response time history with track irregularity
圖15所示為施加軌道不平順時車輛動力響應頻程。由圖15可知:當列車運行速度為200 km/h時,輪軌廓形變化對車輛系統動力響應影響較小;當列車運行速度提升至250 km/h 時,輪軌廓形變化會導致車輛系統動力響應產生明顯變化。其中采用實測輪軌廓形,列車運行速度為250 km/h 時的車體橫向加速度譜峰為0.002 14 g2/Hz,較運行速度為200 km/h 時增大了1.6 倍,較采用CHN60&LMA廓形增大了1.5倍。表3所示為施加軌道不平順時車輛系統振動頻率統計結果,由表3 可以看出:當列車運行速度為250 km/h 時,采用實測輪軌廓形的車體橫向加速度振動頻率為1.37 Hz,與軌向不平順、輪對蛇形運動以及輪軌橫向力振動頻率一致,表明列車運行速度提升至250 km/h時,車輛受到的外部激勵會加劇輪軌動態響應,從而造成車體橫向出現低頻周期性晃動。

圖15 施加軌道不平順時車輛動力響應頻程Fig. 15 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of vehicle dynamic response with track irregularity

表3 施加軌道不平順時車輛系統振動頻率統計Table 3 Vibration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vehicle system with track irregularity Hz
5 結論
1) 當列車運行速度提高至250 km/h 后,晃車區段車體橫向加速度出現明顯低頻周期性波動,對車輛運行安全性影響較小,但會導致乘坐舒適性明顯降低。
2) 與CHN60&LMA 廓形相比,實測輪軌廓形加劇了輪對的蛇形運動,輪對運動偏向一側鋼軌,直接影響車體橫向振動頻率。
3) 列車提速后車輛系統響應對輪軌廓形變化更 敏感,軌道不平順振動頻率與輪對蛇形運動頻率一致時,會造成輪軌動態響應進一步加劇,導致車體產生橫向周期性低頻晃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