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贈書”與吳宓的西方古典學(xué)知識①
郭 濤,陳 瑩
(西南大學(xué) 歷史文化學(xué)院 重慶 400715)
20世紀前半期中國的西方古典學(xué)知識是如何形成的?在燦若群星的先哲中,吳宓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近年來,很多學(xué)者注意到吳宓不僅是比較文學(xué)的開創(chuàng)者,而且也是近代中國研究西方古典學(xué)的先行者之一。有學(xué)者考察了吳宓對古希臘文學(xué)的研究與翻譯,然而因為史料所限主要側(cè)重于線索的勾勒,或者將其置放于“學(xué)衡派”這一較為寬泛的背景中[1-4];也有學(xué)者試圖在世界古代史的框架下展開研究,但只局限于吳宓1953—1958年在西南師范學(xué)院歷史系任教期間的零星材料,難以窺其全貌[5-6]。吳宓究竟讀過哪些西方古典文本,他的古希臘語、拉丁語語言水平如何?吳宓又是如何用中國傳統(tǒng)語匯表達西方古典文化,在翻譯過程中遵循了怎樣的原則?換言之,吳宓的西方古典學(xué)知識是何種面貌?對于這一宏大而又細致的問題,在西南一隅的小城北碚恰恰存有一套鮮被學(xué)界關(guān)注的文獻,能夠提供豐富的史料。吳宓在1956年將自己收藏的大部分外文書籍整體性捐贈給西南師范學(xué)院,現(xiàn)由西南大學(xué)圖書館以“吳宓贈書”專題收藏。這套文獻不僅體量龐大,而且涵蓋了1950年代之前吳宓不同的人生階段。那么,我們能否從“吳宓贈書”的書籍中重構(gòu)吳宓,進而管窺20世紀前半期中國知識精英探索西方古典學(xué)術(shù)的歷程?
一、文獻來源與概況
“吳宓贈書”主要來自吳宓入蜀之后留在北京的藏書,曾由其前妻陳心一女士保管。在遷居北碚后,吳宓在1955年底決定將藏書整體郵寄,并捐贈給西南師范學(xué)院,他在1956年9月14日的日記中寫到:“宓捐送西師之書已達863冊。由友生取去而損失者甚多。現(xiàn)存者,雖宓所極愛重之書,亦無所顧惜,一體捐贈。”[7]511[8-9]關(guān)于吳宓捐贈書籍的具體數(shù)目存在爭議[9]150,經(jīng)常被學(xué)者忽視的一點是,吳宓在1956年之后對這套文獻進行過補充,他在《中世之心:歐洲中世思想感情發(fā)展史》(TheMediaevalMind)下冊扉頁題跋注曰:“今上冊竟遺失,甚望學(xué)校能不茍配全也。”[10]然而,該書上冊的扉頁題跋中則寫道:“此為歐洲中世史、歐洲文化史、世界文學(xué)史之極佳之參考書。共有上下二冊,宓皆購藏多年。初謂上冊遺失,乃1961年至北京竟取得之,喜可知矣。”[11]可見,“863冊”僅是1956年大規(guī)模贈書結(jié)束時的數(shù)字。
經(jīng)筆者新近對這套文獻的全面整理和研究,西南大學(xué)圖書館題為“吳宓贈書”的專題藏書現(xiàn)有外文書約630冊,另有全套的《學(xué)衡》《甲寅周刊》等少量中文書籍。所藏外文書籍主要是由歐美國家出版于19世紀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英語書為主,同時有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希臘語、拉丁語與和闐文。在藏書門類上,西方古典文明約127冊、歐洲中世紀與圣經(jīng)研究約13冊,近現(xiàn)代部分可大致按國別與區(qū)域分為英美約154冊、法國約262冊、德國約9冊、意大利約9冊、西班牙約7冊、俄羅斯1冊、東方約11冊;其它工具書、理論和通史類書籍約37冊。由此可見,古希臘羅馬、英美和法國是吳宓西學(xué)知識體系中的三個重心。
這套書籍的購置伴隨了吳宓在清華讀書、國外求學(xué)、國內(nèi)工作等不同的人生階段。吳宓本名“吳陀曼”,1910年改名“吳宓”[12],贈書中約4冊印有“吳陀曼”印章,其中一冊為《馬考萊擬作(共四篇)古羅馬英雄故事之民歌》(Macaulay’sLaysofAncientRome)[13],內(nèi)容是英國歷史學(xué)家馬考萊(今譯“麥考萊”)擬寫的四篇古羅馬英雄史詩,吳宓在扉頁注釋曰“(中學(xué)讀本)”,這本書是19世紀英國中學(xué)的標準讀本,應(yīng)是吳宓在清華留美預(yù)備科學(xué)習(xí)外文的讀本之一。吳宓赴美留學(xué)后,由于上課所需教材、參考書等原因,開始大規(guī)模購買外文書籍。吳宓在1892年版《威弗里小說集》(TheWaverleyNovels)第一卷扉頁撰寫題跋:“宓在美國哈佛大學(xué)肄業(yè)時1919年春始購置書籍。”[14]在《法國十七世紀文學(xué)選注讀本》(SeventeenthCenturyFrenchReadings)一書的頁邊上,吳宓當(dāng)年為應(yīng)付考試而做的筆記仍依稀可見[15]。回國任教后,吳宓在清華大學(xué)、東南大學(xué)、武漢大學(xué)、西南聯(lián)大等地教授《翻譯術(shù)》《文學(xué)概論》《文學(xué)批評》《英國散文》等課程的外文教材也在這套贈書之中,這部分書籍很多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經(jīng)由漢口、昆明的龍門書局翻印的版本。
在1956年3月至9月,吳宓一邊對這套藏書進行整理,一邊分批交付給圖書館。他用毛筆在大部分藏書的扉頁注釋了作者姓名、國籍和生卒年,將書名翻譯成中文,并做題跋,對書的版本、內(nèi)容進行介紹和評論,僅吳宓題寫的漢譯書名及扉頁題跋兩項,現(xiàn)存約1萬6千字(2)此為經(jīng)筆者整理、校勘后統(tǒng)計得出的數(shù)字。。所以,吳宓對這套贈書的整理,不僅是目錄學(xué)、版本學(xué)意義上的整編,而且也是一次具有相當(dāng)篇幅的、嚴謹?shù)膶W(xué)術(shù)寫作。與此同時,“吳宓贈書”中夾雜了吳宓求學(xué)和讀書時的注釋、筆記、摘抄、讀書卡片等大量資料,不啻為一座研究吳宓學(xué)術(shù)思想如何形成的“圖書館”。很大程度上,吳宓對這套書籍的整理是抱著臨終遺作的心態(tài)進行的。對于這位曾與“新文化運動”頑強抗爭的老先生來說,進入五十年代新的學(xué)術(shù)場景同樣是痛苦的。肖太云指出,吳宓具有某種殉道思想[16];張麒麟則強調(diào)當(dāng)時摯友相繼離散、家庭生活上的打擊造成吳宓晚年避世、出世、厭世,甚至求死的態(tài)度[8]19。無論如何,愛書之人整體性地捐出畢生珍藏,這一行為本身意味著對過去的學(xué)術(shù)與人生,甚至是對當(dāng)下生命的訣別。吳宓在日記中極富悲情地寫到,“如1956春之運書來碚,捐贈西師”等事,皆所謂“完結(jié)此生之債者”[17]112。可以說,吳宓對這套贈書的整理實際上是對自己學(xué)術(shù)思想一次難得的整體性回顧,因而是研究吳宓西方古典學(xué),乃至整個西學(xué)知識的珍貴史料。
二、文本閱讀與研究
吳宓讀過哪些西方古典文本,他的西方古典語言能力到底如何?吳宓深受白璧德等西方新人文主義學(xué)者的影響,認為古希臘羅馬蘊含著對現(xiàn)代人的指引和規(guī)范;不僅如此,西方古典文化因其原典地位,是吳宓及“學(xué)衡派”與新文化運動爭奪話語權(quán)的陣地[2]174。那么,吳宓對西方古典學(xué)是否有科學(xué)的嚴謹研究,抑或只是服務(wù)于對現(xiàn)實的關(guān)切?雖然“吳宓贈書”中的藏書并非吳宓閱讀書籍的全部,比如他曾于1957年將留存南京的希臘文學(xué)史11冊贈于郭斌和[17]72,但是約127冊西方古典學(xué)書籍的龐大體量仍然為我們提供了較為充分的證據(jù)。
吳宓對荷馬史詩頗有心得,這不僅體現(xiàn)在1923年《學(xué)衡》第13期發(fā)表的《荷馬之史詩》一文,同時也反映于他閱讀過的書籍。關(guān)于《荷馬史詩》的文本,吳宓在《西洋文學(xué)精要書目》一文中提到麥克米倫出版社在1883、1879年出版由安德魯·朗(Andrew Lang)等人英譯的散文體《伊里亞特》《奧德賽》[18]1,“吳宓贈書”中藏有該英譯本的節(jié)本2冊[19-20](3)此處“安德魯·朗”為筆者譯名。,扉頁均加蓋西南師范學(xué)院的前身之一“國立女子師范學(xué)院圖書館”印章,沒有贈書中普遍加蓋的“吳宓藏書”印章,但借書卡上寫有吳宓1957年10月10日的借閱記錄,因此至少可以說,麥克米倫出版社出版于1883、1879年的英譯本,或者該譯本的節(jié)本,是吳宓閱讀荷馬史詩曾經(jīng)采用過的文本。除此之外,“吳宓贈書”中還藏有多部研究性專著,在1923年之前出版的有6冊:《荷馬研究手冊》(HandbookofHomericStudy)[21]、《荷馬與史詩》(HomerandtheEpic)[22]、《荷馬同時論:荷馬史詩之時與地研究》(HomericSynchronism:TimeandPlaceofHomer)[23]、《特洛耶城:荷馬史詩之地理研究》(Troy:AStudyinHomericGeography)[24]、《荷馬統(tǒng)一論》(TheUnityofHomer)[25]、《安諾德全集卷七:論古愛爾蘭文學(xué)、論翻譯荷馬》(OntheStudyofCelticLiteratureandonTranslatingHomer)[26]。
在《荷馬之史詩》一文中,吳宓明確指出曾參考安諾德《論荷馬翻譯》對荷馬史詩行文風(fēng)格的論述,上述其他幾冊書籍雖未明確提及,但內(nèi)容基本涵蓋了《荷馬之史詩》一文所涉及的荷馬史詩的語言、結(jié)構(gòu)、創(chuàng)作過程、歷史背景等問題,特別是對所謂“荷馬問題”的討論,吳宓列舉的武魯夫(F. A. Wolf,今譯“沃爾夫”)等十位代表性學(xué)者的觀點在上述參考書中都有涉及。其中,《荷馬統(tǒng)一論》出版于1921年,屬于西方古典學(xué)界久負盛名的“薩瑟古典講座”(Sather Classical Lectures)叢書,遺憾的是,吳宓沒有在《荷馬之史詩》一文中提到該書作者斯科特(John A. Scott),(4)此處“薩瑟古典講座”“斯科特”為筆者譯名。但可以確認他曾認真閱讀過,在扉頁題跋中概括、評論其觀點:“主張荷馬實有其他人,而伊里亞特與奧德賽二史詩皆荷馬一手作成,并指出荷馬以海克多為‘道德之英雄’,其立意之正大。”因此可以推測,吳宓在1923年發(fā)表《荷馬之史詩》一文后才研讀該書。在“吳宓贈書”中,還藏有2冊在1923年之后出版的研究專著:《伊里亞德之傳統(tǒng)及計畫》(TraditionandDesignintheIliad)[27]和《希臘史詩之起原》(TheRiseoftheGreekEpic)[28],吳宓在前書扉頁題寫的書籍中譯名之前,追加標注了一個書目分類名稱“荷馬史詩研究”。因此,可以發(fā)現(xiàn),吳宓在發(fā)表《荷馬之史詩》一文后對荷馬史詩及相關(guān)研究的思考并未停止。值得一提的是,吳宓在《西洋文學(xué)精要書目》一文提到《希臘史詩之起原》的1911年版[18]2,“吳宓贈書”現(xiàn)存版本是1924年版,沒有裁頁,所以對1924年版《希臘史詩之起原》沒有通讀,盡管如此,購置新的版本仍能說明,吳宓持續(xù)關(guān)注、追蹤西方古典學(xué)界的新近研究成果。
相較于荷馬,吳宓研究希霄德(Hesiod,今譯“赫西俄德”)的參考書籍則非常明確,他在邁爾(A. W. Mair)所著《希霄德詩集》(Hesiod:ThePoemsandFragments)扉頁撰寫題跋:“宓1923撰希臘文學(xué)史中希霄德一章,載學(xué)衡雜志第十四期者,即本此書而演述之。”[29](5)此處“邁爾”為筆者譯名。邁爾全書分為四章:導(dǎo)論、文本提要、英譯文及附錄,其中“導(dǎo)論”分為四節(jié),第一節(jié)“希霄德的詩歌”,主要介紹其文體與史詩的區(qū)別、與希伯來智慧文學(xué)的對比和語言風(fēng)格,第二、三節(jié)的標題分別為“希霄德的生平”和“歸于希霄德的詩歌”。吳宓1923年在《學(xué)衡》第14期發(fā)表的《希霄德之訓(xùn)詩》一文分為四節(jié):第一節(jié)“希霄德以前之訓(xùn)詩”、第二節(jié)“希霄德略傳”、第三節(jié)“希霄德訓(xùn)詩之內(nèi)容”、第四節(jié)“希霄德訓(xùn)詩之評論”。
如果將兩份文本對比,會發(fā)現(xiàn)很多有趣的相似和不同。在邁爾的“導(dǎo)論”第一節(jié),首先強調(diào)史詩與訓(xùn)詩的主要區(qū)別是:史詩重娛樂,而訓(xùn)詩重教誨;相較之下,吳宓《希霄德之訓(xùn)詩》的第一節(jié)則列舉了與史詩的八條區(qū)別,只有第三條是對邁爾原書內(nèi)容的概括,其他七條均為吳宓的思考和演繹;繼而,邁爾將希霄德對希伯來智慧文學(xué)進行了對比,吳宓則將這部分內(nèi)容改編至第四節(jié)的第三小節(jié)“希霄德訓(xùn)詩與希伯來圣書比較”;緊接著,邁爾從語文學(xué)的角度,指出希霄德經(jīng)常使用隱喻性的語言,比如用“雅典娜的侍者”代替“木匠”,而吳宓則在第四節(jié)第二小節(jié)“希霄德詩才之特長”介紹了希霄德的語言風(fēng)格,但沒有采用邁爾的觀點,而是歸納為“性情真摯”“文筆簡潔”“描繪逼真”和“利用自然”,這四個方面在邁爾的書中均未提及。
邁爾“導(dǎo)論”第二節(jié)討論希霄德的生平,從內(nèi)證、外證兩個方面列舉西方古典文本證據(jù),沒有過多評述;而吳宓強調(diào)應(yīng)該依據(jù)希霄德自身文本的記載,認為“以上皆希霄德于其詩中所自敘,要皆可憑信也”,指出“后人所作傳,述希霄德之事跡者極多,然皆不可信”,繼而對邁爾列舉的“外證”史料的缺陷、謬誤進行了洋洋灑灑地評述。最后,邁爾在“導(dǎo)論”第三節(jié)整理了提及希霄德及其作品的古典文本,列舉歸名于希霄德的作品名稱,并做簡介;吳宓則將這部分內(nèi)容調(diào)整至自己文章的第三節(jié),在介紹《田功與日占》(WorkandDays)、《諸神紀》(Theogony)的主要內(nèi)容后予以羅列和簡介。不難發(fā)現(xiàn),吳宓的《希霄德之訓(xùn)詩》一文有明顯模仿、改編邁爾《希霄德詩集》“導(dǎo)論”部分的痕跡,但同時在文章的論證結(jié)構(gòu)、具體觀點上有不少自己的思考和創(chuàng)見。
除了荷馬和希霄德,吳宓對很多古希臘羅馬經(jīng)典作家都有閱讀和研究。“吳宓贈書”中藏有:品達(Pindar)1冊、愛斯克勒(Aeschylus)2冊、蘇福克里(Sophocles)2冊、尤里披底(Euripides)5冊、阿里斯多芬尼(Aristophanes)3冊、芝諾芬(Xenophon)2冊(有一冊與柏拉圖為同一本書)、德謨森尼(Demosthenes)1冊、柏拉圖(Plato)15冊、亞里士多德(Aristotle)19冊、海里奧道魯斯(Heliodorus)1冊、凱撒(Caesar)1冊、西塞羅(Cicero)2冊、布魯塔克(Plutarch)7冊、維吉爾(Virgil)3冊、路克安(Lucian)4冊,奧維德(Ovid)2冊、阿普列烏斯(Apuleius)1冊、朗吉努斯(Longinus)1冊、盧克萊提斯(Lucretius)1冊、彼得羅尼(Petronius)1冊、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1冊、隆古斯(Longus)1冊、圣奧古斯丁(St. Augustine)2冊。(6)此處“阿普列烏斯”“朗吉努斯”“隆古斯”是筆者譯名。吳宓對這些古典作家有較為準確的了解,比如:他根據(jù)文本的內(nèi)容將德謨森尼(今譯“德謨斯提尼”)的演說辭《金冠辭》(UpontheCrown)譯為《自辯辭》,并在扉頁題跋中概括其內(nèi)容為“自敘一生功業(yè)應(yīng)受國家榮褒”,注釋這篇演說辭發(fā)表的年代為“330BC”[30];將阿普列烏斯的《金驢記》(TheGoldenAss)譯為《變驢記》,并在扉頁題跋中解釋到“此書在當(dāng)時風(fēng)行,故后人加‘金’字于上,言其書甚可寶貴,稱曰金驢,實非本名也”[31]。對于殘篇、軼文等不那么“經(jīng)典”的文本,吳宓也很關(guān)注,不厭其煩地完整翻譯了1851年版凱撒著作英譯本的書名:《凱撒所作高盧戰(zhàn)紀八卷 其第八卷乃部A. Hirtius所續(xù)內(nèi)戰(zhàn)紀三卷 附非洲西班牙戰(zhàn)紀部將所作詩文集軼》[32]。
吳宓對西方古典文本的閱讀、研究主要依據(jù)當(dāng)時流行的英譯本,但在“吳宓贈書”中保留了不少閱讀古希臘語原文的筆跡。周軼群在《吳宓與世界文學(xué)》一文中認為,吳宓主要是在東南大學(xué)任教時隨《學(xué)衡》同人郭斌和學(xué)過古希臘語[33]38-39,這一說法不準確,“吳宓贈書”中的題跋對此提供了更為詳細的說明。吳宓在1921年牛津版《亞里斯多芬尼所作諧劇云》(TheCloudsofAristophanes)扉頁題跋寫道:“1923年夏英國香港大學(xué)副校長沃姆G. N. Orme先生力勸宓等學(xué)習(xí)希臘文(詳見學(xué)衡雜志二十二期)。宓遂托先生回英國后代為選購希臘拉丁文學(xué)研究之精要書籍。其后先生函告宓曰,英國古典文學(xué)家李文斯敦先生特贈二書與君,今同寄上,望君能日進于所志之學(xué)業(yè)也。宓得讀李文斯敦先生編著之書,殊深敬慕。是年秋始從南京英國教士Mather先生學(xué)希臘文,不久而輟,終于無成。”[34]



西方古典語言是通達古典學(xué)術(shù)的基礎(chǔ),吳宓曾勉勵后輩在留學(xué)期間學(xué)習(xí)古希臘語和拉丁語,強調(diào)“研究古典文字即探求西洋文化之根源之工夫也”[47]。吳宓踐行了自己的學(xué)術(shù)理念,盡管他在1956年為贈書撰寫題跋時聲稱,自己的西方古典語言學(xué)習(xí)“不久而輟,終于無成”,但是我們根據(jù)吳宓讀書時做的筆記、注釋等痕跡,有理由認為他的古希臘語、拉丁語能力至少曾經(jīng)達到文本細讀的水平。1933年出版的郭斌和、景昌極合譯《柏拉圖五大對話集》的序言寫到:“是書之譯,吳雨僧先生實主張之。譯后又取各英文譯本與希臘文原本,詳為之校。”[48]由上觀之,此言誠非虛語。
三、翻譯實踐與理論
吳宓不僅有廣泛的研讀,而且致力于對西學(xué)古典文本的譯介,在其主辦的《學(xué)衡》雜志發(fā)表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的多篇原典。吳宓如何用中國傳統(tǒng)語匯表達西方古典文本?他如何平衡西方古典文明與中國文化的關(guān)系?在已刊印發(fā)表的文獻中,吳宓本人對西方古典文獻原文的翻譯并不多,因而相關(guān)研究往往被置放于“學(xué)衡派”這一較為寬泛的背景中考察。鮮被學(xué)者注意到的是,“吳宓贈書”中的題跋、頁邊注釋記載了不少吳宓關(guān)于翻譯的思考,那么,這些“犄角旮旯”里的文獻對當(dāng)前的相關(guān)研究結(jié)論是否有所補充,甚至是糾正?
首先,吳宓是如何翻譯西方古典研究中的專有名詞的?在“吳宓贈書”扉頁題跋翻譯的書名和題跋中,很多古典作家的譯名在當(dāng)代學(xué)界仍然使用,比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凱撒”“奧維德”等。他傾向于只音譯人名的詞干部分,而不譯會因變格而發(fā)生變化的詞尾,比如“Aeschylus”譯為“愛斯克勒”而不是“愛斯克勒斯”,但偶爾也會全部譯出,比如“Lucretius”譯為“盧克萊提斯”。雖然“吳宓贈書”的題跋主要是在1956年3月至9月期間集中寫作的,但一些譯名沒有統(tǒng)一,比如“愛斯克勒”又譯為“愛斯克洛”,“尤里披底”又譯為“幼里披底”,“阿里斯多芬尼”又譯為“亞里斯多芬尼”,“布魯塔克”又譯為“布爾特奇”。這一現(xiàn)象在“吳宓贈書”其他門類書籍中同樣存在,比如吳宓將《雜俎》(Variété)一書的作者“Paul Valéry” 譯為“韋拉里”,同時注明梁宗岱的譯名“梵樂希”[49]。吳宓沒有像羅念生那樣編訂一份《希臘拉丁文譯音表》,但他意識到翻譯需要警惕方言的影響,吳宓為《孟德恩論文集》一書撰寫的題跋可作參考:“此為法國十六世紀后半散文大作者孟德恩之論文集論文一體乃其所創(chuàng),原‘嘗試’之意,吾國梁宗岱君曾有介紹,譯其名曰蒙田粵音。此英譯本1603作于莎士比亞之時,亦古樸有名。共三冊”,吳宓指出梁宗岱的譯名“蒙田”根據(jù)粵語方言是不妥的[50]。
吳宓在閱讀西方古典文獻的過程中,針對一些短語、短句和段落在書籍的頁邊位置做了批注,對原文進行轉(zhuǎn)寫、概括或摘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對原文的一種“翻譯”,具有代表性的幾例有:

吳宓讀書頁邊注釋舉要(14)序號1—8所在書籍版本信息為Benjamin Jowett trans.,The Dialogues of Plato,vol. 1,New York:Scribner Armstrong and Co.,1873。序號9所在書籍版本信息為:A. D. Lindsay ed.,Plato and Xenophon:Socratic Discourses,London:J. M. Dent &Sons,1910。序號10所在書籍版本信息為:Theodore Alois Buckley trans.,The Tragedies of Aeschylus,London:George Bell &Sons,1901。序號11—17所在書籍版本信息為:J. E. C. Welldon trans.,The Rhetoric of Aristotle,London:Macmillan,1886,該書沒有收藏于“吳宓贈書”之中,扉頁未加蓋“西南師范學(xué)院圖書館”鋼印,但蓋有和“吳宓贈書”所藏書籍相同的“吳宓藏書”印章,遺憾的是,這本書已被私人書商售賣,不知所蹤,筆者只獲得部分照片。
正如很多學(xué)者注意到的那樣,吳宓熱衷于用文言,而非白話翻譯西方古典文獻,比如表格第12例“the law of nature”,今譯為“自然法”,而吳宓則譯為“天道、公理”;吳宓總是尋找與中國古代典籍相互對應(yīng)的表達,比如表格第5~8例,征引《論語》《孟子》《大學(xué)》中的語句來概括,或者說“意譯”柏拉圖的原文語句。吳宓批評郭斌和、景昌極的某些翻譯受到了流行白話文的影響,在1873年版喬伊特(Benjamin Jowett)譯《柏拉圖對話錄》第一卷扉頁,粘貼有郭斌和、景昌極譯《柏拉圖五大對話集》的廣告插頁,吳宓在此寫下評論:“此書原登學(xué)衡雜志,各篇均經(jīng)吳宓校注。其書名應(yīng)曰語錄,不應(yīng)從今俗曰對話,時宓在歐洲,乃逕出版,不從宓定名,可憾也。”[41]對于吳宓的翻譯風(fēng)格,施耐德(Axel Schneider)強調(diào)吳宓是一位“古典保守主義者”,同時混合了孔子和柏拉圖的語言元素[51],姜筠則認為使用中國古典語言翻譯西方古典文獻的目的是強調(diào)兩種文化之間的共性[1]199。需要注意的是,吳宓意識到中西古典語言之間存在無法對譯的情況,比如表格第16例“在古希臘人中,又在古希臘文中,友與愛無別。”因此,劉津瑜的解釋更引人深思,吳宓及“學(xué)衡派”并非簡單地尋找中國與西方古典語言之間的一一對應(yīng)關(guān)系,在翻譯過程中對原文的意思進行增加或刪減,比如:郭斌和用“禮”翻譯柏拉圖的“καλν”,強化了禮教的成分,而弱化或無視歡娛(pleasure)也是這一概念的重要內(nèi)容[4]103。
如果可以接受這樣的解釋,那么吳宓及“學(xué)衡派”在翻譯西方古典文本時遵循的標準是什么?吳宓在1923年發(fā)表的《論今日文學(xué)創(chuàng)造之正法》一文曾指出,翻譯應(yīng)依據(jù)嚴復(fù)的“信、達、雅”原則,但同時又指出翻譯的具體方法以“意譯(Paraphrase)最合中道”[52],這里的“意譯”具體指什么原則?吳宓在閱讀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第332—363行被學(xué)界稱為“人頌”的合唱歌時,在原書第11頁頁邊位置不無自豪地注釋道:“已由宓譯出,見學(xué)衡53期,又載吳宓詩集卷七9—10頁,題曰人智之卓越”[53](15)此處“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為筆者譯名。,然而,《吳宓詩集》刊印的只有文言詩體譯文本身,沒有解釋為何如是翻譯。對于吳宓及“學(xué)衡派”來說,對原文意思的增刪與“信、達、雅”原則如何保持平衡?
在“吳宓贈書”中,藏有1冊“人人文庫”1907年版英國翻譯理論家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的《翻譯原理論》(EssayonthePrinciplesofTranslation)[54],為深層描繪吳宓的翻譯原則提供了形象證據(jù)。吳宓對此書極為愛護,將其作為在清華大學(xué)教學(xué)的課本,在扉頁題跋寫道:“始自1925年,宓在清華授翻譯術(shù)一課程,恒以此書為課本,用之多年,其書尚如新。”在第一章第9頁,泰特勒提出了翻譯的三原則:I.譯文應(yīng)完全復(fù)寫原文的意思,II.譯文應(yīng)與原文具有相同的風(fēng)格,III.譯文應(yīng)與原作一樣流暢,吳宓在此頁的頁邊注釋曰:“嚴幾道(復(fù))先生(一)信(二)達(三)雅之說,似由此出。”緊接著,《翻譯原理論》分章舉例闡釋了翻譯的三原則,吳宓對每章列舉的范文都做了數(shù)字標號,對第一部分關(guān)于“信”的討論尤為關(guān)注,泰特勒認為,譯者擁有增加或刪減原文意思的自由,對此吳宓在頁邊做了多條注釋。
對于增加原文意思,泰特勒主張譯者可以追加從原文衍生出來的意涵,并在書中第22~23頁以英國詩人諦克爾(T. Tickell)《死別》(ColinandLucy)一詩第四、五節(jié)的法譯文為例。有趣的是,吳宓曾將這段詩譯為中文,《吳宓詩集》刊印的版本為:“明日入婚筵,雙雙各整備。勖汝新鴛鴦,露西行親蒞。慎將吾遺體,往見俏郎君。羨郎著華服,憐妾覆素衾。”[55]然而,在《翻譯原理論》第23頁的頁邊位置,吳宓謄寫了自己初期的譯文“明日入婚筵,1彼時同戒備。2勖汝雙新人,露西行親蒞。慎將吾遺體,往見俏郎君。3羨郎著華服,4憐妾覆素衾”,繼而羅列了文中數(shù)字標號處的備選譯法:“1雙雙各整備、2寄語新鴛鴦、3喜郎著華服、4君衾不同顏。”最后,吳宓在同一頁邊位置單獨寫下一句譯文:“往別俏郎君,看郎著華服”,將其中的“別”“看”用紅筆劃線強調(diào),并用英文注明泰特勒使用的術(shù)語“Superadded idea”,吳宓另將1925年翻譯全詩的初稿字條粘貼在此處。字條和頁邊注極為生動地再現(xiàn)了依據(jù)泰特勒的理論翻譯《死別》的全過程。

由此觀之,吳宓在對荷馬史詩具體文本的翻譯上,與泰特勒有不同意見,尤其是對中西方經(jīng)典文獻中英雄形象的比較使他跳出、超越了泰特勒的研究視野。但總體而言,吳宓接受了泰特勒的翻譯原則,不僅將這些原則貫徹于翻譯實踐中,而且將自己的譯詩作為體現(xiàn)這種原則的范例。不難發(fā)現(xiàn),吳宓(某種程度上包括“學(xué)衡派”)從泰特勒《翻譯原理論》那里接受過來的“信”這一翻譯原則與我們通常理解的“忠實原文”的意涵具有顯而易見的差別,譯者可以為保持所謂原文的“本意”對原文的意思進行添加或刪減,究竟什么是“原文的本意”往往取決于譯者自己的理解。事實上,在吳宓的觀念中,“文學(xué)”的旨歸乃是“救世”,他對只強調(diào)客觀實證的考據(jù)之學(xué)是批評的。正如周軼群指出的那樣,吳宓有著強烈的淑世之心[33]83,在“吳宓贈書”收藏的《亞里士多德全集撮要》(Aristotle)一書扉頁題跋中,吳宓寫道:“作者乃一考據(jù)之學(xué)者,思想及文筆無足稱,所著道德權(quán)責(zé)論未能動人,有枯索之感。宓在牛津曾往謁聆教,亦無所得也。”[56]由此觀之,“忠實原文”,抑或“準確”,并不是吳宓翻譯西方古典文本時追求的首要目標,相反,吳宓及“學(xué)衡派” 通過借用泰特勒的翻譯理論獲得了“以新內(nèi)容入舊格律”的方法,在標榜“信、達、雅”的同時,“重寫”西方古典文本,將西方古典知識嵌入中國傳統(tǒng)語言之中,進而實現(xiàn)其最終的文化理想:構(gòu)建一種融合中西方古典文化,卻又超越其上的新文化。
四、結(jié) 語
通過對“吳宓贈書”的研究,我們可以重構(gòu)吳宓西方古典學(xué)知識的大致面貌:吳宓對西方古典文本有著較為廣泛的研讀,雖然以英譯本為主,但他的古希臘語、拉丁語能力達到文本細讀的水平;他對西方古典學(xué)界的研究成果有著持續(xù)的追蹤與研讀,對具體文本的研究既有模仿西方學(xué)者的痕跡,也有不少自己的創(chuàng)見;與此同時,在翻譯西方古典文本的過程中,吳宓的目標不是實證性的考據(jù),他秉承的翻譯原則允許譯者有增刪原文的自由,進而“重寫”西方古典文本,將西方古典文化融匯、嵌入中國的傳統(tǒng)語匯之中。近年來,國內(nèi)學(xué)界對如何建設(shè)中國的西方古典學(xué)科的路徑存在不小爭議,[57]一方面,如何科學(xué)、準確地通達西方古典學(xué)術(shù),另一方面,如何平衡西方古典文明與中國文化,乃至現(xiàn)代中國社會的關(guān)系?這不僅是當(dāng)代學(xué)者爭論的焦點,也是20世紀前半期中國研習(xí)西學(xué)的先哲們曾經(jīng)面對的問題。必須承認,我們無法從先哲那里照搬答案,然而,對吳宓西方古典學(xué)知識的考察仍然能夠為我們重新審視20世紀前半期西方古典學(xué)知識在中國的形成提供了一個縮影,據(jù)此鞭策我們反思前輩們的探索歷程和經(jīng)驗,并進一步思考:如何“讓西方古典學(xué)真正成為最優(yōu)秀的中國學(xué)術(shù)之一部分”?[58]
非常遺憾的是,吳宓的西方古典學(xué)知識在50年代之后的傳承充滿坎坷。他雖然對西方古典學(xué)術(shù)有不少了解和研究,但在歷史系教授《世界古代史》課程期間仍發(fā)出“用宓之才學(xué)不當(dāng),且使本門課程受損也”的感嘆[7]274。對于“吳宓贈書”這套當(dāng)時國內(nèi)不多見的外文文獻,吳宓在1962年致李賦寧的信中寫道:“……此間無人讀此一批書也。其中有許多重要有用之書(如Du BellayDéfenseetIllustrationdelaLangueFran?aise1549)(19)此處原書校勘的作者名和書名有少許錯誤,在征引時糾正,現(xiàn)存“吳宓贈書”中沒有找到這本書。,如北大楊周翰等諸公,編譯外國文學(xué),盡可利用……”[59]此處的“無人讀此一批書”實際上是有所夸張的,但可以想象,這樣的感嘆源自他極度孤寂而又無奈的心境,社會與時代的巨變導(dǎo)致他孜孜以求的治學(xué)方法、學(xué)術(shù)理想不被認同,蜀中知音難覓,畢生所學(xué)無所用之。雖然斯人已去,但值得慶幸的是“吳宓贈書”事實上留下了不少印記,《荷馬研究手冊》一書貼有字條“此書插圖及地圖,甚可貴重。且為世界古代史課之必要參考書。故望能于1956年九月十五日以前,編目完成,可以借”[21],《特洛耶城:荷馬史詩之地理研究》一書貼有字條“世界古代史必用之參考書(望早編目)”[24],這套文獻中的很多書籍成為西南師范學(xué)院教授《世界古代史》課程的參考書,不僅如此,在《西塞羅演說集》(OrationsofMarcusTulliusCicero)[60]、《西塞羅道德論集》(Cicero’sThreeBooksofOffices,orMoralDuties;andhisCatoMajor,anEssayonOldAge;Laelius,anEssayonFriendship;Paradoxes;Scipio’sDream;andLettertoQuintusontheDutiesofaMagistrate)[61]、《布魯塔克希臘羅馬英雄傳》(Plutarch’sLives)[62]、《劍橋中世紀史》(TheCambridgeMedievalHistory)[63-65](20)此處“《劍橋中世紀史》”為筆者譯名。等書籍的借書卡片上留下世界古代史教研室教師孫培良、王興運、陳濟滄、喻小航等在1950—1980年代的借閱記錄。隨著歷史的變遷,書籍不斷被重新閱讀,吳宓的西方古典學(xué)知識也隨之被繼承和重塑,而這則屬于一個新時代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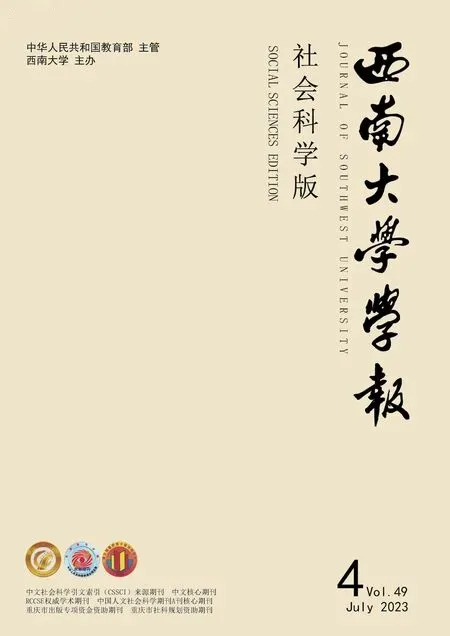 西南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3年4期
西南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3年4期
- 西南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唐代城市應(yīng)對戰(zhàn)爭機制的歷史考察
- 機構(gòu)投資者實地調(diào)研對高管機會主義減持的影響研究
- 金融科技與制造業(yè)創(chuàng)新結(jié)構(gòu)特征
——兼論科技和金融結(jié)合試點的效應(yīng)差異 - 城鎮(zhèn)化路徑對農(nóng)民工城市化質(zhì)量的影響研究
- 中西部農(nóng)業(yè)縣的拆分型城鎮(zhèn)化與依附性城鄉(xiāng)關(guān)系
——基于甘肅省X縣的實證研究 - 中國共產(chǎn)黨人英雄精神譜系構(gòu)筑的百年傳承與守正創(chuàng)新>
——基于Gephi的可視化分析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