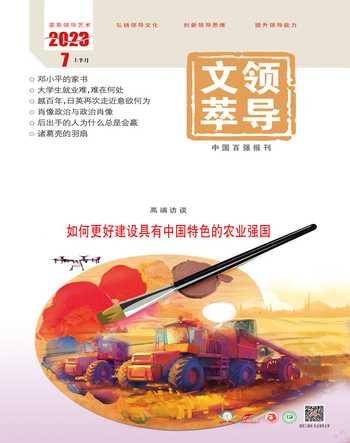大學生就業難,難在何處
柴新社

近些年,大學生就業問題備受關注,眼下更是如此。日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目前高校畢業生就業已進入關鍵階段,要不斷優化完善相關穩就業政策,加大對吸納高校畢業生數量多的企業的政策、資金支持,深入實施“三支一扶”等計劃,推動應屆畢業生多渠道就業。此外,近期各級地方政府、有關部門也紛紛出臺政策穩就業,重點是促進大學生就業。這些政策動向折射出大學生就業形勢之嚴峻。
就業是民生之本,關乎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近些年來,每年的高校畢業季都被稱作“最難就業季”,今年也不例外。據教育部預測,2023年,將有1158萬名應屆高校畢業生,比2022年增加80余萬,創歷史新高。加上近百萬歸國留學生,今年大學畢業生總量可能達到1250萬以上,就業壓力看起來確乎不小。
大學生就業難是如何造成的?不少人指責大學畢業生眼高手低、就業觀不正、求安求穩,這種指責既不公平,也無濟于事。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有政協委員提出,化解就業難,不能圍著“假問題”費盡力氣找答案;現在主要“難”在崗位供給上,而不是高校和學生身上,應抓住主要矛盾針對性地解決問題。我們基本贊同這一觀點。大學生就業難與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相伴隨,不是偶然的。
大學生就業難是國內整體就業市場矛盾的集中體現,其原因錯綜復雜,短期因素與中長期因素交織,周期性因素與結構性因素疊加。其中,既有三年疫情沖擊的累積作用,也有一些行業前期收縮性政策的時滯效應,還有經濟下行帶來的周期性失業,更有產業升級導致的結構性失業。更嚴重的是,一些深層次的體制機制扭曲仍在阻礙就業市場充分發育、良性運轉,放大了上述所有效應。因此,這一問題應對起來相當棘手,要穴則是推動結構性改革。
中國經濟正在復蘇,但是,房地產、互聯網等行業面臨深度調整,廣大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等市場主體有待恢復元氣。總體而言,經濟仍未完全回歸正軌,因而吸納就業能力不強。在此情形下,部分應屆畢業生考研考博延遲就業,“考公”“考編”熱度居高不下,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編制重新成為年輕人眼中的“香餑餑”。上述種種情形只能說明大學生的就業出路在收窄,而他們做出的選擇亦屬經濟人理性,對此應抱“同情式理解”。
緩解大學生就業難,當務之急是穩住經濟大盤、提升經濟景氣,歸根結底要靠市場、靠改革開放。倍加愛護市場主體是題中應有之義,避免出臺收縮性政策則是底線。依靠市場規模與勞動分工之間的相互促進,市場吸納就業的能力幾乎無窮無盡,關鍵是市場是否遭受體制性的抑制和扭曲。
民營經濟吸納了超過80%的城鎮就業。所以,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主要出路在于提振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信心,穩定其預期。這要求各級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擴大市場準入,打造穩定透明、公平競爭、激勵創新的法治化營商環境。當下,應集中清理三年疫情遺留的商業不友好舉措。此外,還應深化土地、戶籍、教育等領域的改革,使得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類生產要素能夠更加自由流動,由市場合理配置稀缺資源。由政府出面多張羅幾場招聘會或“強化就業觀念引導”,作用實在有限。
強調結構性改革,并不是說可以忽略其他方面的改進。高校需要積極探索改革之路,大學生也應主動求變,這自不待言。近日,教育部等五部委印發《普通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優化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優化調整高校20%左右學科專業布點,新設一批適應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學科專業,淘汰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學科專業。這可看作高等教育主管部門因應就業市場變化之舉。不過,中國高校更須注重人才培養方式變革。近期,社會上彌漫著有關人工智能(AI)未來沖擊就業的焦慮。誰也無法準確預言未來就業市場具體情勢,甚至連廢設專業本身也冒著一定風險,但是,真誠鼓勵創新、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高大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是高等教育可以做、也最應該盡快做的工作。
關于大學生就業難,最難以令人接受的是大學生“過剩論”。國際上通常用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指高等教育在學人數與適齡人口之比)作為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的指標,50%以上為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中國剛剛進入這一階段。中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與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仍有不小差距,而大學生就業難并未成為他們的突出社會問題。大學生“過剩論”不僅難以成立,還會引致荒唐的解決方案,即大幅壓縮中國高等教育規模。
2021年,中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達到2.4億。用不好,大學畢業生就會被當作穩就業的負擔;用好了,他們就是服務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寶貴人力資源。緩解大學生就業難,當下需要對癥下藥、多管齊下、形成合力。重中之重是通過深化體制改革為就業加“潤滑油”,力避或隱或顯的收縮性政策向就業“扔沙子”。
(摘自《財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