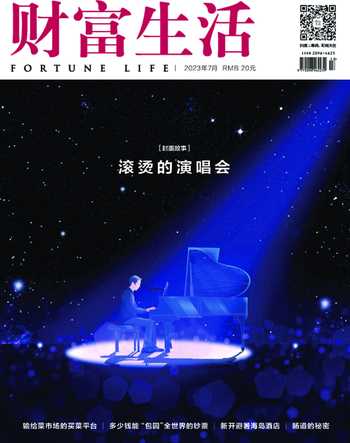貨郎擔與換糖人
仲富蘭

最近滬上五角場大學路推出了步行街集市,其中“后備廂集市”的新聞很搶眼,不禁令我想起了舊時走街串巷的“貨郎擔”與“換糖人”。
說起這汽車后備廂里的生意,是汽車普及的產物。曾幾何時,有水果小販,開著車去周邊各地收水果,夏天賣西瓜,秋天賣桂圓、梨、橘子、橙子、桃、李子……收來之后再拉到城里各個小區門口賣,開著汽車畢竟與拉勞動車、踏黃魚車不一樣,效率高多了,汽車開到小區集中的路口,就地打開車廂板就是貨架,交易就如約而至。
不知怎的,這汽車“后備廂集市”,總是讓我想到早先的“貨郎擔”與城市里游走的“換糖人”。所不同的是,后者人挑肩扛、走街串巷,如今則是販運工具現代化而已。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永遠是社會底層生活最基本,也是最有智慧的力量,人間生活須臾難離啊。
在基本沒有商品流通的時代,貨郎的一副擔子,實際上就是一個流動的百貨店。元代王曄《桃花女》楔子:“我待繡幾朵花兒,可沒針使,急切里等不得貨郎擔兒來買。”《水滸傳》第七十四回:“你既然裝做貨郎擔兒,你且唱個山東《貨郎轉調歌》與我眾人聽。”說明那個時候的貨郎擔已經發展得很成氣候了。明清以降,商業日益發達,但貨郎擔依然是民間重要的老行當。明代劉若愚《酌中志·內臣職掌紀略》說:“又御用監武英殿畫士,所畫錦盆堆則名花雜果,或貨郎擔則百物畢陳。”,那個時代,貨郎擔在民間很是普遍。有歌謠唱道:“貨郎兒,賣花線,挑著擔子走街面。叮當搖動喚嬌娘,引出嬌娘門口見。嬌娘宜笑宜復嗔,價要便宜貨要新。僥幸貨郎有艷福,生涯常與美人親。”在鄉村女子眼中,貨郎就是一個大英雄,嬌娘跟著貨郎走,也不乏其例。
我想起童年時代,生活在上海,小孩子家對走街串巷的貨郎一概喚作“換糖的”,那個時候沒有城管,街頭弄堂都會回響著撥浪鼓清脆的聲音。“換糖的”就是以物易物,“雞毛換糖”“牙膏片換糖”之類,也兼收破爛。雖是一些針頭線腦、糖果紐扣之類,但還是受到孩子們的歡迎。
只要孩童們跟著“換糖的”走,或走或停,嬉笑聲和喧嘩聲會引來湊熱鬧或是購物的大人。“換糖的”就放下擔子,打開他的“百寶箱”,介紹他的“新產品”。孩子們就會拿著雞毛、鴨毛、牙膏殼、爛布料之類的東西換糖果吃,沒有這些東西的孩子就鬧著要家人買糖吃,或買那些塑料小水槍。于是乎,買紅頭繩的、買糖的、買小玩具的,一時間熱鬧非凡,孩子們都沉醉在無言的快樂之中。接著就輪到婦女們挑揀適用的生活用品了,或是一把木梳,或是一些針線紐扣之類。
“換糖的”經歷了漫漫歲月,大約到了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就漸漸地不見了蹤影,成為民眾一種久遠的城市生活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