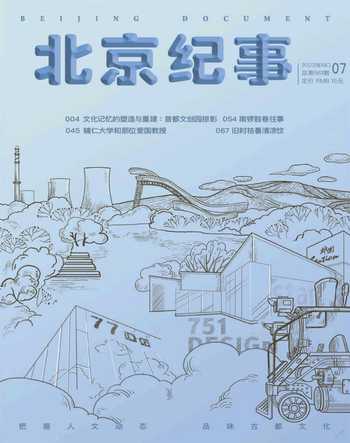永定河傳說的“源”與“流“
永定河系海河支流之一,源于山西省寧武縣的管涔嶺天池,流經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天津等地。該河水流湍急,上流所經,多為黃土地帶,水濁泥多。“蓋自石景山而下,兩岸既無高山以束之,泥沙壅積,泛濫之患,無歲不有。加以人民日增,土地漸狹,相率以堤防限制河道,乃至河床淤積,歷年遞增。”此實泛濫成災之一因。據《元史·河渠志》載:“盧溝河,其源出于代地,名曰小黃河,以流濁故也。”此外,永定河又有“渾河”之名,“本盧溝水,從大興縣流至東安州、武清縣,入漷州界”。
永定河之得名
從永定河河道的自然條件來看,其山區段為中山峽谷區,山高谷深,天然落差大,水流湍急。進入平原后,水流變緩,加上積年累月,泥沙淤積,致使河床抬高,自盧溝橋以下形成地上河。從石景山麓至盧溝橋以南,金、元、明曾建有石堤工,然而清朝以來久無修防,水勢散漫,中下游河道仍然搖擺不定,洪澇頻發,是一條善決、善徙的河流,對京畿各縣的侵害相當嚴重,所以歷史上又稱“無定河”。康熙三十七年(1698)二三月間,“無定河”自新城九花臺漫決,環繞霸州,水患頻發,康熙帝親臨災區巡視,見田畝淹泡,百姓流離失所,以水藻為食,生計艱難,深為憐憫,即令直隸巡撫于成龍速往渾河決口處詳細勘察。于成龍偕同西洋人安多仔細勘察了自霸州至郎城段的水患,繪制出河圖后進呈。《清史稿·圣祖紀》載曰:“(康熙)三十七年三月辛卯,直隸巡撫于成龍奏偕西洋人安多履勘渾河,幫修挑浚,繪圖呈進。”康熙詳看工程圖后,決心采用挑河筑堤的方法對永定河加以改造,疏浚修筑的河道“自良鄉老君堂舊河口起,徑固安北十里鋪,永清東南朱家莊,會東安狼城河,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達西沽入海,浚河百四十五里,筑南北堤百八十余里”。至七月二十一日,“霸州等處挑濬新河已竣”,巡撫于成龍上書康熙,“乞賜河名,并敕建河神廟”。康熙下旨曰:“照該撫所請,賜名永定河,建廟立碑。”《畿輔通志》記載,自此“湍水軌道橫流,以寧三十年來河無遷徙,此從古所未有也”。
永定河傳說概況
永定河被譽為北京的母親河,其流域內流傳著“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環繞北京灣”的歌謠。永定河傳說誕生于人民的真摯感情中,呈現出一種自然淳樸、雅俗共賞的藝術氣質,是一種新的“民族的詩”。這些民眾以口頭方式創作和傳承的有關永定河的傳說,包含了神話傳說、史事傳說、人物傳說、風物傳說,等等。這些傳說中包含著河道的疏浚歷史及灌溉之利,表達了民眾對于美好幸福生活的希冀與向往。


永定河河道歷史悠久,流經地域廣,跨越眾多省市,自古以來即有“浴水”“?水”“黑水河”“無定河”等多種稱謂。與此相關的命名傳說較多,如《無定河改為永定河》《浴水的傳說》《大黑龍大鬧無定河》等傳說中都提到了永定河各種名稱的由來。其中《大黑龍大鬧無定河》傳說中還描述了永定河獨特的“惡開”現象,認為冬春之際冰雪消融時冰面爆開的情形是河中黑龍在疏浚河道,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
史書載永定河流域“官廳山峽坡度陡峭,兩岸支流為山河,每遇驟雨,一泄無余。下游成水患。上游河底土質多為松泥沙土,一觸即潰。”因而永定河流域多歷史遺跡,如三國時期劉靖開發的戾陵堰和車箱渠、“銅幫鐵底”的石盧段工程、北惠濟祠等。很多永定河傳說則以這些實際存續的風物為“承載物”,講述的內容也大多與水患、治水及護水有關,這種講述實際上喻示著某種群體性內涵,因此也賦予了傳說“地方感”。如《劉靖筑戾陵堰裕民》《康熙皇帝浚河筑堤》《和碩怡親王和北惠濟廟》《會跑的金門閘》等,是基于大量的史實資料撰寫而成的傳說,詳述了三國與清代永定河的疏浚工程;《河擋擋河戲弄劉瑾》一則傳說充分體現了永定河的軍事作用,傳說講到明朝宦官劉謹圖謀泄放永定河之水以謀權亂政,但被河中的護水神靈阻礙。“治水掌故”類傳說還有《康熙下令鑄鐵狗》《于成龍生死不離永定河》《曾國藩修河難如愿》《左宗棠治水有招》《馮玉祥出兵永定河》,等等。
永定河流域的神靈、精怪與神獸亦是永定河傳說的一大特點。“華北諸水,永定為大,而為禍亦最烈”,常年的水災使得民眾相信永定河底臥藏著駭人的水怪。如《大黑龍大鬧無定河》《石景山鎮惡龍》《天河吞水獸》《龐村大廟和鎮河牛》等“鎮惡治水”類傳說,將永定河中的惡龍、烏龜、黑龍等描述為河水潰決的“罪魁禍首”,而將鐵牛、趴蝮(吞水獸)等視為鎮水之神,作為鎮水獸放置在河邊堤岸用來震懾水怪。民間的鎮水獸造型多樣,包括牛、犀、獅子、龍形神獸等,其材質也有石質、鐵質、銅質等。如頤和園中的標志性景觀銅牛,其背部有乾隆所題的《金牛銘》,“夏禹治河,鐵牛傳頌,義重安瀾,后人景從”。鎮水獸廣泛存在于永定河流域的橋、閘、堤壩處,反映了民眾鎮水消災的樸素愿望。如《饕餮鎮水》傳說中的“饕餮”指的就是廣利橋兩側的龍形鎮水獸,民間也將其視為“龍生九子”之一,但其究竟是哪一位龍子卻始終存在著較多爭議。明代楊慎在《升庵集》中列舉了他所記錄的“龍之九子”,即“赑屃”“螭吻”“蒲牢”“狴犴”“饕餮”“蚣蝮”“睚眥”“金猊”“椒圖”,其中“饕餮好飲食,故立于鼎蓋”,而“蚣蝮性好水故立于橋柱”。李詡在《戒庵老人漫筆》中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因此,在楊慎眼中,這些石質的鎮水獸應為“蚣蝮”,而在李詡看來則應為“饕餮”。“饕餮鎮水”傳說中提到,河水的泛濫是鲇魚精作祟的結果,而饕餮的“好飲食”正巧能威脅河妖,鎮壓水患。民眾也希望它能把泛濫的河水吸入肚內,以此鎮壓水患。
此外,人們認為供奉的神靈也具有治水功能,如《衙門口村的雙關帝廟》中的關羽;《北辛安鎮的老君廟》中的太上老君;《雙女墳神丘》中的仙女等,都能夠在永定河流域發生水患時施展神力,化險為夷。這些傳說通過時空交錯的故事和場景,展現了神靈背后的集體記憶和時代投影。以龍王傳說為例,自古以來,永定河畔修建了許多龍王廟,歷經金、元、明、清,現存文獻記載較多的龍王廟主要有四座,分別是門頭溝區三家店的龍王廟;石景山區的北惠濟廟;豐臺區的南惠濟廟;大興區安福莊鄉趙村的永定河河神祠。每年農歷六月十三祭河神,村里村外的人都趕往龍王廟吃筵席,給河神祝壽。相關傳說有《渾河岸邊河神祠》《北辛安龍王廟》《飛龍救婆婆》《河神和神羊》《龍王槐的傳說》,等等。
永定河流域的盧溝橋傳說也因其蘊含的特殊生活記憶一直備受人們關注,早在戰國時期,盧溝橋一帶就是燕薊地區沿太行山脈通向華北大平原的要津,是南來北往的重要渡口。自金朝興建中都城之后,盧溝上的浮橋遠遠不能滿足金朝統治者政治、軍事、經濟上的要求,于是便開始建造石橋。《金史·河渠志》載:“大定……二十八年五月詔:盧溝河使旅往來之津要,令建石橋……明昌三年三月成,敕名曰廣利。”明昌三年(1192)三月建成。初名“廣利橋”,后改稱“盧溝橋”。除藝術欣賞價值之外,盧溝橋建筑技術的高超與精湛亦為后人所稱贊。其橋基和橋身均使用巨大的鐵柱、鐵榫予以拉接補強。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一年(1786)修理橋面時記載:“石工鱗砌,錮以鐵釘,堅固莫比。”1991年修復橋面和清理河床基礎時,果然發現了橋面兩側伏石用鐵桿穿接,橋下基礎用密布的鐵柱層層貫穿,所以在數百年的人馬通行和洪水沖刷下,仍安然無恙。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迎擊初春上游冰融后大量冰凌、冰塊的沖撞,在迎水的橋墩分水尖上,安設了巨大的三角形鐵柱,以其鋒利的尖刃斬凌破冰,被人們稱之為“斬龍劍”。此外,還有被稱之為“插架法”的打“梅花樁”基礎等等。盧溝橋建橋技術之精湛,可以說是達到了當時造橋工藝之高峰。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更使其成為中華民族堅強不屈、抵御外侮的民族象征。
自遼代開始,盧溝橋傳說逐漸以京西永定河流域為核心,散布全國;更因其所承載的民族精神及體現的民族氣節,在東南亞各國及世界華人聚居區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盧溝橋傳說大致可以分為“盧溝橋修建歷史”“盧溝橋上石獅子”“盧溝橋與龍蛇龜獸”“盧溝橋與皇帝、臣子”“盧溝橋與普通百姓”“盧溝橋抗戰事跡”六類傳說。
永定河傳說的文化意蘊
永定河傳說以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價值意蘊,激發了民眾對地方文化的自豪,民眾不僅能夠通過傳說感知地方文化,還能夠在傳說中找尋到靈魂與心靈的歸處。新世紀以來,特別是“永定河傳說”“盧溝橋傳說”相繼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之后,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將傳說文本納入“地方政府文化記憶展示的新秩序”之中。那些包孕著大運河文化特質的民間傳說,承載著運河沿岸民眾的歷史記憶與共同情感,那些融匯在血脈之中的依戀與期待,那些在田間地頭被娓娓道來的帝王將相的治水逸事,那些至今仍舊存續于永定河流域的地方風物,喚醒的不僅是民眾對地方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更是一種“人與地之間情感紐帶”的貫通,真正作為“支撐之物”的還是深蘊在傳說內部的自強不息和艱苦奮斗的精神。永定河傳說的傳承及傳播在不斷喚起民眾集體記憶的同時,也不斷融入民眾的日常生活經驗,這也是傳說得以不斷衍化、傳承的基礎。永定河傳說在歷史與現實的交織、傳承與超越中,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鑄提供了生命經驗和情感紐帶。
(毛巧暉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 研究員)
北京市非遺項目門類豐富,具有多民族、多地域文化交流交融的特色,又兼容并包南北方文化特質。希望通過這一欄目的開辟,使廣大讀者能夠感受到流傳在民眾中口耳相傳的民間傳說、精彩絕倫的傳統技藝、美輪美奐的傳統舞蹈、精雕細琢的手工藝品中那一份厚重的歷史文化內涵。
編輯 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