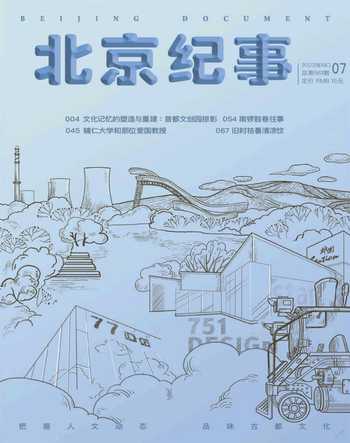南鑼鼓巷往事
就像每個讀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賈寶玉”“林黛玉”“哈姆雷特”一樣,每個與南鑼鼓巷有過交往的人,也必定會有自己心目中的“南鑼鼓巷”。
從革命圣地走來的藝術沃土
這所位于東棉花胡同39號的中央戲劇學院,其前身乃是“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晉察冀邊區“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南京戲劇專科學校”等。1950年各校聯合組建了中央戲劇學院,隨后又改為專門的話劇學院。及至特殊年代,這里曾更名為“中央五七藝術大學戲劇學院”。1978年再度恢復中戲之名。該院的首任院長是戲劇大師歐陽予倩(其故居就在張自忠路北側),副院長乃曹禺。第二任院長是表演藝術家金山。
據說,就在中央戲院建立以前,于同一位置上,曾住過民國時代的國務總理靳云鵬。我對此人的最初印象,是通過在報國寺市場內,淘換到的一枚民國時期的人物郵票。靳爺在其中露了一次臉。
要說起來,這位靳云鵬,早年畢業于北洋武備學堂。就其求學的經歷而言,算是袁世凱的“門下弟子”并不為過。他也確實得到了袁世凱的信賴,進而擔任袁世凱時代的山東都督之職。靳云鵬曾兩次出任國務總理,掌握軍政大權。他是段祺瑞為首的皖系骨干分子,卻跟直系掌門人曹錕拜了把子,又與奉系首領張作霖結成了兒女親家。就在靳大帥于仕途上順風順水之時,買下了東棉花胡同西口的這片宅邸。在他的授意下,一部分四合院被拆除,繼而建造起幾座西式樓房。當然,靳云鵬于此地并未住上多久。待他在民國十年(1921年)辭去要職以后,開始長期居住于天津,直至1951年去世。到了1960年代,靳云鵬所建造的洋樓尚存。再過些年,樓宇便片瓦不剩了。
一方碑石與南鑼鼓巷由來
南鑼是在至元四年(1267)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間建成,這與元大都的建造時間基本一致。到了明代,南鑼鼓巷的巷名為“鑼鍋巷”。至清乾隆十五年(1750)繪制的《京城全圖》上,已經將“鑼鍋巷”更名為“鑼鼓巷”。“文化大革命”時期,南鑼鼓巷曾一度改稱“輝煌街”。后因使用不便,又恢復了原名。
話說回來,明代的“鑼鍋巷”之名,究竟是如何得來的呢?有學者指出,這應該與此處地形特殊有關。南鑼鼓巷南北兩頭低、中間高,路東各胡同西高東低,路西的胡同東高西低。
2006年8月,南鑼鼓巷在進行市政道路改造時,在75號和77號院墻外出土了一塊“水準點”石碑。
所謂“水準點”,是指一個地區海拔高度的基準點,所有地形圖,各種小準包構建筑物以及各等高程控制點,都以此為基準。
北京的水準點始建于1914和1916年之間,是北京地區首次進行的近代水準測量,起算點為正陽門的將軍石,當時全市共埋設了81塊水準點石碑。根據資料顯示,南鑼鼓巷的水準點的高度為50.071米,在此埋設水準點石碑表明此地是北京城里地勢高點之一。而75號和77號院位于南鑼鼓巷中段西側,恰恰說明該巷中間是這一地區的最高點。
以南鑼鼓巷為主干,巷內東西兩側如蜈蚣手足般地伸出八條相對平行的胡同。路西由北至南依次為:前鼓樓苑胡同、黑芝麻胡同、沙井胡同、景陽胡同、帽兒胡同、雨兒胡同、蓑衣胡同、福祥胡同;路東自北及南依次為:菊兒胡同、后圓恩寺胡同、前圓恩寺胡同、秦老胡同、北兵馬司胡同、東棉花胡同、板廠胡同、炒豆胡同。16條排列有序的胡同,被民眾俗稱為“蜈蚣街”。據說以前在南鑼鼓巷的最北端有兩眼古井,恰好就成了這條蜈蚣的兩只眼睛。
與南鑼鼓巷“有緣”的洪承疇
南鑼鼓巷59號,據說是明末清初將領洪承疇家族祠堂的所在地。但從目前的建筑式樣來看,大體屬于清代中晚期。
洪承疇受到崇禎帝賞識,是從鎮壓高迎祥等部的農民起義時開始的。大明王朝的內患頻仍,崇禎帝卻不能一門心思地應對。就在此時,關外的清軍已然能夠隨心所欲地“進出關內”了。到了崇禎十一年(1638)九月,清軍第三次南下,陷真定、廣平、順德、大名、高陽等地,負責抵抗清軍的朝廷重臣孫承宗、盧象升皆亡。至次年正月,清軍又搶掠山東濟南諸城。實際上,按照清軍將領們當時的想法,占據北京也可以辦到,但被皇太極否決。他所采取的方式,是來回掃蕩京畿地區,將北京孤立起來,“砍倒大樹,先斫兩旁”。
清軍的第三次南下,總共俘獲四十六萬人,掠得黃金百余萬兩。面對皇太極的攻勢,崇禎帝不得不從西線將主帥洪承疇調來入衛。時隔未久,洪承疇調任薊遼總督,帶著屢勝農民軍的陜西兵東來。此時,在崇禎帝的眼里,洪承疇不只是“救命稻草”,他簡直就是“鋼鐵長城”。
“鋼鐵長城”是否堅不可摧,松山一戰見分曉。崇禎十四年(1641),清軍第四次南下。皇太極重兵圍困錦州,打算攻破明軍于關外的最后防線。薊遼總督洪承疇親率十三萬軍隊支援,結果與清軍“邂逅”松山。皇太極調集兵馬圍攻,洪承疇寡不敵眾,兵敗被俘。至此,皇太極認定“明軍精銳已盡”。
崇禎帝得到消息,說是洪承疇戰死疆場、為國捐軀。于是,悲痛之中的崇禎帝決定,在正陽門下最熱鬧的關帝廟邊,再建一座用來祭祀洪承疇“亡靈”的廟宇。而當廟宇建成,遵照皇帝旨意進行的一系列喪儀全部舉行之時,崇禎帝卻得到消息:洪承疇不僅未死,而且還投降了滿洲人,做了個“貳臣”。這還得了,甚為尷尬的崇禎帝,下旨拆除小廟不是,留著亦不是。最終,在大臣們的提議下,改祭祀廟為觀音大士廟。

從此,民諺中“九門九廟”之說,便被改成了“九門十廟”。這多出來的一座廟,便是一座帶有尷尬色彩的觀音大士廟。其實,觀音菩薩本身并不會“尷尬”,應感到尷尬者,實乃崇禎帝是也。
洪承疇是怎么降清的?他在被俘之后,曾絕食數日,拒不肯降。皇太極命大學士、吏部尚書范文程前去勸降,看他是否果有寧死不屈的決心。范文程也不提招降之事,只是跟他談古論今,同時悄悄地察言觀色。談話之間,梁上落下來一塊燕泥,掉在洪承疇的衣服上。洪承疇一面說話,一面“屢拂拭之”。范文程不動聲色,告辭出來,回奏太宗:“承疇不死矣。承疇對敝袍猶愛惜若此,況其身耶?”皇太極接受范文程等人的意見,對洪承疇倍加關照,恩遇禮厚,最終打動了洪承疇,成為帶領清軍南下的急先鋒。
后世對于洪承疇的評價,是由乾隆帝一錘定音的,那就是“貳臣”。其實,這個“貳”字既有貶損之意,也帶有一絲尷尬與無奈。畢竟,在歷史長河中,總會有相當多的官員經歷過改朝換代之痛。他們的人生選擇與悲劇命運,是所處時代造就的。
一座小院,不凡主人與“北京猿人”
作為洪承疇家族寓所一部分的南鑼鼓巷59號,在數百年之后,又成為著名的考古學家、古生物學家、古人類學家裴文中教授的寓所。
作為周口店“北京猿人”頭蓋骨的發現者,裴文中教授跌宕起伏的人生命運,或多或少是與“北京猿人”相關的。在特殊年代里,裴文中教授的居住條件十分簡陋。他的南鑼房舍低矮、窄小、擁擠。與他生活在一起的外孫女,甚至沒有安放床的地方,只好睡在廢棄的衛生間中的澡盆里。

居住條件的好壞,似乎并不是裴文中教授最為關切的。于他的心目中,沒有任何事情的分量能超過“北京猿人”。在那段特殊年代里,裴文中對審問他的人講:你們說我是“叛徒”,我可以承認;你們說我是臭老九,我也承認;你們說我是反動學術權威,我還是承認;但你們說第一個“北京猿人”的頭蓋骨不是我發現的,我不承認,打死也不承認!
特殊年代過去,裴文中搬到中關村,生活條件也得到改善。然直至1982年去世前,裴文中心心念念的,仍是尋找“北京猿人”的下落。裴文中教授在彌留之際的最后話語,是“死不瞑目”啊。
“萬慶當鋪”和它的主顧
位于南鑼鼓巷中段路東的“萬慶當鋪”,是家旗人開設的買賣。東家曾在內務府當差,掌管著皇家金庫,居住在南鑼鼓巷的蓑衣胡同。由于家中有錢,附近居民稱其“金王家”。
按照清廷對旗人的要求,除了為官、當兵之外,從事工商業、農業是一律禁止的。清雍正年間,俗稱“內府官當”的皇室內府典當業創辦,用以解決八旗兵丁“人口日繁”而造成的日用困缺、生計艱難等問題。到了清末,許多內務府官員和太監間接經商,與漢民合營并由其出面,開設錢莊、票號、當鋪等。到1900年前后,北京當鋪多達200多家。
當時,南鑼鼓巷東西兩側的達官顯貴,是萬慶當鋪的基本客戶。晚清之際,這些人家因錢糧俸祿日減,不得不將祖輩遺留下來的值錢物品送進當鋪,以維持日常生活。進入民國,“鐵桿莊稼”無存,遺老遺少們進出當鋪更加頻繁。此等業務,一直持續到新中國成立前夕。
2006年7月,南鑼鼓巷胡同整修過程中,工程隊拆出了老當鋪的門臉,“萬慶”字樣的兩塊磚雕也露了出來。
高申,北京城市發展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文物學會會員 ,北京史研究會會員,北京市史地民俗學會會員。
中國文聯出版社簽約作者。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財經之聲”欄目、北京人民廣播電臺“樂行京津冀”“文化之門”“運河”節目嘉賓。北京日報客戶端“光影記憶”“舊京圖說”“胡同冷知識”客座嘉賓。
著有《北京中軸線文化游典·建筑》(北京出版社)、《帶著課本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等圖書,于多家報刊雜志發表文章,并接受《人民日報》等媒體訪談。
我對北京有情,因我生于斯長于斯。我對歷史與考古有意,因我用腳步丈量著這座城市。但是要把“城市”與“考古”相融,卻從未敢想。如今,不妨帶著考古的視角,尋胡同、找名人、觀滄桑、感人情。
編輯 郎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