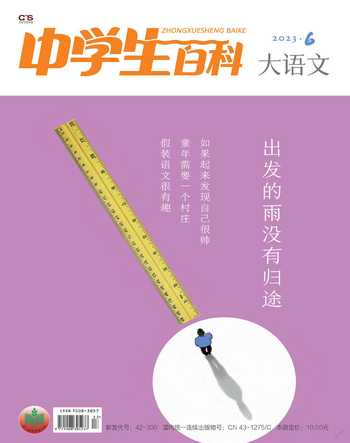動物有情說
梁無猜

“當你沉迷于低級的快樂,你其實沉迷的是屬于動物層次的快樂,你卻忘了人類所應該有的快樂。”中國政法大學羅翔教授這番話是對人類說的,自然沒有貶低動物的用意。只是,快樂真的在動物的情感詞典里嗎?動物層次的快樂又是怎樣的呢?
大蜥蜴在溫暖的環境中會感到快樂,它們會經歷與人感到快樂時相同的生理反應——心跳加速,體溫升高。雖然看起來理由并不充分,但科學家的確是這么下的結論。另外,有研究表明,具有高級情感的動物,正是從爬行動物開始的,可見大蜥蜴除了能體會到快樂的感覺,還有一大串其他的情感體驗。那是不是也意味著,比爬行動物更低級的動物,可能就終生都生活在“一個沒有快樂的星球”呢?果真如此的話,其實也談不上不幸,因為它們也不會在或長或短的生命旅程中與悲傷邂逅。自然的偉力讓它們來世間走一遭,卻忘了附贈它們一本情感詞典。大概,生命的最初本就是無憂無慮、不喜不悲的吧!
關于動物的情感問題,一直以來都存在爭議。有人認為動物的很多情感表達,只是一種本能,是我們的過度解讀讓這些原本屬于本能的行為被視作情感。而如今,一些科學家通過觀察和研究,證明在“豐富的情感世界”里,人類并不孤獨——很多動物以與人類相似甚至相同的方式表達諸如愛、友誼、忠誠等一系列極其復雜的情感。當然,它們也像人類一樣,有貼著生命匍匐而行的苦樂與悲喜,它們也嘗得出孤獨、感動、絕望、驕傲等百般滋味。支持“動物有情說”的代表人物是達爾文,他說:“較低級的動物,也能像人一樣明顯地感覺到快樂與痛苦,幸福與悲傷。”
跟人類相比,動物的情感詞典或許是簡化版本,有所刪減,但很多個體所演繹的故事已然足夠動人。日本有一則民間故事,說的是一只被釘在墻上無法掙脫的壁虎居然長時間活了下來,活了五年。這只壁虎之所以在生命的死胡同里創造奇跡,靠的不是勇氣和毅力,而是另一只壁虎持之以恒的“投喂”。故事自然不能視為現實,但類似的例子在有血有肉的自然界并不罕見。
動物行為學家用一幀幀真實的畫面,為我們展示動物情感世界的充盈內涵:“母猴懷抱死去的幼猴孤零零地呆坐山頭,絕望與悲傷中夾雜著無聲的祈禱,希望自己的孩子活過來。”“歐洲有一種白頭翁,雄鳥從遠處飛回來,總不忘帶上一枝鮮花獻給情侶,那種愛的深重與熱烈如童話一般羨煞旁人。”“非洲有一種駱駝,懂得尊敬老者。只要有年老的駱駝在,大家都不會躺著。偶爾有不懂禮貌的小駱駝躺倒,旁邊的駱駝就會催促它趕緊站起來。”當然,也有人認為這些動物的行為跟情感無關。事實上,從人類的視角否定動物世界這些生動鮮活的情感表達,是兼具運動員和裁判員雙重身份的人類的自傲與偏見。就連達爾文也不得不承認,人的情感在進化過程中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源自動物祖先的情感。所以說,人類的任何一種情感其實也都是可以沿進化樹向前溯源的。
倘若把情感的定義擴展得更寬泛,大多數人并不會否定或懷疑動物是有情感的。比如你突然靠近家里的金魚缸,就會有來自金魚的情感漣漪泛起。沒錯,就是恐懼。這可能是我們最容易求證的動物情感了。不過,恐懼是一種初級情感,是動物在神經系統或激素的調節下對環境變化所做出的反應。那么,讓情感更進一步又會是什么局面呢?我們都見識過動物的憤怒和絕望,但我們并不容易從邏輯上證明,因為“憤怒”和“絕望”由人類創造和定義。再比如說動物世界里的有情,那些被傳為佳話的故事的底色果真就是“有愛”嗎?
在“愛狗圈”有個故事被人津津樂道。故事源于英國《太陽報》的一篇報道。英國薩羅普郡的一只名為莉莉的大丹麥犬,在18個月大的時候不幸患上了無法治愈的眼病,為防止感染,摘除了眼球。失去光明的它陷入了消沉,以至于茶飯不思,體重下降。往后余生于它而言似乎沒了意義。好在導盲犬麥迪遜走進它的生活,開始充當它的眼睛。麥迪遜會把好吃的讓給它先吃,會經常帶它出去玩耍,靜下來的時候,會有意無意地用自己的身體去蹭它的身體,似在給它安慰與溫暖,似在告訴它,黑暗世界也有長情的陪伴。漸漸地,失明的莉莉找回了往日的活力與光彩,重新變得樂觀起來。不得不說,這的確是一個感人的故事。
問題在于,盲犬莉莉和它的導盲犬麥迪遜之間真的存在友情嗎?我們沒辦法證明,科學家也束手無策。雖然狗跟人類足夠親近,但并沒有親近到可以就友情的真偽與我們深入探討的地步。所以說,對動物的情感,特別是動物的高級情感的證明,最好的方式不是科學研究,而是理解。只有像理解人類自身的情感一樣去理解動物的情感,認知和定義上的隔閡才會消除。然后你甚至會發現,理智感、道德感、美感這些高級情感在一些動物行為中似乎也顯而易見。哪怕討論作家周國平對高級情感的定義,動物也不一定就應該被排除在外。周國平說:“低級情感是一己的恩怨悲歡,高級情感是與宇宙眾生息息相通的大愛和大慈悲。”如果以一顆柔軟之心去尋找共情,你也許真的可以于童話世界之外在動物身上感受到大愛和大慈悲。
總之,我們都不相信動物是“冷冰冰”地與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個藍色星球上的,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