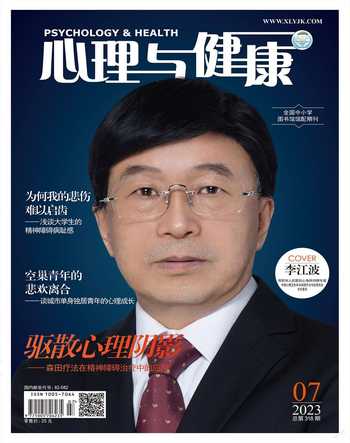你的記憶也會“說謊”嗎?
邱翠微

人們會對自己的記憶堅信不疑,認為記憶就像一卷心理錄像帶,忠實地復制了過往事件。然而,人們關于復雜事件的記憶基本上是一個重構過程。
人腦平均能存儲100萬億比特的信息,管理如此大批量的信息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回憶以一定的方式組織存儲信息是為了便于理解現(xiàn)在,因此我們編造了關于生活以及現(xiàn)實世界的故事,使記憶與故事相互吻合。總體而言,我們的記憶存在偏差。
記憶偏差是如何產(chǎn)生的?
記憶是在頭腦中積累和保存?zhèn)€體經(jīng)驗的心理過程,從信息加工的角度看,是對輸入信息的編碼、存儲和提取的過程。過程中的任何缺陷都可能導致記憶的偏差。下面我們從這些基本過程中解開記憶產(chǎn)生偏差的謎題。
1注意選擇性提供了過濾
如果你想記住某一信息,通常你需要注意它。
人的注意力有限,這就決定了人不能對所有信息進行注意,選擇性注意對人們的日常運作尤為重要,也就是說你需要過濾掉身邊的大部分信息,只讓一小部分進入意識。
注意的選擇性對編碼的作用如同過濾器,只有經(jīng)過選擇以后的信息,才能受到進一步加工、處理。這表明了為什么人們對世界的經(jīng)驗是主觀的。在很大程度上,你所看到的事物取決于你所關注的內(nèi)容。隨著時間推移,那些突出和過分強調(diào)的某些細節(jié)將服務于人們的記憶動機,被記住的信息就可能出現(xiàn)偏差。
2想象可得性提供了便利
我們?nèi)粘I钪凶龀龅脑S多判斷都以記憶為基礎,即利用過去習得并存儲于長時記憶中的相關信息做出簡便的檢索提取,以應對判斷任務。這種簡單的聯(lián)想思維被稱為可得性啟發(fā)式。
當意識努力從記憶中提取信息時,我們有時會依賴于提取的流暢程度,有時會依賴于即刻闖入腦海的事例。此時,人們需要回憶表現(xiàn)出果斷性,但人不可能記住一生中所有的事,遺忘是很正常的。這種時候,就有可能發(fā)生錯憶,把想象和真實混淆,歪曲事實。
有研究發(fā)現(xiàn),失憶與錯憶是兩個互補概念,當記憶中出現(xiàn)大段缺失時,錯憶是為了填補記憶空缺而出現(xiàn)的毫無根據(jù)的記憶,也就是“腦補”,因此“想象”在判斷可能性時存在著缺陷。
3記憶重構性提供了后見之明
后見之明偏差是指個體在知道事情的真相或問題的結果后,高估自己過去的預測能力的傾向。即知道事件結果之后做出的判斷與未知事件走向時的判斷之間存在的系統(tǒng)差異。“我早就知道了”,但其實我們并不清楚自己知道什么,尤其是在已經(jīng)知道事件發(fā)生結果的情況下。
這也就是我們說的“事后諸葛亮”。當我們相信某件事情已經(jīng)發(fā)生時,我們會傾向于扭曲過去,以使之與事件結果相一致。回憶是為了便于理解現(xiàn)在,因此強化了我們關于過去如何決定現(xiàn)在的信念。正如在對歷史事件、政治選舉、比賽排名等事件的判斷中,人們都會在得知事件結果后高估自己過去做出正確預測的可能性。
記憶偏差對我們的影響
● 影響判斷與決策?
記憶可以激發(fā)情緒,記憶向我們提供的“真實”信息會影響我們的想法與感受,而情緒也可以反過來左右記憶。當帶著主觀感受與明確的目的去探訪記憶時,我們會通過某些方式對經(jīng)歷過的人或事加以“解釋”,而真實發(fā)生的事情與大腦推理后認為應該存在的事情往往很難區(qū)分。
比如,英國華威大學的心理學家就曾經(jīng)成功地給人植入虛假的童年回憶。心理學家向?qū)W生父母咨詢并確認了部分學生沒有乘坐過熱氣球的經(jīng)歷。然后,心理學家通過技術把那部分學生兒時的形象放進正在飛行的熱氣球的籃子里,再把這樣的照片拿給學生看。兩星期后再次訪問學生,有的學生就能以令人驚訝的細致程度虛構出小時候乘坐熱氣球的經(jīng)歷。
倫敦大學學院的心理學家甚至能夠讓人們相信自己有過從未發(fā)生過的暴力犯罪。他利用記憶檢索技術,讓參與者在三次訪談中都被問及暴力犯罪的問題。其中70%的人會產(chǎn)生自己年輕時犯罪的虛假記憶,有些人甚至相信自己曾用武器攻擊過他人。
由此可見,當我們從別人那里獲得間接信息時,自己的期望與別人的暗示都會使我們產(chǎn)生記憶偏差。再加上情感、道德、思維方式等因素干擾,我們的記憶與真實可能相差甚遠,并據(jù)此做出錯誤的判斷和不恰當?shù)男袨椤?h4>● 影響司法裁決
在牽動整個美國社會的辛普森謀殺案的審判中,瑪西亞·克拉克作為起訴人做出了最后陳詞,原原本本地總結案件的經(jīng)過,包括完整的時間表。相比之下,辯護律師約翰尼·科克倫則力勸陪審團,在法庭上有義務保護那些受迫害的少數(shù)種族,甚至為他們復仇。事件激發(fā)的情緒對記憶有長遠的影響,進而影響到根據(jù)記憶所做出的判斷:當我們處于一種特定的情緒狀態(tài)時,會傾向于記住與情緒狀態(tài)主題一致的事件。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原則很簡單,歪曲時常不需什么精美的操縱就能發(fā)生,簡單重述一遍故事就能使記憶變得不準確。當人們復述故事時,往往會按照他們的目標、聽眾和社會情境而做出一些“調(diào)整”。我們知道記憶的正確與否決定于編碼時的注意程度以及編碼和提取的環(huán)境匹配程度,即使在人們熱切地希望說真話時,他們也有可能無法報告“真相”。
如何讓我們的記憶變得可靠?
在日常生活中,多數(shù)人一旦得出了自己認為是正確的答案,就立馬停止了對記憶的搜索。因此,認識你的記憶可能有偏差需要運用一些批判性思維技能。
理解人類記憶的局限性和易繆性
即便是目擊證詞也可能是扭曲或不準確的。因為目擊者對事件的回憶常常會因事后引入的信息發(fā)生扭曲,這些事后信息可以來自警官、律師、新聞報道等。
認識后見之明分析中的偏見
得知事件的結果后,會給我們對此事件的回憶和闡釋帶來偏見。“事后諸葛亮”會讓你帶有偏見地回憶該事件是如何發(fā)生和發(fā)展的,以及你當時在想什么。借著事后聰明帶來的優(yōu)越感,人們在解釋事件時會聲稱“我早就知道了”,盡管從客觀上來看我們很難預知事情的走向。
認識人類認知中的過分自信
明白人們經(jīng)常自信地認為,自己對未來的憧憬和對過去的回憶是準確的。一個造成人們過分自信的原因是他們無法找到自己可能出錯的原因。所以,過分自信又源自另一個常見的思維錯誤—— 不能尋找反駁證據(jù)。
理解尋找反駁證據(jù)的需要
思考自己可能會怎么犯錯或者為什么會犯錯是有價值的。為了對你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事情做出更準確的判斷,你需要再三考量自己為什么可能錯了。
現(xiàn)在你知道了記憶不像自己認為的那樣可靠,了解了記憶的多面本質(zhì)及其對我們行為的主宰之后,就可以運用一些批判性思維技能來影響自己解決問題、思考問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