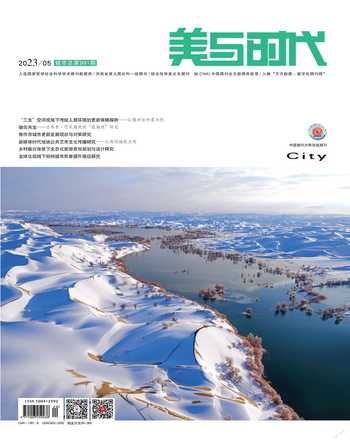迷霧中的現(xiàn)代性:新地形學攝影中的重慶景觀
賀琳娟 劉斯博

摘 要:進入21世紀后,以中國為題材的新地形學攝影佳作頻出,而在這當中,又以重慶為最重要的取景城市之一。那么,重慶到底提供了哪些與眾不同的現(xiàn)代性審美議題,從而引得大批攝影師爭相奔赴?他們又是如何通過個人化的影像語言來描述與重構(gòu)這座城市的? 本文針對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從三峽庫區(qū)的涅槃重生景觀、山水城市的魔幻現(xiàn)實景觀、城鄉(xiāng)交錯的融合共生景觀三個方面梳理、研究了新地形學攝影中的重慶景觀,試圖回答上述疑問。新地形學攝影中的重慶景觀。
關鍵詞:新地形學攝影;重慶景觀;現(xiàn)代性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2—2023年度重慶對外經(jīng)貿(mào)學院科研項目“新地形學視域下當代攝影中的重慶景觀研究”(KYSK202230)研究成果。
1975年,在“新地形學:人為改變的風景的照片”(New Topographics:Photographs of a Man-Altered Landscape)展覽中,策展人威廉·詹金斯(William Jenkins)引入了“新地形學”這一跨學科術(shù)語,意指攝影師通過地理測繪式冷靜客觀的視角,以理性的目光觀察人類介入自然環(huán)境后的種種現(xiàn)實。今天,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新地形學攝影依然具有廣泛而深入的影響力。攝影師多以某一地域為線索,擺脫對自然的唯美再現(xiàn),用無表情、非敘事的中性立場展開對現(xiàn)代化進程的審視和批判,從中反思發(fā)展的代價,并帶來了風格上新的可能性。
顯然,中國的現(xiàn)代化劇變引起了中外攝影師濃厚的興趣。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以中國為題材的新地形學攝影佳作頻出,如納達夫·坎德(Nadav Kander)的《長江》、曾翰的《超真實中國》、駱丹的《318國道》等。其中有一個現(xiàn)象,即重慶這座位于中國西部腹地的“巨無霸”之城頻繁出現(xiàn)在攝影作品當中。那么,重慶到底提供了哪些與眾不同的現(xiàn)代性審美議題,從而引得大批攝影師爭相奔赴?他們又是如何通過個人化的影像語言來描述與重構(gòu)這座城市的?本文將從三個維度對新地形學攝影中的重慶景觀進行探討。
一、三峽庫區(qū)的涅槃重生景觀
1997年,為了統(tǒng)籌三峽庫區(qū)的移民搬遷等問題,重慶被設立為直轄市,三峽也成了這座城市的底色。作為一項世紀工程,三峽可以被看作當代中國的一座模型。宏大的家國敘事同微觀的肉身體驗在這里碰撞。因此,自2000年以來,眾多攝影師進入三峽地區(qū),他們摒棄了瑰麗雄渾的風光,而是從問題出發(fā),思考現(xiàn)代性背后的代價。從涅槃到重生,三峽在攝影師的鏡頭下被賦予了一層憂郁的浪漫主義色彩。
顏長江的“三峽”系列攝影構(gòu)圖方正端莊,影調(diào)冷峻凝重,飽含矜持纏綿的情緒。肖萱安的《156水位線下的風景》以清冷的色彩、極簡的構(gòu)成,觀望著即將被淹沒的江灘、人去樓空的街鎮(zhèn)。黎明的《家園》使用大畫幅相機,以俯瞰的視點、開闊的相場、灰白蒼茫的色調(diào)將異化的三峽景觀融入如素描般古拙質(zhì)樸的情懷里。顏長江、肖萱安、黎明都是地道的“三峽人”,因此對于家鄉(xiāng)的天翻地覆,他們的感情比旁人更加深切和復雜。從地理家園到精神家園,三峽成為他們觀看世界的原點。但是他們的抒情和鄉(xiāng)愁是內(nèi)化的,是一種跳脫了原境的上帝視角。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他們將對三峽的情感隱藏在理性背后。正如顏長江所說:“我在三峽,多少經(jīng)歷最后都化為一張冷風景。其實,道是無情卻有情。外冷內(nèi)熱,這是景觀攝影的要處。無表情,不是無情;新地形學,不是只是地理攝影。”
攝影師曾翰的“酷山水”系列聚焦的是蓄水后的三峽。在創(chuàng)作中,他借鑒了北宋畫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和南宋畫家夏圭的《長江萬里圖》等中國繪畫的長卷形式,使用624的寬幅全景相機,從三峽大壩到朝天門碼頭一路溯流而上拍攝,最終以十張照片組成了《三峽止水圖》。他曾寫:“從2005年起我嘗試將類型學、新地形主義和傳統(tǒng)山水散點透視法融會貫通,以山水長卷的方式拍攝蓄水后的三峽庫區(qū)。”經(jīng)過改造,此時的三峽已呈現(xiàn)出“高峽出平湖”的壯景,之前的長江在此已被徹底淹沒,眼前是像鏡子一樣光亮平靜的水面。“蓄水之后的三峽有一種喧囂之后的鎮(zhèn)靜,正所謂靜水深流,潛流暗涌,我越是冷靜地拍攝這山水,而這山水卻在對著我‘此恨綿綿無絕期地欲說還休。”
這里筆者想單獨提一下位于重慶奉節(jié)的三峽移民紀念塔,這一建筑場景曾出現(xiàn)在多位攝影師的作品中,如駱丹《318國道(2006年5月13日重慶奉節(jié))》、納達夫·坎德《長江》、曾翰《酷山水05-三峽止水圖-三峽移民紀念碑》、黎明《三峽情景系列之奉節(jié)2007》、劉珂《平湖·移民紀念塔2007》等。該建筑由13層大小不一的混凝土方盒疊加而成,整體設計形似繁體的“華”字,其后現(xiàn)代主義的造型顯得與三峽的山水人文環(huán)境格格不入,充滿了一種神秘的未來感。紀念塔于2003年完成主體框架后停工,2008年被爆破拆除,在它短暫存在的五年間,只以未完成的水泥色爛尾樓形象示人,似乎又與這里大拆大建的氣質(zhì)水乳交融。因此,攝影師們不單單是不想錯過這一戲劇性的景觀,更是想為變遷的中國留下證據(jù)。
二、山水城市的魔幻現(xiàn)實景觀
重慶是山城,山水匯聚、峽高谷深是它典型的自然特征。如此的地理條件原本為建造城市設置了巨大的障礙,然而“人定勝天”的豪言壯語卻在此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凌霄盤旋的高架橋梁、獨一無二的立體交通、垂直層疊的建筑空間等景觀在不斷突破著人們的經(jīng)驗,形成一座猶如存在于未來的朋克之城。重慶也是霧都,氤氳的水氣自然屏蔽了多余的物象,為攝影這一“減法的藝術(shù)”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籠罩在云霧中的城市猶如一座巨大的迷霧劇場,朦朧,凜冽,詩意。
以色列攝影師納達夫·坎德拍攝的《長江》曾獲得世界環(huán)保攝影獎(Prix Pictet),他在2006—2007年間五次來到中國拍攝,其中重慶就到訪過三次,是其最喜歡的臨江城市。他拍攝了建設中的朝天門大橋、嘉陵江上高聳的路基,癡迷于表現(xiàn)這里混凝土與自然界在山水間的博弈現(xiàn)場。“搞我這種攝影,中國似乎就是我的一個自然的去處。能拍出我常拍的那種不安與質(zhì)疑,引人思索、回應。我選擇長江作為我的拍攝地,就是想以奔流的江水作為中國飛速變化的隱喻。”納達夫·坎德以局外人的視角表現(xiàn)出對中國的窺探,他受到英國現(xiàn)實主義風景畫家康斯特布爾和德國浪漫主義風景畫家弗里德里希的影響,從遠處凝視那些凝視風景奇觀的人物背影,表現(xiàn)出宏大場景與渺小人物的對比。他的構(gòu)圖空曠干凈,色調(diào)暖灰而清淡,在優(yōu)美與崇高中流露著淡淡的憂傷。納達夫·坎德說道:“在我自身的生活與個人經(jīng)歷中,也有一些東西是與此相通的,而這恰恰觸發(fā)了我身上的某種傷感的情緒。因此我對自己的所見所為有了更多的認識,而最近兩次在中國的旅行中,我的作品也因此變得更加簡練清晰起來。”
嘉陵江和長江在重慶匯合,形成了兩江四岸的城市格局。法國攝影師賽勒斯·科努特(Cyrus Cornut)的《重慶,逝水四岸》即從這四邊江岸出發(fā),記錄了飛躍江面的路網(wǎng)、鱗次櫛比的建筑、千篇一律的樓盤,觀察著城市化速度是如何淹沒人們緩慢而傳統(tǒng)的生活節(jié)奏,試圖以詩性的鏡頭沖破籠罩著它的現(xiàn)代性迷霧。他在自述中寫:“只有幾近狂野的河岸既抵抗著變幻無常的河流,又與其保持著結(jié)盟。坐在堤岸上的人們看著它蜿蜒前行,看著越來越稠密的河岸阻擋著他們的視線。在這里,人們?nèi)匀辉诓藞@中耕種著一些作物,并宿命地等待著最后一塊裸露的土地消失。”
愛沙尼亞攝影師亞歷山大·格隆斯基(Alexander Gronsky)關注地理環(huán)境是如何影響居民的情緒和行為。“山水”系列展示了他在重慶的探索。街道、河流、房屋、山地、工廠、森林……它們相互穿插,相互干擾,錯綜復雜,共存共生,形成奇妙的并置關系。高架橋下的廠房、排水渠旁的居室等頗具反烏托邦的味道。“山水”系列的形式也十分別致,攝影師通過精湛的接片技術(shù)在同一視點拍攝2—4張膠片,形成橫排雙聯(lián)(或三聯(lián)、四聯(lián))的組合。照片既具有獨幅性,又在一組的編輯中完成了對話。這種引導觀眾橫向觀看的方式,也暗合了中國山水長卷的閱讀習慣和美學意蘊。
三、城鄉(xiāng)交錯的融合共生景觀
重慶展示了這樣一種包容性:人們可以在繁華的CBD旁看到原生態(tài)的菜地,也可以在區(qū)縣旅游時一起看到變形金剛和飛天仙女。鄉(xiāng)土既在地理空間上頻繁與城市化的區(qū)域接合交錯,又在文化空間上滲透進城市的文脈,呈現(xiàn)出城鄉(xiāng)間融合共生的視覺層次。這樣的景觀特質(zhì)也為新地形學攝影注入了別樣的意趣,使觀眾在妙趣橫生的“土味”間感受著這座城市的豁達耿直,也回味著農(nóng)耕文明與工業(yè)文明中間的緩沖地帶。
法國攝影師蒂姆·弗蘭柯(Tim Franco)在2009—2015年間完成了“蝶變”系列作品。他將鏡頭對準了重慶的“都市農(nóng)業(yè)”景觀,記錄了這座城市怪異、輝煌、兼收并蓄的城市風格。一方面,由于城市迅速向農(nóng)村擴張,原有的土地被包圍、分割成微小的單元;另一方面,隨著大體量的農(nóng)民搬進城市,他們依然想在樓宇間開墾出一方天地,以還原他們本來的生活方式。并且受制于山地環(huán)境,重慶不像平原城市那樣具有高度集中的硬化覆蓋率,在水泥森林的縫隙間依然存在眾多坪、坡、溝、坎,為“發(fā)展農(nóng)業(yè)”提供了便利。因此,“都市農(nóng)業(yè)”現(xiàn)象在重慶蓬勃興盛。“他們開始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種菜,在建筑工地上,在路邊——任何地方,在巨大的、千篇一律的現(xiàn)代化大廈的陰影中,生長出一片片田野。”蒂姆·弗蘭柯將這種農(nóng)業(yè)文明和都市文明既沖突又和諧的場面表現(xiàn)得有趣而迷人。他使用方形構(gòu)圖,一分為二描述“農(nóng)業(yè)”和“都市”,在自由與秩序、原始與現(xiàn)代、生機與冰冷、肉身與工業(yè)、飽和與灰調(diào)、開闊與密集的對比中形成令人無法抗拒的影像。
洋人街是位于重慶南岸城鄉(xiāng)接合部的一處主題游樂園,以混雜了各種不同風格、不同年代的山寨、夸張的建筑、雕塑和陳設而聞名,加之重慶獨特的地貌環(huán)境,使其成為奇詭又妙趣橫生的地方景觀。不同于迪士尼和歡樂谷,洋人街粗糙、野生,以非理性的審美范式打破了城市空間文明的秩序,充滿城鄉(xiāng)對撞的視覺張力,成為重慶城中的“異托邦”。攝影師華偉成長期關注這里,他從中選取了幾處在他看來別有意趣的場景,通過攝影、手繪地圖、虛構(gòu)故事等手段創(chuàng)作了《洋人街十二景》。在作品中,華偉成以雅致逸趣命名了十二處代表性景點,表面上看似為洋人街披上了文化的外衣,實則是以戲謔的姿態(tài)重建了審美經(jīng)驗與魔幻現(xiàn)實之間的鏈接。
四、結(jié)語
新地形學攝影中的重慶悲情、魔幻、有趣。作為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人工與自然纏斗的修羅場,重慶這座“大城市、大農(nóng)村、大山區(qū)、大庫區(qū)”并存的超級城市為新地形學攝影提供了立體豐富的可能性。浸潤在迷霧中的景觀在此更加祛魅,現(xiàn)代化帶來的矛盾在奇異、失序、混沌的地景中被審美化,成為可被觀看的文本。這迷霧不僅是天氣,也是對現(xiàn)代性的不確定與懷疑,是對危機的追問。而攝影師的使命,正是撥開現(xiàn)實的迷霧,直指現(xiàn)實的真相,因此他們在重慶的實踐并沒有陷入對地方文化獵奇僵化的采風,而是用一種國際通識的當代藝術(shù)語言將在地性問題投擲到全球化的語境中,以回應今天人類所面對的普遍性問題。羅伯特·亞當斯(Robert Adams)在《把它作為家園》中就曾表示:“面對‘天堂不在的現(xiàn)實,(要求人們)以一種更積極的態(tài)度去正視發(fā)生在‘家園里的一切,而不是以被人稱為‘糖水照片的東西制造假象,回避表態(tài)。”隨著重慶近年來愈發(fā)火爆,以其為題材的新地形學攝影也不乏同質(zhì)化、流行化等趨勢,但換一個角度看,這不僅為這座城市留下了一份歷史檔案,更是通過對地理形貌的“測繪”而直面未來,并最終指向人的發(fā)展(圖1)。
參考文獻:
[1]顏長江.祛魅而圣:被稱作景觀的風景攝影[J].中國攝影,2020(6):40-49.
[2]曾翰.風景、景觀、山水:一種文化的隱喻與洄游[J].中國攝影,2018(11):94.
[3]布萊克威爾.攝影的智慧:當代攝影大師眼中的攝影藝術(shù)[M].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2.
[4]顧錚.風景本身就是問題:有關風景攝影的筆記[J].中國攝影家,2010(4):6-9.
作者簡介:
賀琳娟,碩士,重慶對外經(jīng)貿(mào)學院藝術(shù)設計學院助教。研究方向:美術(shù)學。
劉斯博,碩士,四川美術(shù)學院實驗教學中心助理實驗師。研究方向:美術(shù)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