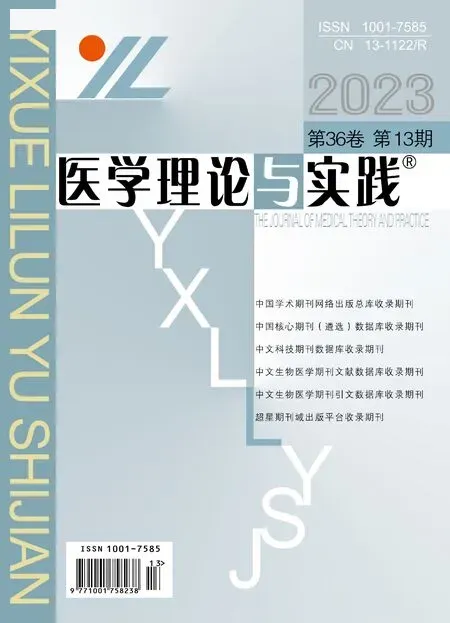女性月經性癲癇的診治進展
樊 珂 董 斌
安徽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安徽省合肥市 230092
癲癇(Epilepsy)是一種有著不同病因基礎,臨床表現各異,但以反復癲癇發作為共同特征的慢性腦部疾病狀態。月經性癲癇(Catamenial Epilepsy)是女性癲癇的一種特殊類型,其發作頻率往往與月經周期的某一時期呈密切相關。隨著臨床病因診斷、動態腦電圖、生物標志物等診療技術的飛速發展,月經性癲癇的診療水平不斷提高。相比起男性患者,女性患者存在特殊的生理周期內分泌特點,同時女性還需要考慮妊娠、遺傳、容貌體型等方面的問題,了解癲癇發作和月經周期的關聯機制有助于制定月經性癲癇患者的治療策略,能及時預警癲癇發作,加強預后管理則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目前國內對月經性癲癇的相關研究有限,本文圍繞月經性癲癇的概念及分型、近些年的診斷治療、預后管理等方面的進展展開綜述。
1 月經性癲癇的概念和分類
月經性癲癇是已知的最古老神經系統疾病之一,在20世紀末Herzog等人[1]對184名患有難治性復雜部分性癲癇的女性進行評估,通過對癲癇發作頻率數據、月經記錄和黃體中黃體酮水平結果的分析,認為月經周期中癲癇發作呈現周期性惡化,當發作頻率比基礎頻率增加2倍以上提示月經性癲癇可能性較大。同時Herzog等人結合女性正常月經周期的四個階段進一步分類出月經性癲癇的三種模式:即C1月經期型:在月經來潮前后,孕激素及其衍生物含量減少,癲癇發作惡化,是最常見的類型;C2排卵型:排卵前雌激素水平升至高峰,癲癇在排卵前加重,但月經來潮前后正常;C3黃體功能不足型:黃體功能低下無反射性排卵,孕激素水平較低,在整個月經周期的后半期癇性發作頻率明顯增加。該項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考慮了耐藥性顳葉癲癇患者,并且僅評估了1個月經周期[2]。盡管當前各界對月經性癲癇的臨床觀點不盡一致,但是與月經期有時間關聯的周期性發作規律逐漸被普遍認同,成為“月經性癲癇”概念的基礎。
2 月經性癲癇的診斷
完整的診斷程序需要4個步驟:(1)患者確診為癲癇;(2)既往有明確與月經相關發作時間規律病史;(3)常規檢查顯示有病灶或異常放電;(4)對確診患者進行發作分類[2]。相較臨床上常見類型的癲癇,月經性癲癇的診斷更強調對既往月經史和癲癇發作史的整理比對、血清激素水平變化測定、體內AEDs血清濃度變化測定等特殊檢查,這些都與月經性癲癇的發病機制密切相關。
腦電圖檢查對于診斷癲癇有決定性作用,對于一些未出現形態學改變的癲癇病灶,早期腦電圖檢查可及時捕捉異常的放電活動,從而快速定位相應病灶部位。既往有研究報道月經性癲癇的發生率以顳葉癲癇較高,并且左側顳葉起始的癲癇發作較右側常見[3]。Fedele等人試圖對顳葉癲癇(TLE)患者的卵巢周期定量腦電圖(qEEG)變化進行評估分析[4],根據發作是否在C1時期將35名顳葉癲癇女性患者分成C1型顳葉癲癇和非C1型顳葉癲癇,結果發現與C2和C3型相比,C1型顳葉癲癇患者在時間衍生方面的alpha MPS顯著降低,theta MPS顯著升高。M期α節律的降低推測可能是C1型顳葉癲癇患者發作的原因,這種特殊的qEEG模式可以作為C1模式的生物標志物,有助于和其他模式的月經性癲癇進行鑒別。目前對這一手段的應用相對較少,未來還需要更多相關的臨床試驗進一步證實。
大部分癲癇患者的不良臨床表現往往在監測一段時間后才發現,因此需要借助某些生物標志物來更早地預測不良反應[5]。Fedele等人發現不同模式下的月經性癲癇發作患者的心率變異性(HRV)存在不同。HRV與心臟自主活動有關,可用于評估心臟自主控制,女性體內生理激素的變化可能會影響HRV,增加了癲癇易感性,可能是癲癇猝死的一個生物標志物。有診斷為C1型顳葉癲癇的女性患者HRV降低[6],有助于和另外兩種模式的月經性癲癇進行區分。
3 月經性癲癇的治療和預后

3.1 藥物治療 目前尚無官方批準專用月經性癲癇治療的藥物,仍以常規抗癲癇藥物(AEDs)為主,療程中強調以單藥為主。但AEDs普遍療效不佳,患者多在治療一段時間后表現出耐藥性。丙戊酸鈉是全球范圍內最常用的一類不含氮的廣譜抗癲癇藥,然而對女性癲癇的毒副作用也較明顯,包括多囊卵巢綜合征(PCOS)、下丘腦閉經、過早絕經、功能高乳素血癥等[8]。2018年歐洲藥品管理局(EMA)就丙戊酸在育齡期和妊娠女性患者中采取全新限制措施,指出患者僅在無其他合適的替代藥物時方可使用,育齡期女性使用時應嚴格避孕且較小劑量[9]。一些新型抗癲癇藥物的應用被證明對月經性癲癇患者有良好的療效。拉莫三嗪是一種電壓依賴型的鈉通道阻滯劑,在神經元中可反復放電抑制谷氨酸病理性釋放或抑制谷氨酸誘發的動作電位爆發,具有較好的抗癲癇作用,并且在穩定情緒、修復認知功能方面常優于其他AEDs[10]。對于有生育需求的患者拉莫三嗪和左乙拉西坦可作首選推薦用藥,但是較高劑量的拉莫三嗪可導致嚴重先天性畸形。因此權衡好控制癲癇發作用藥水平和AEDs的潛在致畸風險成為臨床醫師的工作重點。國外關于提取AEDs與人體相關的基因組信息作為潛在生物標志物來指導女性癲癇患者的個體化給藥的相關試驗正在研究中[11],將有助于未來臨床醫師對癲癇患者進行精準擇藥、早期不良風險規避和靶向治療。
3.2 孕激素及神經類固醇相關治療 在常規藥物治療的基礎上,還可考慮進行孕激素輔助療法。鑒于孕激素的鎮靜、抗驚厥效果,在月經期保持較高的孕激素水平有助于減少癲癇發作。韓國忠北大學醫院報道了2例通過孕激素聯合AEDs治療成功緩解癲癇發作的月經性癲癇病例[16],2名患者分別診斷為特發性全面性癲癇和青少年肌陣攣性癲癇且通常在月經來潮左右發作。在使用丙戊酸鈉、左乙拉西坦等AEDs效果不甚滿意的基礎上分別在黃體期均輔助添加醋酸甲羥孕酮10mg,經過1年維持治療后其中一名患者聚集性肌陣攣頻率減少,另一名患者盡管發作頻率未見明顯改變,但月經周期變得規律,恐懼情緒之前好轉。表明在黃體期孕激素和AEDs聯合治療有較好的耐受性和安全性,也為相關病例治療提供了用藥經驗。此外,曲普瑞林、戈舍瑞林等人工合成的GnRH類激素在20世紀末也被證明在月經性癲癇的治療上發揮作用。
神經類固醇是在膠質細胞內由膽固醇經過一系列酶促反應合成,包括孕激素、雄激素、腎上腺皮質激素等的衍生物等。在Reddy等人20余年的專業研究下,基于神經類固醇撤退(NSW)機制創造性地提出了“神經類固醇替代療法(NRT)”[17],發現神經類固醇或合成物在月經性癲癇動物模型中表現出較強的抗驚厥活性。進一步觀察發現神經類固醇的抗癲癇活性的性別差異顯著,女性較男性更為敏感[18]。這也為針對癲癇發作的個性化神經類固醇替代療法具有重要意義。加奈索酮是別孕酮類似物,耐受性良好,藥物相互作用較低,可以較好地與AEDs一起使用,不良反應有輕度鎮靜和嗜睡,目前正處于抗癲癇治療的臨床試驗中。此外四氫孕酮、布瑞諾龍也是當前的神經類固醇熱門開發產品,在月經性癲癇領域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19]。
3.3 其他治療 生酮飲食療法是治療癲癇的一種古老方法,即通過攝入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適當蛋白質的飲食誘導脂肪代謝和酮體產生從而控制癲癇發作,作用機制尚未明確,考慮可能與多因素作用的結果[20]。國外亦有研究者嘗試將該種療法用于月經性癲癇的治療。改良阿特金斯飲食(MAD)是一種經典生酮飲食配方,中鏈甘油三酯(MCT)常被推薦作為MAD的補充[21]。美國一項前瞻性雙中心研究評估了在該療法的基礎上增加MCT對月經性癲癇患者的可行性[22],16名符合條件的女性患者被納入研究對象,其中13名女性完成了研究且依從性為100%,包括退出參與者在內的整體干預依從率為81.2%。結果顯示患者的依從性和耐受性較好,且具備一定未來可行性。近年來中西醫結合治療月經性癲癇的案例也有所報道[23],通過西藥口服結合古法針灸的治療方案,經1個月隨訪后患者抑郁情緒和抽搐癥狀皆有所改善。
3.4 改善預后和生活質量 了解癲癇發作和月經周期的關聯機制有助于制定月經性癲癇患者的治療策略,而及時預警癲癇發作、加強預后管理則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24]。對于育齡期癲癇患者來說,有效避孕能夠規避意外妊娠所致的風險。由于激素在體內與抗癲癇藥物可互相產生作用,在未來例如宮內節育器等非激素且高效的措施可能是育齡期癲癇患者理想的避孕手段[25]。長期藥物治療是癲癇的一大特征,部分育齡期癲癇患者在治療穩定出院后因擅自停藥導致復發,并且沒有獲得有效的孕前咨詢,開展專門的育齡期女性癲癇用藥隨訪與妊娠登記中心能有效解決這類難題。目前國際上已有多個國家和地區相繼建立,而我國這方面的工作還有較長的路要走,并且加強神經內科醫師與婦科醫師的協同指導[25],且應把治療的長期性與復雜性向患者及其親屬解釋,提高治療依從性,改善生活質量[26]。總之,與一般人群相比,癲癇患者的精神障礙、自閉抑郁等情緒反應發生率更高[27],除了疾病本身帶來的痛苦,女性癲癇患者由于其性別特征更容易發生焦慮、抑郁,甚至是自我羞恥感,且起病年齡越小、病程越長,患者的心理陰影越重[28]。因此對于確診的月經性癲癇患者,如果尚處于未成年期,盡早予以科學的生理教育和長期有效的心理關懷,家庭成員注意記錄月經周期發作的規律,提前做好防范準備,防止躁狂、摔傷等[26]。幫助患者克服心理負擔,盡早融入社會生活。
4 展望
月經性癲癇的臨床病例總體來說在各國并不少見,長久以來已經引起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和更深入的認識。未來還需要在進一步詳盡病理機制的基礎上,建立更多多中心大樣本臨床試驗來確定最有效的治療方案,并早日建立相關專家診療共識。月經性癲癇作為女性癲癇的特殊類型,還應格外注重對此類患者的預后護理、精神關懷,不斷完善專業的患者登記隨訪中心制度,切實提高患者后續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