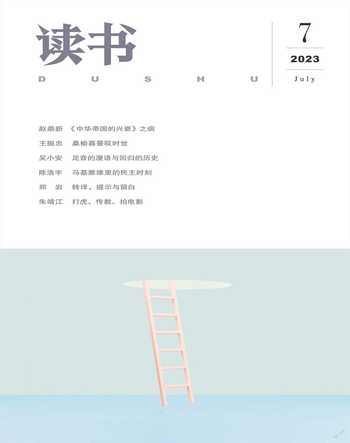今天我們?nèi)绾伍喿x列文森?
葉文心 歐立德 董玥等
列文森的著作自從出版以來,漢學界學者們的反應不一,有很多贊譽,亦不乏質(zhì)疑的聲音。列文森所著眼的,在空間上是橫向的銜接,在時間上是縱向的斷裂與延續(xù)的交錯。他把天下、國家、認同、疏離、忠誠等議題一方面看成近代中國知識人的經(jīng)歷,一方面也看成現(xiàn)代文明轉(zhuǎn)型的社會中知識承載者共同的經(jīng)歷。在這種大跨度的框架下,他下了不少宏大的結(jié)論,但史料的收集不是他的志趣與長項。列文森對儒家傳承多元體系的內(nèi)涵也并沒有下過太多功夫,他的詮釋理論對漢語原典文本極具選擇性,這些都成為漢學學術界批評的重點。老一輩的代表人物恒慕義(Arthur W. Hummel,1884-1975)根本不認同列文森,甚至不愿意承認《梁啟超與現(xiàn)代中國的心靈》是歷史著作。
列文森的三部曲,從構(gòu)思到出版,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產(chǎn)物。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不到十年。解釋共產(chǎn)黨何以在國共四十年代的戰(zhàn)爭中取得勝利,是一個政治性很強的當代話題。在朝鮮戰(zhàn)爭的氛圍之下,麥卡錫主義黑網(wǎng)密布,糾拿叛徒、處置蘇聯(lián)間諜、猶太裔的學人常遭另眼相看,被質(zhì)疑是否對冷戰(zhàn)時期美國自由主義右派所界定的國家絕對忠誠。列文森并沒有頌揚中國共產(chǎn)黨,但是他也沒有把共產(chǎn)黨的建國簡單地看成是國際共產(chǎn)主義的陰謀與顛覆,而是在更廣闊的歷史時空里思考這個過程。他把帝制結(jié)束之后的儒家思想看成失去體制、無所附著的游魂,把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與共產(chǎn)主義在中國的勝利看作長期歷史演繹、內(nèi)源蛻化不得不然的結(jié)果。這樣的立場在五六十年代的北美漢學界自然不會人人贊賞。華裔的名師碩儒或?qū)W術新秀,比如趙元任、蕭公權(quán)、房兆楹、瞿同祖、楊聯(lián)陞、張仲禮、劉廣京等,好像與列文森都沒有多少來往。他們在四十年代中或一九四九年之后離開大陸,雖然身在海外,但是心存故土,把懷抱寄托在對中華民族文化的想象上。在他們看來,盛年的列文森尚未進入中國經(jīng)史的殿堂,就斷然宣布儒家傳承已經(jīng)破產(chǎn),不免顯得既主觀又輕率。另外,列文森不把共產(chǎn)主義看成外來植入的異株,反而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將之詮釋成儒家傳承在思想情感功能上的替代。這些結(jié)論,都讓他跟同時代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中傾向反共的自由主義陣營產(chǎn)生分殊。
無論如何,對列文森觀點的爭論引爆了北美中國學界在相關問題上的批判或商榷性的研究。列文森以梁啟超為基礎,把儒家傳承等同于帝王主導的天下觀與天命論,把科舉制度看成意識形態(tài)的檢測,大膽地引進正在形成中的歷史心理學,認定晚清以后的中國制度與文化缺乏內(nèi)源再生的能力。列文森在世的時候,這些論點已經(jīng)促使青年學者從各方面開展研究,展現(xiàn)儒家文化在中國的豐富多元內(nèi)涵,及其在官場之外、社會民間或家族村落之中的規(guī)范作用。學者們結(jié)合思想、制度、社會、文化史,探究儒家倫理的宗教性以及心性層面、儒家思想在商人倫理中的作用、地方世家與書院的治學體系、科舉考試中的實學成分、地方士紳以及家族在公眾領域中的禮教實踐。這些研究全面地擴大了對傳統(tǒng)知識、“入世修行”、“克己復禮”等的理解。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隨著社會史和文化史的勃興,西方學者陸續(xù)解構(gòu)了“儒家中國”的概念,勾畫了“三教合一”的思想脈絡,凸顯了晚明的儒僧、僧道、寺廟、戲劇、繪畫,指出官訂的儒家教條在民間通俗文化以及地方精英階層中的輻射力度是有限的。二十世紀晚期和二十一世紀初期,學者們更撇開對思想內(nèi)涵門派的辯論,重新評價科舉對于清代思想發(fā)展的影響,探討明清王朝在近代早期歐亞火藥帝國體系中的位置以及與全球經(jīng)濟、科技、文化的交流,開展對于思想究竟如何轉(zhuǎn)型的研究。他們討論書籍的生產(chǎn)流播與閱讀、新知識體系的具體建構(gòu)與傳遞、語言文字表述體系的重新認定、古文詩詞文學與國學內(nèi)涵的重塑、知識人社會身份的形成、信息體系在近現(xiàn)代的轉(zhuǎn)型、廣義的“經(jīng)世之學”在二十世紀如何致用與實踐,以及在科舉制度之外,中國實用知識體系如何形成專業(yè)制度、建立實踐基礎。這些研究,主要針對明清以及民國,都發(fā)展于列文森過世之后,遠遠超出了他的三卷本的視野。這些研究成果綜合起來,不但重新界定何為儒學、何為轉(zhuǎn)型中的文化中國,并且重新思考近代知識、人文與轉(zhuǎn)型社會國家之間的關系,重新認識在走進世界、走向科技現(xiàn)代之后,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文化如何形成脈絡。在相當程度上,西方明清及民國史學的這些進展是列文森當初提供的刺激的長期結(jié)果。對近現(xiàn)代中國的理解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延續(xù)著列文森關心的問題,而且以各種方式回到列文森,即使人們有時并不直接在文本上與他進行對話。
從另外一面講,我們也需澄清,列文森辯證性極強的歷史心理分析,雖然極有助于厘清晚期以來中國思想界的取舍動態(tài),但是很難把他這種別致的方法傳給學生。在某種意義上,這個著重情感張力的分析似乎也沒有為近代中國思想史勾畫出一個多元并進的發(fā)展軌跡。然而正因為他的《梁啟超與近代中國思想》與《儒家中國及其現(xiàn)代命運》并不依傍他對一兩個學人或?qū)W派在文本生產(chǎn)上的描述,反而更有啟發(fā)作用。
試以他和后來者對梁啟超的研究為例。列文森出生的時候梁啟超仍然在世。在列文森生活的半個世紀中,中國處在不斷的分裂、戰(zhàn)亂、持續(xù)斗爭、困乏、在國際上逐漸孤立的狀況中。列文森同輩以及稍后的學者們,不少人同樣關切一九四九年所標志的歷史性開創(chuàng)與結(jié)束,同樣關懷其中所蘊含的古與今、中與西、必然與偶然、邏輯與人為的對立與結(jié)合關系,想要理解一九四九年后最迫切的問題:“到底發(fā)生了什么?”(“What has, in fact, occurred ?”) 與列文森不同,其他研究者仔細閱讀梁啟超的事跡與著作,認真對待梁啟超的文本闡述與思想內(nèi)涵;他們并不把梁啟超個人的經(jīng)歷擴大,看成一種具有典型性的中國知識心路歷程。而列文森所關切的是他平生如何游走四方,如何一變、二變,而三變,如何在行旅之中出入一己的外視與內(nèi)省。他所勾畫的是一代思想者在面臨時空秩序斷裂與重組時候的彷徨、焦慮、自省與追尋。他認定每當文明急劇轉(zhuǎn)型,轉(zhuǎn)型時代的知識承載者就無法像過往一般地依循規(guī)矩方圓,四平八穩(wěn)。轉(zhuǎn)型時期的失態(tài)與脫格是常態(tài),這個時期的不改平常反而是無感與脫序。列文森把現(xiàn)代性帶進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視野,把改造創(chuàng)新與失衡失語看作一體的兩面,把幸福與災禍看成緊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中國思想界對這個正反兩面交織并存的辯證式思維并不陌生。列文森不但把這個概念帶進歷史研究的視野,并且透過人物傳記,具體呈現(xiàn)了近代巨變時刻歷史人物身處其中,在時間上所經(jīng)歷的急迫感以及在空間上所經(jīng)歷的壓縮感。其他學者很難趕上列文森去走的這條纏繞崎嶇的路,或許并不奇怪。
列文森另一個引發(fā)辯難的,是他跟同時代不少英美學者共同持有的一個預設,就是把科學理性主義與工業(yè)科技文明看作近代西方文明的標志,把科技看成橫掃天下的普世實踐。在這個框架中,他把鴉片戰(zhàn)爭視為一個現(xiàn)代文明與一個前現(xiàn)代帝國的總體沖突。這個觀點,沿承自他的老師費正清,也反映出大多數(shù)國內(nèi)史學家們的基本姿態(tài)( 費正清畢竟師從蔣廷黻),到目前為止仍然如此。他雖然大力指出西方文明不足以作為完整的世界性知識,但是他對文明體系的表述,不經(jīng)意之間展現(xiàn)了十九世紀文明等差時空階段性的分殊。列文森對啟蒙運動的無條件欽佩可能會讓生活在后現(xiàn)代主義時代的我們覺得老派,而他引用未翻譯的法語和德語的參考資料可能顯得自負或歐洲中心。
此外,我們也很難支持列文森關于中國歷史的一些籠統(tǒng)的概括,例如關于晚期帝國思想潮流(我們甚至已經(jīng)不再使用“儒家”一詞)或滿洲人的漢化和最終“消失”(我們現(xiàn)在知道這沒有發(fā)生),或者同意他的一些更激進的立場,例如聲稱宦官和滿人在明清兩朝中央集權(quán)的政治中有著相似的功能。我們拒絕列文森的一些論點是非常自然的:鑒于世界各地的學者在這些問題和其他問題上已經(jīng)付出了三代人的努力,我們的知識在許多領域都有了進步。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大量新資料,尤其是檔案材料的出現(xiàn),以及新方法(包括那些依靠大數(shù)據(jù)和地方田野調(diào)查的方法)的出現(xiàn),意味著我們對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的理解比當時更加細致和全面。
那么,現(xiàn)在是否仍然值得我們花時間去讀(或重讀)列文森精妙的文章呢?答案是肯定的。列文森提出的問題——調(diào)和民族主義和文化主義,將中國置于世界歷史的潮流中,以及歷史和政治中的連續(xù)性和斷裂性的一般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而且在今天也許比在列文森的時代更加緊迫。在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中,歷史和歷史學家的重要性也沒有改變。事實上,鑒于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的崛起”,它們的重要性甚至可能更加突出。
“在很大程度上,近現(xiàn)代中國思想史是‘天下如何轉(zhuǎn)型成為‘國家的過程”,一九五八年列文森這樣寫道。按照他的解釋,這是一種極為艱難的過程,其中充滿彼此相互沖突的對立元素:普世和特殊,絕對和相對,文化和政治。在從文化主義到民族主義的轉(zhuǎn)變中,我們能夠追溯到中國如何從一個“自成一體的世界”轉(zhuǎn)化為“在世界里的中國”。總而言之,列文森對這段歷史的結(jié)論是:共產(chǎn)主義的到來為中國提供了另一個概括全世界的體系,這個體系能夠提供一個既是“現(xiàn)代的”,又是“中國的”未來。他說:“共產(chǎn)主義者所尋求的是一種綜合全局的全盤理解。 這個理解可以用來替代被拋棄的儒家理念,也可以用來取代跟儒家相互對立的西方理念。”列文森和其他人在冷戰(zhàn)早期寫的文章所預測的結(jié)果是,一個普世的革命理念會成為現(xiàn)實存在,并得以不斷完善,為中國的精英們源源不絕地提供必要的思想、政治和歷史解決的資源與方案,以應對中國在一個徹底改變了的世界里所面臨的生存威脅。
這些冷戰(zhàn)早期的預見在后來的現(xiàn)實發(fā)展中并沒有應驗。六十多年后,今天“中國模式”所建構(gòu)的中國軟實力,所依傍的是中國經(jīng)濟崛起的成績。在建構(gòu)一個強大、富裕、現(xiàn)代、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中國的同時,中國的理論工作者仍然在尋找一種既可普遍應用,又能被一眼就識別出具有 “中國特色”的模式。傳統(tǒng)中國的歷史也因此獲得了新的重要性。諸如“盛世”“復興”“大一統(tǒng)”等經(jīng)典表達方式在政治和流行話語中的復蘇,標志著理論工作向傳統(tǒng)主義思維的回歸。以列文森的話來說,這可以說正是“回歸之路亦是出發(fā)之路”的體現(xiàn)。
讓我們再次引用列文森三部曲第一卷的內(nèi)容:
頑固的傳統(tǒng)主義者似乎已不是單純在智性上信奉那些恰好是中國歷史產(chǎn)物的令人信服的觀念,而是成了決心去信奉——這種決心是去體會智性上的強迫感(compulsion)的情感需求——那些觀念的中國人,只是因為它們是從中國的過去傳承下來的。當人們接受儒家傳統(tǒng)主義不是出于對其普遍正確性的信心,而是出于某種(傳統(tǒng)主義)強迫感去公開承認這種信心,儒家就從首要的、哲學意義上的效忠對象,轉(zhuǎn)變?yōu)榇我摹⒗寺梢饬x上的效忠對象,而傳統(tǒng)主義也從哲學原則變成了心理工具。
列文森認為這種思維所提供的主要是心理安慰,而非令人信服的哲學論證。當然,思想的軌跡即使來自傳統(tǒng)主義的陳舊體系,也不一定缺乏魅力或感染力。這種種現(xiàn)象表明,列文森所提出的兩個結(jié)構(gòu)性的問題仍然是我們今天理解中國的關鍵:意識形態(tài)或文明建構(gòu)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在國族建設(nat ion-making)這個從天下到國家的過程中,中國處于何處?正在朝什么方向發(fā)展?
列文森的中心議題常常也正是近年引起國內(nèi)學界最大關注的問題,比如“何為中國”。今天的中國究竟是一個政治共同體還是文化共同體?現(xiàn)代中國人的認同基礎是什么?“中國”是一個自然的存在還是一個需要不斷建構(gòu)的機體?源于西方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帝國”“民族國家”“主權(quán)”等,能否用來分析中國歷史?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源泉來自何處?中國與西方是否完全不存在可比性?列文森在晚清民國歷史中所看到的矛盾,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同樣存在。他在第三卷中指出五十年代的史學家們一方面通過分期將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等同起來,同時又堅持認為所有過渡在本質(zhì)上都是中國內(nèi)源變動的產(chǎn)物。今天“中國模式”的世界意義與中國“國情”的特色也同時受到強調(diào)。中國常被人看作一種單一的、隔絕的、自我參照、自我封閉的政治思想體系,其“國情”比其他國家的“特殊情況”更特殊,因而是“獨一無二的”。根據(jù)這個“中國特殊性”的邏輯,中國不受一般歷史規(guī)律的制約,也無法與全球規(guī)范做比較。
同樣的現(xiàn)象也可見于大家對今天中國社會的“價值真空”問題的關注上。列文森認為,晚清儒家思想失去了君主政治的制度基礎,應當無法生存,注定要瓦解消失,只會剩下殘損的碎片,成為“舊結(jié)構(gòu)的殘磚斷瓦”(bricks of the old structure)。但在這一點上他似乎錯了:盡管有核心變化,“儒家思想”不但依然生存下來(或者說,各種自稱是儒家的思想流派經(jīng)久不衰),而且即使它今天沒有帝制時代的那種力量,也竟然再次產(chǎn)生一種出乎列文森想象之外的能量。從五六十年代以來形成的革命傳統(tǒng),也變成另一種傳統(tǒng)主義。列文森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一旦一個事物或思想被發(fā)明出來,它便不會徹底消失,而往往以變化了的形式在某個時刻復現(xiàn)。這個問題,即思想體系半衰期問題,提醒我們在思考當前中國所面臨的挑戰(zhàn)與話語抉擇時,要像列文森一樣,考慮話語形態(tài)所應付的是何種問題、所給出的是何種答案、所否定的又是何種方案。新一代讀者在關注列文森著作時,應能不僅關注歷史學問題和方法,而且能夠參照他的提問線索,理解目前意識形態(tài)的語境和我們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持續(xù)現(xiàn)代化。進入二十一世紀,現(xiàn)代化取得正當性,步伐只有加快,沒有放緩,哲人能者認識到居安必須思危。列文森當年所提出的議題與解析的方式,不僅著眼在現(xiàn)代性外發(fā)的體現(xiàn),并且打開了思維世界內(nèi)省的視野,關注到世代交替之際的傳承斷裂和話語重構(gòu),以及現(xiàn)代人情感與知識資源上所經(jīng)受的挑戰(zhàn)。就這個意義來看,列文森的史學關懷與方法,超越了對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解析,持續(xù)具有廣泛的闡釋力與開創(chuàng)性。從宏觀歷史層面來說,即使列文森有所誤判,也還能為我們提供一個有意義的視角,借以審視當前的中國。
最重要的是,盡管文化體驗和表達方式上的差異可能會妨礙人們立即相互理解,但列文森的世界主義、對人類智慧和人文價值觀的普遍性的信念依然很吸引人;這無疑是列文森對一種全面的、全球性的觀照中國歷史的方法最有意義的貢獻之一。它既反駁了西方對于自己的觀點的普遍主義的假設,也挑戰(zhàn)了中國的例外主義假設。要把中國歷史寫成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不等于說史學家必得找一大堆直接類比說明中國的歷史發(fā)展跟外國史一模一樣,但同時也不等于說中國的歷史發(fā)展與外國史不可比、無法比。在這些不相容的極端之外,必有許多中間道路可以選擇。與此同時,列文森對于歷史書寫持肯定態(tài)度,把歷史性的責任放在歷史學家的手里。天下體系的崩潰有其悲劇的一面,但作為一個樂觀主義者,列文森想說服所有關心中國歷史的人士,這是歷史工作者參與到把中國史編入到普世、全球歷史這一事業(yè)中的一個機會。把中國歷史經(jīng)驗再次整合于新的世界思想體系中,這是列文森才情所至、無所畏懼的一個表現(xiàn),也是他作為一個開放的思想家、一個真正的人文主義信徒的理想目標。他在“三部曲”的第二卷里這樣講道:
某種真的可被稱為“世界歷史”的東西正在浮現(xiàn),它不只是各種相互分離的文明的總和。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在書寫過去時,可以有助于創(chuàng)造這種世界歷史。歷史學家若遠離了任何事實上和想象中的文化“侵略”和文化辯護,就能通過將中國帶入普遍的話語世界,幫助世界在不止于技術的層面上統(tǒng)一起來。絕不應該去制造大雜燴,也不應該歪曲中國歷史去適應某種西方模式。相反,當對中國歷史的理解不傷害其完整性和獨特性,而且這種理解和對西方歷史的理解相互補充的時候,才會造就一個“世界”……研究中國歷史則應該不僅僅是因為其異國情調(diào),亦不僅僅因為其對西方戰(zhàn)略的重要性,而是因為我們可以想象用來理解西方的同樣話語世界來理解中國,而不必強求二者有相同的模式。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去理解中國和西方,也許我們就能有助于造就這樣一個共同的世界。書寫歷史的行動本身即是一種歷史性的行動。
列文森是一個充滿個性與智識上的魅力的人;他去世后,朋友們記得他“謙遜的魅力和愉快的自嘲故事”。作為一個在盎格魯- 撒克遜世界找到了一種生活方式卻又同時保持了自己的身份的猶太人,列文森本人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人,并期待或至少希望看到中國也能夠以自己的方式進入(或重新進入)世界。列文森對我們當前思考中國的努力——其統(tǒng)一但不乏矛盾沖突的政治、多元化的社會以及經(jīng)久不衰、代代有變的各種文化傳統(tǒng)——所做的貢獻遠不止“……及其現(xiàn)代命運”這個時髦的比喻。列文森以其獨特的風格對思考歷史大問題所展現(xiàn)出的雄心令人驚嘆。半個世紀過去了,列文森當年對問題的提法仍然得到關注,這個意義比他所提出的答案更能啟發(fā)思路。盡管他關于從天下到國家的轉(zhuǎn)變以及儒家思想與現(xiàn)代生活不相容的闡述在今天可能無法說服我們(這些觀點在當時也并沒有說服所有人),但他的觀點對我們提出了挑戰(zhàn),促使我們提出具有相似格局和意義的替代答案。但愿有更多的人以列文森本人在短暫生命中既嚴肅又興趣盎然的精神來參與他未完成的思想學術工作,并通過這種參與,更好地理解那些塑造了中國的過去和現(xiàn)在的力量,并使得塑造中國未來的力量更為強大。
〔《儒家中國及其現(xiàn)代命運:三部曲》(“列文森文集”之一),約瑟夫·列文森著,劉文楠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0二三年即出。本文節(jié)選、整理自文集導讀《在二十一世紀閱讀列文森:跨時空的對話》(導讀原文作者還包括白杰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