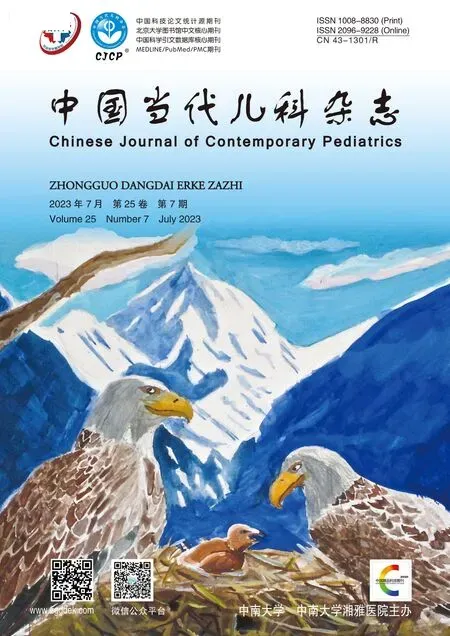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兒童的體格生長和膳食特征:一項橫斷面研究
林霜 吳丹丹 陳書進 燕武 竇麗華 李曉南
(南京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兒童保健科,江蘇南京 210008)
注意缺陷多動障礙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一種常見的神經發育障礙,以注意力不集中、多動、沖動為主要癥狀,通常起病于童年期,影響可延續至成年[1]。研究顯示,ADHD兒童群體中肥胖、消瘦、生長遲緩發生率均高于正常發育兒童[2-4]。兒童期膳食情況是生長發育的基礎,對ADHD 兒童的膳食調查顯示該類兒童更易出現營養素攝入不合理、膳食結構紊亂等問題[5]。既往有研究發現ADHD 兒童疾病癥狀和膳食攝入之間具有相關性[6],但結果并不一致,并且很少有研究關注ADHD 癥狀、膳食攝入情況及體格生長之間的關系,膳食因素在ADHD癥狀和該類兒童生長偏離之間發揮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證實[7]。本研究在比較ADHD 組和非ADHD 組兒童體格生長狀況及膳食模式的基礎上,進一步尋找ADHD 兒童生長偏離與膳食模式的內在關系,旨在為ADHD 兒童的臨床管理提供更多的科學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橫斷面研究。選取2020 年6—12 月在南京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兒童保健門診及心理行為門診就診的268 例初診為ADHD 的兒童為ADHD組。患兒均由主治醫師及以上職稱的醫師確診。納入標準:(1)年齡6~13 歲;(2)首次就診并符合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中關于ADHD 的診斷標準[8];(3)無ADHD 藥物使用史;(4)父母無重大軀體和精神疾病,意識清楚,無智力障礙,能完成問卷評定。對照組選自同期在我院兒童保健科進行健康體檢的同年齡兒童(102例)。排除標準:由其他神經發育障礙、精神病障礙、情緒障礙、藥物或器質性疾病引起的ADHD癥狀的兒童。本研究已通過南京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審批(審批號:NMUB2018074);患兒及父母自愿配合參與評估,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1.2.1 一般情況問卷 采用自編問卷收集研究對象的一般資料,內容包括:性別、年齡、既往史、電子產品使用時間、父母親文化程度、父母親身高體重、家庭年收入等。
1.2.2 膳食調查 (1)使用半定量食物頻率問卷法[9]調查兒童近1 個月食物攝入情況,包括主食、粗雜糧、蔬果、畜禽、魚蝦、零食、含糖飲料等14 個食物類別。根據食物攝入的頻率,將食物攝入分為:每天2次及以上、每天1次、每周4~6次、每周2~3次、每周1次、每月2~3次、每月1次、每月不足1次。展示食物分量大小的照片,以協助估計食物攝入量。參與者選擇每種食物的頻率及單次攝入量,并轉換為每天的攝入量。
(2)膳食模式分析:采用因子分析法[10]提取膳食模式。依據Kaiser-Meyer-Olkin(KMO)檢驗和Bartlett 球形檢驗結果判斷是否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并依據特征值、碎石圖和專業知識確定膳食模式的個數。統計方差最大正交旋轉后各類食物的因子載荷,因子載荷值越大表明該組食物與膳食模式關系越密切。本研究按照因子載荷系數>0.3的食物組選擇公因子,并根據食物的攝入量及其旋轉后的因子載荷,計算個體各種膳食模式的標準化因子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該個體對該膳食模式的傾向性越高。
1.2.3 體格測量與評估 采用人體成分測定儀(InBody J20)測量兒童青少年身高、體重、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體脂百分比(fat mass percentage,FMP)、骨骼肌質量百分比(skeletal muscle mass percentage,SMMP)等體成分指標。同時計算身高標準差評分(height standard deviation score,Height-Z)和體重指數標準差評分(body mass index standard deviation score, BMIZ)[11],并定義:Height-Z≤-2為矮小,BMI-Z≤-2為消瘦,-2<BMI-Z<1 為正常,1≤BMI-Z<2 為超重,BMI-Z≥2為肥胖。
1.2.4 ADHD 癥狀評分 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 版中關于注意力缺陷項目和多動-沖動項目各有9 個條目[12],共18 個條目,每個條目都有“是”或“否”兩個選項,按照“是”得“1”分、“否”得“0”分的方式記分,注意力缺陷項目和/或多動-沖動項目≥6 分方可診斷。兩個項目評分總分計為ADHD 癥狀評分,此評分尚不能說明ADHD 癥狀的嚴重程度[13],但評分越高,表明個體具有的ADHD癥狀種類越多。
1.3 質量控制
研究者進行統一規范化培訓。用統一的指導語對整套問卷進行簡單說明后,指導研究對象的父親/母親填寫一般情況調查表,并由經過專業培訓的研究人員進行膳食調查評估。
1.4 統計學分析
使用EpiData 3.1 軟件輸入數據,使用SPSS 22.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值±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使用兩樣本t檢驗;非正態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U檢驗。定性資料用頻數和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卡方檢驗或Fisher 確切概率法。采用Spearman 秩相關分析探討ADHD 癥狀評分、膳食模式得分及體格生長指標之間的相關關系;構建中介效應模型[14]后,以ADHD 癥狀評分為自變量,以零食快餐模式因子得分和FMP 分別作為中介變量和結局變量,并采用Bootstrap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及體格生長情況
ADHD 組納入268 例兒童,對照組納入102 例兒童。ADHD 組癥狀評分總分、注意力缺陷評分、多動-沖動評分、BMI-Z 及FMP 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而SMMP低于對照組(P<0.05);ADHD組超重/肥胖率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兩組矮小和消瘦的檢出比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兒童父母親BMI 值、父親文化程度及家庭年收入等一般情況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母親文化程度及家庭類型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兒童一般情況及體格生長狀況
2.2 兒童膳食模式評估
依據食物頻率問卷結果進行因子分析,KMO值為0.703,Bartlett 球形檢驗P<0.05,共提取3 種膳食模式:素食膳食模式(以粗雜糧及薯類、蔬菜類、堅果豆類食物為主)、傳統膳食模式(以蔬菜類、畜禽類、魚蝦類及水果類食物為主)、零食快餐模式(以加工肉類、油炸膨化類、含糖飲料類食物為主),累計方差貢獻率為43.97%。各類食物在3種膳食模式中的因子載荷情況見表2。

表2 膳食模式的因子載荷
ADHD 組零食快餐模式因子得分高于對照組(P<0.05),兩組兒童在其他兩種膳食模式上的因子得分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入組兒童3種膳食模式的因子得分 [M(P25,P75),分]
2.3 ADHD 癥狀評分、膳食模式及體格生長指標的相關分析
ADHD癥狀評分、膳食模式得分及體格生長指標之間的相關性分析顯示:ADHD癥狀評分與零食快餐模式因子得分、BMI-Z 及FMP 均呈正相關(P<0.001);零食快餐模式因子得分與FMP 呈正相關(P<0.001)。見表4。

表4 ADHD癥狀評分、膳食模式得分及體格生長指標間的相關分析#
2.4 ADHD 癥狀評分、零食快餐模式因子得分及FMP間的中介效應分析
依據中介效應分析原理[14],以ADHD 癥狀評分作為自變量,FMP 作為因變量,零食快餐模式因子得分為中介變量,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并采用Bootstrap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零食快餐模式在ADHD 癥狀評分與FMP 的關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直接效應值為0.513(95%CI:0.274~0.753,P<0.001); 間接效應值為0.187(95%CI:0.087~0.304,P<0.001);中介效應百分比為26.66%。見表5及圖1。

圖1 ADHD 癥狀評分與FMP 關系中零食快餐模式的中介效應

表5 ADHD兒童零食快餐模式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
3 討論
波蘭一項納入408 例7~18 歲兒童的研究發現,ADHD 兒童超重(14.71% vs 12.83%) 和肥胖(6.37% vs 3.45%)的患病率顯著高于對照組兒童[15]。Meta 分析也顯示ADHD 與肥胖存在顯著的正向關聯[16],并且肥胖也可能導致ADHD 疾病進展及預后較差[17]。本研究中ADHD 兒童超重/肥胖率是對照組兒童的1.66 倍,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18]。ADHD 與肥胖在遺傳因素、神經遞質[19]、晝夜節律[20]及炎癥通路[21]等方面的聯系,為解釋ADHD 共患肥胖提供了理論依據。除外超重/肥胖,Spencer等[22]對學齡前期ADHD兒童的調查發現,10%的ADHD兒童在早期可出現矮小,而對照組的發生率僅為1%,但是部分患兒在青春后期身高可恢復正常。研究顯示,ADHD兒童服用哌甲酯類中樞興奮類藥物可能會抑制食欲[23],接受1~3年藥物治療的學齡期ADHD 兒童體重較對照組兒童明顯下降[24]。本研究中兩組兒童消瘦和矮小的檢出比例無明顯差異,可能與本研究中兒童為學齡期兒童、首次診斷ADHD且無藥物使用史有關。
膳食模式代表了個體更廣泛的食物和營養素攝入組合,比單個食物或營養素更能預測疾病風險[25]。本研究結果表明ADHD 組的零食快餐模式因子得分高于對照組,提示相較于對照組,ADHD組兒童整體膳食更傾向于加工食品、油炸膨化類及含糖飲料等,同時粗雜糧及蔬果類食物攝入過少。類似地,一項關于ADHD 兒童膳食模式的研究表明,ADHD與以果蔬類、不飽和脂肪酸類食物為主的健康膳食模式呈負相關,而與以高糖、高鈉類食物為主的膳食模式呈正相關[26]。兒童期體格生長與膳食攝入情況密切相關。含糖飲料及加工食品等是兒童青少年的潛在致肥胖食物,攝取過多該類食物與后期體重增加呈顯著正相關[27]。此外,某些特征性的膳食模式,如對地中海膳食模式的低依從性,與ADHD 癥狀呈正相關[28],提示ADHD 與不合理膳食的關聯可能是雙向的,ADHD 患者更傾向于選擇不太健康的食物[29],如加工食品、甜食等;同時不健康的飲食本身會加重ADHD癥狀[30-31]。因此,對ADHD兒童膳食模式的關注,不僅有助于體重的管理,對其臨床癥狀的改善也可能有積極作用。當然,由于兒童膳食模式除受到自身因素的影響外,還受到家庭因素、社會經濟因素及地區因素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臨床中針對不良膳食模式的干預,也應從多角度制定全方位綜合性的措施。
既往研究表明,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肥胖密切相關[32]。本研究在調整了混雜因素(包括父母親BMI、父母親文化程度、電子產品使用時間、家庭類型和家庭年收入)后,ADHD癥狀評分與零食快餐模式因子得分仍呈正相關;同時零食快餐模式因子得分與FMP 也呈正相關。中介效應分析提示,零食快餐模式在ADHD癥狀評分與FMP 的關系中發揮了部分介導作用,這表明ADHD 癥狀可能會通過影響膳食模式進而改變身體成分。Seymour 等[33]研究發現在兒童青少年中,ADHD、膳食失調和肥胖三者之間在獎懲機制和情緒處理與調節方面具有重疊的行為通路。一項前瞻性研究也表明,ADHD核心癥狀先于不健康的膳食模式出現[29],這為ADHD 癥狀和不良膳食之間的因果關系提供了證據。膳食因素在ADHD癥狀與體格生長的關系中發揮介導作用可能與多巴胺(dopamine,DA)獎賞通路調節異常相關。DA作為中樞神經系統中一種重要的神經遞質,在空間記憶、獎勵或性行為維持方面起著重要作用[34]。ADHD患者體內DA處于低水平狀態,因而獎賞通路調節失調,最終出現注意力不集中、多動/沖動等核心癥狀[35-36]。為了彌補DA 表達的缺失,個體可能需要更強烈的外部刺激。食物作為獎賞物質的一種,能刺激突觸前細胞釋放大量的DA。因此ADHD患者對高熱量/高碳水化合物食物的反應更強烈,通過攝入更多這類食物,作為調節DA 代謝紊亂和獎賞通路失調的自我治療形式,以平衡情緒障礙[37],而長期的高熱量飲食不僅會造成體重的增加,也會提高機體DA 的刺激閾值,降低DA的釋放,形成惡性循環[38]。
本研究的局限性:研究期間正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流行,來我院健康體檢的兒童數量較少,以致對照組兒童樣本量偏少;其次,研究對象的一般情況及膳食調查均為父母主觀報告,可能存在主觀報道的偏差;最后,因子分析提取4種膳食模式的累計方差貢獻率為43.97%,提示還有其他膳食模式未被表達,需要進一步探索。
綜上所述,學齡期ADHD 兒童超重/肥胖及膳食結構問題檢出比例高于非ADHD兒童;ADHD兒童核心癥狀與膳食模式、體格生長狀況相關,其中零食快餐模式在ADHD 核心癥狀和體格生長狀況之間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臨床醫師在關注ADHD核心癥狀的同時,應將ADHD兒童的體格監測和膳食特征的評估納入臨床監測和管理中,有助于改善ADHD兒童的身心健康。
利益沖突聲明: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