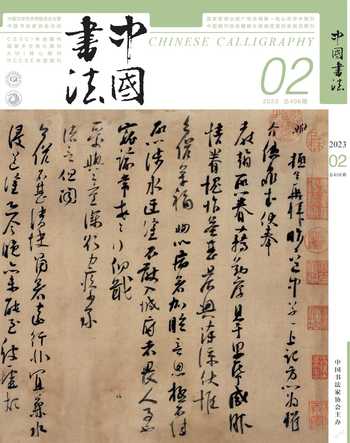晚清書法個案中的藝術社會史
冉令江
山西大學博士生導師劉維東教授新著《學古有獲:晚清大學士祁寯藻的書法生活》(以下簡稱《學古有獲》)近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以藝術社會史的視角反觀藝術本體,很好地把握了當代學術前沿,并由微觀個案的特殊性反映了宏觀的普遍性,是一部跨學科的藝術史研究專著。
劉維東長期關注以藝術家為中心的藝術史個案研究,《學古有獲》是他繼《張大千》(中國近現代美術經典叢書之一)之后的第二本藝術史個案研究專著。
該著與張大千研究不同,是對以祁寯藻(一七九三—一八六六)為中心的晚清仕宦書法環境與生活細節的全景式寫照。作者站在文化史和社會發展史的高度,把祁寯藻置于晚清特殊的政治、社會、文化環境中審視,在深入挖掘基礎史料、搜羅新史料的基礎上,運用藝術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文獻學、圖像學和考據學的方法,對祁寯藻的書法藝術、書法交往、書法饋贈、書法鑒藏和書法理論進行了詳實細致的考察、梳理和富有啟發性的探討。
大體而言,傳統藝術史的寫作是圍繞藝術家和藝術作品展開的。在這種范式中,『風格』問題自然是藝術史研究和寫作不容忽視的重要內容。劉維東的《學古有獲》一書雖然是以晚清書法家祁寯藻為研究個案的,但他并沒有按照固有的藝術家個案研究套路和模式,從慣常所見的『時代與生平』談起,而是以祁寯藻的書法作品為綱,分書體、依類別展開對其作品風格的梳理和分析。白謙慎先生在《晚清官員日常書法活動的研究》中,大致分為練習、自娛和應酬三類。[1]
劉維東在祁寯藻書法作品分類中,雖然沒有依此分類展開,但在其研究中不同程度地涉及對這三類書法作品和活動的討論,并且在書法作品風格分析的基礎上,強調了在時代語境中作品用途與書體、風格之間的內在關聯,凸顯書體、風格背后所蘊含的文化意義。比如,他分析祁寯藻的柳體書法風格時,在將其所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與柳公權《玄秘塔》具體字例、筆畫、結字體勢進行形式層面對比分析的基礎上,不僅指出祁寯藻將柳體更加美化、成熟化的風格特征,而且還從皇帝、同僚的影響和祁寯藻自身身份變化等三方面,闡述了其書法風格形成的原因,以及因此折射出的晚清官方書法審美風尚和政治文化意蘊。『這些與祁寯藻本人的生活環境和特殊地位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晚清官方書法的存在狀態。』[2]毫無疑問,祁寯藻的書體選擇及其書法風格的形成,無不與其當時所處的生活環境和社會關系有著密切的關聯。
在藝術社會學家的眼中,藝術是一種集體性的活動,而對集體性的強調無疑是為了凸顯藝術的社會本質。英國藝術社會學家詹妮特·沃爾芙說:『藝術社會學打開了一種視角,我們可以理解藝術和文化的建構性質—它的實踐者、觀眾、理論家和批評家以及它的產品。』由此可見,藝術社會學既可以關注藝術的社會建構,同時并不喪失對藝術獨特性的敏感。[3]
書法藝術作為中國傳統文人精神和文化生活中被高度珍視又極為精妙的藝術,同時也是最具普及性和社會性的藝術形式之一。為了更全面、深入地挖掘和探究祁寯藻的書法交往,劉維東在遍覽正史的基礎上,對晚清學術、詩文、題跋、書札、日記、著錄等文獻和書法遺跡中有關祁寯藻的書法內容一一進行梳理和考證,從中探尋與祁寯藻書法相關的『事件』,并努力將它們還原到原始的歷史、社會語境中進行解讀和分析,不僅真實還原了祁寯藻書法交往的點滴,也為我們構建了一個以祁寯藻為中心的晚清仕宦書法乃至詩文交往的社會『朋友圈』和『關系網』,凸顯了與書法相關的文藝活動在構建仕宦人際網絡方面的背景、原因和作用。特別是對祁寯藻與老師黃鉞、直隸總督那彥成、朋友何紹基、晚輩莫友芝等仕宦、名流的詩文、書畫、學問、仕進等方面交往的梳理和考察,作者通過交往過程中的一個個事件,引出由事件所引發的書法作品而展開深入討論,并指出『書法在晚清是仕宦文人生活中的重要內容,書法交往是他們文化生活的重要一環,它雖然常常伴隨著詩歌唱和、書畫鑒賞、文字探究等活動而展開,但卻深刻反映出仕宦文人雅致的生活方式和理想追求。』[4]無疑,這還原了祁寯藻書法學習和創作的具體社會情景,為我們呈現了祁寯藻社會生活中的『真實圖景』。例如,在祁寯藻接受御賜書法作品一節的論述中,作者在對具體史實細節進行深入考辨的基礎上,把祁寯藻接收御賜書法時的心態刻畫得淋漓盡致,而且進一步闡述了御賜書法所反映的深層次仕宦生活、君臣關系,以及特殊的文化內涵和政治意味,特別是凸顯了書法在構建和反映君臣、仕宦政治關系方面的特殊意義。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就書法談書法,而是把書法放在廣闊的政治環境、社會制度、文化語境和君臣關系之中,討論祁寯藻所代表的晚清仕宦群體的日常生活、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書法所起到的獨特的載體或媒介作用。
由此,也為我們生動展現了晚清官員日常生活中的書法實踐活動,及其所蘊含的政治性和制度性等因素。
在藝術社會學的宏觀敘述中,作者還對一些微觀的細節問題進行探討,比如對明代以來普遍存在的『代筆』現象的關注和討論。關于明清書畫的『代筆』問題,啟功先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曾有過討論,研究明清書畫藝術史的高居翰、白謙慎、陳怡勛等學者也有所涉及和專門討論,但對于此問題的關注和研究仍遠遠不夠。有關祁寯藻書法饋贈活動中出現的代筆現象,劉維東通過對其書法作品的對比分析和相關史料的引證,不僅辨明了代筆作品,闡述了晚清仕宦代筆現象的衍生和特點,而且明確指出代筆現象是中國禮儀文化深層內核及其發展狀況在晚清時期的延續和體現,從中也反映了書法藝術在晚清所發揮的維護人際關系的社會功能。
再如,關于祁寯藻的書法鑒藏活動,作者在搜羅其有關的詩文、題跋、信札等瑣碎文獻的基礎上,進行歸類并展開對比論證,不僅詳細梳理了祁寯藻的書畫收藏、流傳、版本和鑒賞等情況,而且為我們還原了以祁寯藻為中心的晚清京城宣南(宣武門以南)鑒藏文化圈及其雅集、鑒藏等活動。在該書中,作者特別是對宋拓《大觀帖》的收藏和鑒賞進行了詳細考察,并透過那些歷史細節,生動地還原了當時仕宦文人對于刻帖鑒賞的熱情和嚴謹考證的學風。
此外,在書法理論方面,祁寯藻雖沒有專門的書學論著,但其書法主張散見于詩文、題跋和部分書作中。
劉維東遍覽祁寯藻浩瀚的詩文、題跋和書作,從中梳理和歸類,以南北書派論、帖學、碑學和『詩書悉從至性出』四個方面,對祁寯藻的書學主張進行提煉、概括、總結和論述。特別是對于清代中晚期興起的『南北書派論』和碑學主張,作者在祁寯藻與何紹基的詩書唱詠和碑帖題跋中條分縷析、比較論證后指出,祁寯藻對阮元的『南北書派論』表示肯定,并盛贊何紹基對碑學所做出的貢獻,但對于阮、何將『顏(真卿)柳(公權)書法列入北派,異于王(羲之)派』的主張,祁寯藻并不贊同,他主張顏柳書法與王羲之書法是一脈相承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從祁寯藻『心正筆正真諦存,肥瘦何須苦分判』『自古書家出忠孝,尋常乖合不須論』兩句詩中,點明了祁寯藻看重的是經世致用的大作為,風格的區分和討論并非問題的核心。這一見解,無疑直接抓住了祁寯藻關于碑帖書法理論主張的根本。作者還從兩漢經學、宋明理學兩大學術研究范式和祁寯藻、何紹基的學術背景、書法實踐經歷等方面進行分析,深入論述了祁寯藻在一定程度上是肯定碑學的,但他更注重維護帖學的地位以及謀求帖學發展的學術態度,證實了晚清并非碑學理論一統天下的書法史實。
通觀整部著作,劉維東以藝術史個案研究出發,不僅為我們細致地梳理了祁寯藻的書法生活狀態,探究了以祁寯藻為中心的晚清仕宦藝術史問題,而且也為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及其看待問題的方式,正如他文中指出:『完美型書寫的審美是書法史上長期存在的現象,我們可以將之與館閣體相聯系,卻不應簡單地等同對待』『我們應該加強以文化傳承的視角來重新審視這段耐人尋味的歷史現象(帖學的堅守、包容,與碑學的激烈、偏執)。』[5]因此,《學古有獲》這部著作,不僅對祁寯藻的書法藝術、書法生活進行了全面細致的論述,為研究祁寯藻書法提供了豐富的材料;而且作者以書家個案揭示了晚清仕宦群體的書法生活和書法之變,以及仕宦書法生活與書法藝術之間的互動關系。該著作不僅對很多具體的問題進行了細致深入的討論,而且能夠從中圍繞每個具體的問題展開高于個案的討論和對話,并引出一些藝術史上共同關心的問題。通過對一個藝術家生活細致入微的考察和論述,揭示了一個時代、一個階層形成的藝術世界或文化史中所蘊含的問題,這無疑對晚清書法史和藝術社會史研究,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和方法論意義。因此,如果將該著作置于藝術社會史的譜系中衡量和看待,也是值得我們多加留意和重視的。
注釋:
[1]白謙慎.晚清官員日常生活中的書法[C]//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第一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219.
[2][4][5]劉維東.學古有獲:晚清大學士祁寯藻的書法生活[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35,76,154-155.
[3]盧文超.中間道路的藝術社會學—詹尼特·沃爾芙藝術社會學思想探析[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5).
作者單位:中國國家博物館 山西大學美術學院
本文責編:熊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