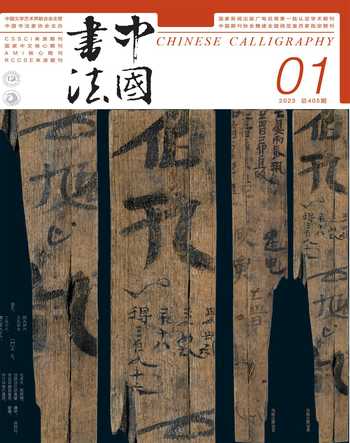五屆草書展評議
劉宗超


全國第五屆草書作品展覽的作品形式豐富而且具有作品感。『作品感』是指每件作品都具有美術作品一樣的完整形式,作品的內部構成和諧統一,尤其是對一次性、不重復性書寫形式來說,作品的內部構成非常重要。我們可以把作品形式分為外形式和內形式來進一步分析。外形式是作品的整紙形式、形狀、色彩、質地,以及構成整體作品的拼貼組合形式,本次展覽外形式可以分為:條幅整紙、拼貼而成的條幅、對聯、橫幅、冊頁。因考慮到展覽效果和評審公平性,尺幅作了統一限定:投稿原件尺寸為八尺整張以內,小字類(單個字徑一般在二厘米以內)作品尺寸為六尺整張以內。所以,入展作品基本上是這個規模。當然,為了擅長寫小字草書的投稿者達到六尺整張規模,作品往往以多塊手札拼貼而成。據筆者統計,本屆入展作品拼貼而成的條幅比例達到百分之五十一,可見作品拼貼現象較為突出,設計色彩濃厚。同時,拼貼的作品都為小字草書,書寫精細,筆法細膩,缺少的正是具有大氣象的作品。對聯、橫幅、冊頁占比極少,字形碩大的少字數草書沒有出現,也顯示出本屆展覽工細有余,大氣不足。
作品的內形式指的是所采取的書體(章草、小草、大草)、作品取法以及書體本身的組織形式(如單字組合的章法、多字連寫加單字組合的章法)。據筆者統計,本屆入展作品書體中,大草、小草、章草占比大致為5:3:2,因為其中的章草作品多為小字作品,小字草書實際包括小草、章草兩種體勢的作品,小字草書占比百分之五十二,略高于大字草書作品。這與上面一組的比例分析基本一致。這進一步說明,本屆展覽出現的工細傾向,小字草書作品眾多,顯得有些平面化,在密密麻麻的小草書作品面前,草書的氣勢表現得不夠充沛,有些瑣碎化。
作品書寫內容是衡量創作者文化修養和審美取向的重要因素。本屆展覽《征稿啟事》明確說明:『提倡投稿作者自撰書寫內容,文白均可。』但從入選作品可見,自作詩文作品僅占百分之四,說明作品內容的原創性比較低。書寫內容的選取也有扎堆現象,按占比多少依次為:蘇東坡詩詞、李白詩詞、董其昌《畫禪室隨筆》節錄、黃庭堅《山谷題跋》節錄。蘇東坡詩詞智慧達觀、李白詩詞浪漫奔放、董其昌《畫禪室隨筆》、黃庭堅《山谷題跋》多內蘊。四者之中,李白詩詞本應最適合表現草書的開張大氣,而占比遠低于蘇東坡詩詞,由此可見本屆草書展總體上偏于內蘊、節奏偏于舒緩,與創作者投稿前的反復推敲有關,當然也與評委對作品細節的評審取向相關。草書展覽評審注重的依然是評委審美差異的最大公約數,精心設計的作品入選幾率較大。那些雖有個性和氣魄但是存在瑕疵的作品,很難進入入選環節。當然,如果增加初評和終評評委的『一票提名權』,可能有利于有個性、有氣魄的作品的入選。另外,清代王文治《快雨堂題跋》、明代郭尚先《芳堅館題跋》能夠引起一定的重視,也說明這些不夠經典的文本更容易逃避評審者的挑剔。另外,有的作品作者在落款中沒有說明文本出處,有的僅落二三字窮款,說明作者對作品內容的原創性不夠重視,這應該引起各方重視。
作品取法是衡量書法家深入傳統經典的程度和審美取向的重要觀察點。本屆草書展在取法上也有一些特點。大草多取法張芝、《古詩四帖》、懷素《自敘帖》和大草《千字文》、黃庭堅、祝枝山、徐渭、王鐸、張瑞圖、倪元璐等草書體勢;小草則以取法『二王』、孫過庭《書譜》、懷素小草《千字文》、董其昌一路風格為主;章草多取法漢簡、《平復帖》、宋克、王蘧常等典型書風。這顯示出本屆展覽作品取法草書經典的鮮明取向。當然,取法也非平面化,大草作品取法懷素《自敘帖》、黃庭堅、祝枝山、王鐸、倪元璐的更為突出,作品以八尺或六尺整張書寫,簡潔明快,注重形式的空間構成感、時序的節奏感和線條的奔突感,富有形式張力。在草字造型表現上,時有經典作品造型的運用,試圖喚起觀者對經典的記憶。也就是說,作品處于臨寫到創作的過渡表現階段,甚至有些作品處于集字創作的初步階段。本屆草書展小草作品多為拼貼而成,局部字法精致,筆法一絲不茍,整體有密不透風之感,對經典的學習與表現比較到位。這標志著當前草書創作的路子正,技術表現到位,專業化走向突出。章草作品的規模與小草相近,但是追求古樸蕭散之韻,尤其是筆法上多使用破鋒、漲墨、宿墨,營造出較之小草更為古樸蒼莽的效果。
大草、小草、章草的不同表現,顯示出當下對草書傳統經典的取法與藝術表達已經比較深入。當然,作品取法表現的直接與清晰,也顯示出本屆草書展存在囿于傳統經典而創造性不足的弊端。比如,入選作品中出現了酷似懷素《自敘帖》、王鐸草書、董其昌草書的作品,結字和筆法再現得很到位,但是從草書本身的屬性而言,如此精準不見得是好事。與其他書體屬性有別,草書書寫的時間性突出,在迅捷的書寫中追求外在形式語言的酷似,難免陷入刻意和做作,作者的真性情如何能表現出來呢?所以,精準臨寫對草書學習而言,未必合適。本屆作品小草多,作品過于平面化,抒情性不足。對孫過庭《書譜》、董其昌小草的偏重,使得一些作品易于出現媚俗和油滑之氣,降低了草書的品格。另外,對『二王』帖學、徐渭、現當代草書名家、少字數大草的取法明顯不足,使得本屆作品的面貌有些扁平和單調。
對草書屬性的把握不足,是制約當代草書健康發展的根本因素。全國第五屆草書作品展作品模仿痕跡太重。從本屆草書展可見,作品取法古代經典的跡象非常突出,清晰可見。如出現酷似某一書家法帖的現象,有的甚至有集字的感覺。篆隸楷行書體體勢特點突出,取法某一法帖尚可理解,但是草書的迅捷性、至情性特征非常突出,若再亦步亦趨追求準確性臨摹或再現(甚至『集字式』創作),就有刻意做作的弊端。當一件大草作品模仿痕跡非常突出時,我們就會感覺到這就是一件只見手跡不見作者心跡的『偽作』!草書的至情性抒發的是自我真性情,而不應該是被模仿的古人的性情,實際上也不能重復古人的性情。我們在模仿顏真卿《祭侄文稿》時,臨摹皴擦涂抹的方式只是適用于學習中的技法訓練,而不能成為自己創作時的套路。由于全國草書展的參賽者多為中青年新人,作品為獲得評委認可爭取入展,精準模仿的取向可以理解,但是并不可取。其實,應該遵從草書本性,在掌握了基本技法后融入己意,寫出自己的情懷和哀樂。由于書寫的疾速,只要解放心態,放開自我,由『我法』化解『古法』,實際上也很難刻意地形似古人。
當代草書家應該重啟『意象』思維。古代草書書論都重在分析草書作品的意象,而很少談一筆一畫的技法規范,因為對高度抒情、高度抽象的草書來說,不能套用其他正書體勢的方法簡單分析其章法、結字或筆法,而對『意象』的發現和解讀更為根本和重要。由于當代人已經從鄉土文化發展到了現代『混凝土文化』,人與自然、書法與自然的純樸關系容易被遮蔽,我們現在看到的書論基本上都是現代形式分析,而對于這個形式的產生根源一般不怎么關注,而這正是當代書法家所應思考的。只要細心研讀古代書論和古代草書經典,不從『意象』著手難免有所隔閡。漢字產生是『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的結果,古代草書經典的產生也是書法家把『天地萬物之變』,通過自己的『可喜可愕』而『一寓于書』的結果。當代人也應該在一定的臨摹基礎上,從大自然的『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生活感受中,再去感悟和發現草書之源。草書經典只是一個跳板和媒介,是藝術學習的『流』,大自然和人本身之『道』才是書法學習創造之『源』。黃庭堅最終從自然中獲得書法創造的原動力,他在《山谷題跋》中說:『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法,王右軍錐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蠆尾,同是一筆法,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他找到了書法藝術與自然規律相通之關鍵——『同是一筆法』,也就是從自然界發現書法創造的原動力。實質上,藝術家只有回到自然,在自然、社會、人生中得『道』,才會獲得藝術創造的本源,從而通過『天人合一』的體驗,創造出新的藝術風格。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