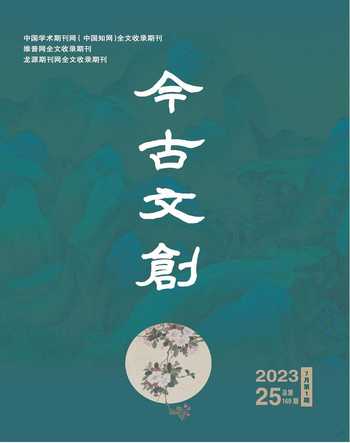民國時期成都地區婚姻自由觀念的變遷
王俊謙 郭清源 陳林星
【摘要】民國時期是中國報刊發展繁榮的一個時代,而報紙作為人與社會之間重要的交流媒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特定時期中國社會的人文風貌。《新新新聞》是民國時期四川報界持續時間最長影響面最廣的民辦商業性報紙,本文通過梳理其1931-1949年與“婚姻自由”相關的事件報道、時評文章,分析成都地區婚戀自由觀念演變中發生的理想化、混亂化問題。
【關鍵詞】《新新新聞》日報;婚姻;四川
【中圖分類號】G212?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25-0055-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5.018
基金項目: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近代報刊視域下的成都地區婚戀觀研究——以〈新新新聞〉為中心》(項目編號:S202210656145)。
《新新新聞》報創刊于1929年9月1日,停刊于1950年1月13日。《新新新聞》的報道內容涵蓋經濟、政治、民生等廣闊領域,早在1933年,其日銷量就已超過成都市日銷總量的一半以上,日銷最高時可達22000余份[1],不僅是當時四川地區的第一大報,也是研究者發掘成都歷史文化的重要途徑[2]。
目前學界對《新新新聞》的研究集中在報刊史、版面特征、廣告內涵研究,對涉及婚姻題材,尤其是涉及現代成都婚姻自由觀念的大量報道與評論文章,缺乏專門的研究,《新新新聞》作為四川新聞史上的重要文本資料,在四川婚俗文化的發掘上也應該得到一定的重視。
本文力圖通過查閱《新新新聞》的保存資料,以該報中的婚事啟事、婚戀新聞、婚俗評論為切入點,勾勒民國時期四川婚俗的社會風貌,探討當時男女的婚戀情況與現實困境,豐富對于近代成都地區婚戀文化尤其是“五四”之后自由婚姻觀念的席卷帶來的種種問題的具體論述。
一、20世紀20-40年代《新新新聞》中的婚姻自由圖景總覽
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為婚姻準則的舊中國,“戀愛”這一婚姻中必經的程序一直被長久地遺忘。可以說,舊社會的青年人在自身的婚姻戀愛方面毫無自主權利。
清末民初以來,隨著西方的性別觀、婚姻觀等先進思想不斷傳入,在文明先進的新思想對中國封建舊婚俗的沖擊之下,國人對婚姻自由的認識發展到達了一個新的階段。1931年南京國民政府《民法親屬編》同《民法親屬編施行法》正式實施,同年中央蘇區政府也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二者都規定“婚姻以自由為原則,男女均具有結婚和離婚的自由”,這標志著婚姻權力正式在法律層面完成了由封建大家長到兒女本人的轉移。而《新新新聞》的婚事新聞是對這種思想解放的清晰反射。
第一,自1929創刊以來,報紙所發行的關于婚姻戀愛的時事評論已經形成了一種提倡婚姻自由的共性,并圍繞婚姻自由的話題開展了對當時社會婚姻問題的探討和反思。僅1931一年報紙就刊登了數起“逃婚”事件,如《婚姻自由——有情人都成眷屬》《永川逃婚女郎白順貞——父母包辦婚姻,堅不承認脫逃》等,這些新聞中的主人公都面臨著父母包辦婚姻的境遇,并最終通過逃婚等各種方式進行自己的抗爭,至于離婚啟示以及婚姻官司的新聞更是屢見不鮮。
第二,在涉及少數民族以及國外婚姻風俗與制度的報道中,著色于自由戀愛的筆墨也占有相當大的分量,后期關于婚姻的報道中甚至多了不少對于青少年如何戀愛擇偶的指導性文章。一篇新聞評論更是戲謔地說道:“近來我國發生了一種新的名詞,這名詞是什么呢?就是三歲的孩子也是知道的,又是如常所聽見的,就是‘戀愛二字。現在社會上一般的人,對于戀愛是非常喜歡,并且是很濃厚的。”[3]無疑,是時婚戀自由的概念已經深入人心,成為社會婚戀觀中的主流思想。
二、對婚戀自由實踐中的問題呈現
在封建時期,婚姻作為鞏固、增強家族勢力的有效工具,其最高目的一直是傳宗接代。隨著社會風氣的開化,新型婚戀觀的擴散,城市中父母主婚權逐漸下移,男女交往趨向開放,不少青年不同程度上獲得婚姻的自主權,新式文明婚禮與婚制也得到傳播,城市婚姻制度發生大裂變,一部分青年正從傳統婚制中走出來。[4]但封建禮教的影響一時難以根除,被包辦婚姻壓迫的青年男女不在少數,一方面封建制下的非常態婚姻仍在縣區與農村地區肆虐,另一方面本身涉世未深青年男女,對當時盛行的婚姻自由觀念盲目崇拜,經常做出草率的婚戀決定,在當時的社會也引起了一陣軒然大波。
(一)封建思想的強大慣性
盡管青年男女對婚戀自由翹首以盼,但婚戀自由在某種意義上仍然只存在于幻想。根據對《新新新聞》結、訂婚啟事的抽樣統計(自1945年開辟結婚訂婚啟事板塊后,隨機選取50天的報紙查看結訂婚啟事),出現“經某某先生介紹訂婚、結婚”字眼的比例反而高達46%(鑒于未提及戀愛方式的啟示占大多數,這個數字只會更高),這透射出了民國青年美好希冀與現實之間的反差——他們看似已經從封建婚姻的束縛中解放,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供他們自由戀愛的社會空間比較狹窄,并不足以支撐起社交公開、廣泛交際而后自由戀愛的構想。
究其原因,是因為四川大部分地區的婚姻狀況仍然受著封建意識形態的影響。
一方面,除去最普遍的“聘嫁娶”以外,許多非常態婚姻形式也被一并保留了下來。纏足作為中國古代審美觀種的一種畸形觀念,是封建禮制強加于女性的惡果之一,也是封建婚姻制度下延續千年的一種婚俗。1924年,四川郫縣知事呈報本縣婦女纏足及禁纏情形說,“川省禁止婦女纏足,不啻三令五申,而一般人民仍陽奉陰違,不肯開放”,且將“放足引為畢生之恨”[5]。在《新新新聞》1932年7月29號所發行的內容中,有一篇名為《綿陽纏足風盛——男女婚姻父母包辦 愛憎在足而不在人》的報道,提到在“風氣閉塞”的綿陽,纏足依然是能否成婚的決定性因素,地方政府的禁令不曾發揮效用。這篇報道也印證了傳統非常態婚姻的余毒在彼時四川的部分地區仍具有強大的影響力。除卻纏足,《新新新聞》所報道的多起非常態婚姻新聞可以證明這些畸形婚姻形式并非孤例,其所涉及的畸形婚姻大致有三類——童養婚:《姑惡!姑惡!心腸太惡——殺死童養媳婦》(1947.10.27);轉房婚:《滅絕倫紀嬸侄竟轉房——事出隆昌縣》(1935.7.15);入贅婚:《談談松茂贅婚——贅婿是女家的變態奴隸》(1937.4.26)。
另一方面,青年男女在自己的婚姻問題上仍然受到封建家長的限制。尤其女性在面對自己與家長之間懸殊的力量差距,往往只能用逃婚等較為極端的方式來反抗,更有甚者以死言志。在《新新新聞》1936年4月20日的第五版中有一篇報道,雅安張氏女子與同齡錄事師爺暗生情愫,但因父母早已定下婚約,為反抗而吞煙自殺,轟動全城。1934年《新新新聞》所刊登的一篇名為《婦女的兩個切身問題——婚姻與職業問題》的文章指出:“戀愛”是“每個青年男女一種本能的要求”,但是“我們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看看那些報紙雜志上的小品論文所描寫的青年們的痛苦、煩悶,和常常登載的那些青年們自殺的消息,如果追溯其原因,不是為生活所壓迫,便是婚姻的不自由或失戀”[6]。在相關報道中不難發現,這些自殺案的涉案主體都是一些剛到適婚年紀的青年男女,他們同時承受著自由觀念的沖擊與封建禮俗的壓迫,以死言志成為涉世未深的他們對于封建觀念最后的反抗。
(二)婚姻自由主流化后的亂象
在當時婚戀自由剛剛成為主流觀念的社會,青年男女往往在婚戀問題的處理上過于草率——戀愛時對方的身份、性格、心理和結為伴侶后的生活方向、經濟考量、生育問題等等,許多青年人全不考慮,只憑著一腔激情就戀愛結婚。從而矛盾一觸即發,社會亂象頻生,具體表現為離婚率的非正常增長。
隨著思想的解放與婚姻法律的完善,離婚不再是人人避之不談的道德禁忌,成為人們解決婚姻問題的有效手段。這本該是思想進步與社會發展的體現,然而在《新新新聞》的啟事板塊中,離婚啟事日日都有,所有聲明中占比最高的離婚理由就是“意志不合”。據《新新新聞》中一篇名為“民事案件,離婚最多”的報道,成都地方法院在短短一個月時間里收入的離婚狀紙高達三百四十份。《安縣離婚風盛——縣府婚姻案月必數見》這篇新聞中也提到“平均計之,訴請縣府離婚者,月必數現,其年齡尤以廿至卅歲之青年男女為最多云”[7]。這些新聞報道充分展現了離婚事件在當時社會中的普遍性。數量如此之多的離婚事件不免反映出社會婚戀領域存在的問題:因過度提倡自由而導致的草率婚戀。
這種完全憑借一時沖動就私訂終身的事情,在當時經常發生。此種現象的頻發也引發了進步青年們對婚戀問題的反思。《自由婚姻的真義》的作者就直筆批判這種過分“自由”的戀愛:“現在一般講愛情的朋友,對于手續信條完全沒有……據個人看來,這種戀愛不是真的戀愛,這叫著亂愛,也叫著獸性之愛,這些講愛情的沒有照著真正的婚姻手續去做”[8]。
三、對婚姻自由觀念演變中的問題分析與思想立場
20世紀20-40年代的中國,社會的婚姻狀況仍然處于轉型的階段,在整體承認和推進婚戀自由理念的基調之下,封建思想的強大慣性依然影響著現實的婚戀行為。同時,數千年的禮教壓迫一朝瓦解,人們對于婚戀自由的追求產生了一種過激的傾向。透過《新新新聞》的時事評論^可以分析出其報紙立場體現出一種對婚戀自由深層次的思考。一方面,《新新新聞》通過對少數民族及國外婚姻事件與婚姻制度的報道來傳播婚戀自由的理念,并且針對國內青年的戀愛問題也做了諸如擇偶標準之類的指導。另一方面,面對當時社會狂熱崇拜婚戀自由的現象也做了較為深刻的批評和反思。
第一,《新新新聞》敏銳地觀察到當時封建思想作用于婚姻生活的強大慣性。在1934年8月4日第十版的《婚姻問題之我見》中,作者這樣分析傳統的婚姻模式:
“兩性若要結合,動輒就要‘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致演成一種‘包辦式的婚姻,所有雙方情愛、意識,完全一筆抹殺,將一素未睹面,情感不洽的男女,強逼成為一塊兒的夫婦,還借什么‘良緣鳳締,佳偶天成……各種神秘的話來掩飾,真是荒謬極了。結果大多數‘琴瑟不調,比目變成反目成為惡姻緣的慘劇,像這樣,還望得著和的目的,家道還能有成就么!?是等于癡人說夢了。”[9]
作者指出,社會上的大家族依然在用最專制的思想,借舊禮教束縛的力量,將青年男女壓制得極端的閉塞,“男女授受不親內外防閑”等等的腐論在中國仍然具有相當的話語權。尤其是縣城、農村地區,這大概是由于民國時期新思潮集中在城市的傳播,而農村或邊遠縣城則相對閉塞,封建思想殘余較重。
第二,《新新新聞》作為秉持著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媒體,發揮著傳頌婚戀自由的作用。在《新新新聞》的事件報道中,外省、少數民族及國外婚姻的報道不在少數,基本上每年都會刊登一到兩篇相關的報道。如1931年4月1日所刊登的《青海人的婚姻》、1936年1月19日所刊登的《寫寫苗族婚姻——綠草代絨氈巖作枕頭,便成就夫妻名分》以及1940年8月30日所刊登的《康人的婚姻》等文章,都是對外省及少數民族婚俗與婚姻觀的報道,在這些報道中,“自由結合”等詞語比比皆是。而在1936年十月到十二月,《新新新聞》連續刊登了三篇報道英國國王愛德華以退位為代價迎娶一加拿大平民女子的事件,對此給予了“打破傳統習慣”“合于時代性的英明之主”的高度評價。可以發現《新新新聞》秉持的是一種贊揚并積極傳播婚戀自由觀的態度。
第三,在反對傳統、提倡自由的基調之上,《新新新聞》對當時社會因過度提倡自由而引發的亂象也有著較為深刻的認識,并就解決方法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在《婚姻問題之我見》中,作者對當時社會對婚戀自由的實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批評。
“當一般青年受新潮流沖刷之際,一時熱度澎湃,自不免蹈過于浪漫之弊,于異性的結合,大多任一時熱情的沖動。而至于雙方的人格、知識……各種,就缺乏正當的考慮,和認真確的認識,而趨于盲愛,這樣干去,不論有無環境各方的阻力,一旦熱情冷退了,思感變遷了,就會發生成不可揣測的變故,所以多數竟演成離棄的悲劇,得到不可想象的痛苦。況加以社會,和家庭的雙重壓迫,怎得不終歸失敗呢?”[10]
這篇時評指出了青年婚姻問題的一個原因:對新觀念狂熱的追求。面對新文化的激蕩,青年們往往著迷于其觀念的先進性,對于結婚之前必經的“擇偶”的程序,他們是一概不論的。而通過對《新新新聞》婚戀內容的整理,可以發現數篇討論青年男女擇偶標準的文章。時人歐陽蜀文在1934年6月1日第十四版的“男子擇妻與女子擇夫”一文中提出了六條男女通用的擇偶標準:一,意志相同;二,思想適合;三,體格健全;四,學識優美;五,無惡嗜好;六,經濟獨立。[11]
總的來說,《新新新聞》對于婚戀問題的報紙立場是在批判封建、提倡自由的基調上,對婚戀自由的實踐現狀進行剖析和反思。但站在今天的角度上來說,《新新新聞》的立場略顯矛盾,且對于婚戀自由引起的亂象的認識和分析并不徹底。
第一,精英視角過強。由于時代的局限性,當時可以秉筆為報紙書寫時評的作者大多是接受過完整教育的知識分子,這也使得《新新新聞》的婚戀評論表現出很強的精英視角,缺乏對社會各階級群體婚戀實踐的考察。如《婚姻問題之我見》《談青年婚姻問題》《擇妻與擇夫》等文章,幾篇文章的作者不約而同談到“學識對等、經濟獨立”在婚姻中的重要性。然而,怎樣達到男女雙方“學識對等、經濟獨立”的婚姻,作者們卻沒有詳細論述。一篇關于婦女職業現狀的報道詳細說明了當時時代婦女的工作境況:
“至于說到婦女的職業,雖然社會各方面為婦女開辟了許多謀生的道路……但這只能容納最少數比較有社會地位和專門技術的婦女……那些當官立學校教員的往往領不到薪金而發生生活上的恐慌;那些當私立學校教員的,其待遇又異常的刻薄……至于那些投入工廠勞動的女工,其生活之悲慘痛苦,更是不堪言狀……那些不能維持生活的女工,以及簡直不能找得工作的婦女,都最后的被迫而當娼作妓……”[12]
在義務教育難以普及、現代學校仍然較少的民國時期,接受教育的門檻實在很高,基本取決于家庭的地位和財力,且“最少數比較有社會地位和專門技術的婦女”都無法保證維持個人的生活。不難想象,這種理想化的“學識對等、經濟獨立”的婚姻愛情只能停留為一種理想中的假設,在那個時代根本不是普通民眾可以擁有的。
第二,作為對社會大眾婚姻觀建立有強大影響的公共媒介,《新新新聞》上所刊登的時事評論出的理想化特征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自身婚戀觀念的建構。其所報道的一些婚俗內容,本身就呈現出一種過度的自由,無須婚姻的程序和信條,只強調男女間的情感。
除卻此類報道,《新新新聞》上所刊登的時事評論也呈現出一種理想化的趨向,往往只從概念上推崇和贊揚婚戀自由的實踐,但除了少數幾篇在關于擇偶標準的文章,對于青年如何戀如何婚的指導文章卻數量極少。
四、結語
處于前現代向現代過渡的復雜歷史情境,民國時期的成都社會現實處處體現著新舊變易的矛盾與發展。作為近代中國最普及的大眾媒介,新聞報紙在社會接受新思想與新文化的現代化進程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通過整理分析《新新新聞》的婚姻內容,人們便可大致描摹出民國時期成都社會婚戀文化和婚戀實踐的綜合圖景,進而窺斑見豹,瞰視當時婚姻自由觀念從過度追捧到開始反思的歷史變遷。
總覽《新新新聞》的婚戀內容,《新新新聞》對婚戀文化的闡釋是現代的、進步的,在這種積極的主調之下,《新新新聞》刊載了大量反抗封建婚姻、實踐自由戀愛的案例。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新新新聞》并未忽略新舊轉型時期社會中傳統思想的遺留,而是積極推動二者的相互融合。甚至完全可以說,《新新新聞》對現代婚戀文化的建立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然而,盡管可以看到《新新新聞》對民國時期成都青年的婚戀實踐給予了一定程度的指導,但其本身呈現出一種理想化的精英視角,對青年婚姻實踐困境成因的分析淺嘗輒止,沒有實際性的幫助。
此一時期的《新新新聞》開辟了對封建婚戀觀念與婚姻習俗的批判場域,為當時的市民大眾(尤其是青年人)創造了理想婚姻生活的想象空間。然而,作為此一時代成都地區影響最大的報刊,《新新新聞》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現代婚戀文化自由至上的觀念的接受。正如上文所說,在當時那種封建思想殘余的社會,實踐新型婚姻行為的難度不可謂不大;且良好的婚姻生活并不僅僅取決于“男女雙方互相愛慕的激情”,而是和職業、家庭、文化水平等等因素息息相關。綜合來看,《新新新聞》中的婚戀新聞聚焦于贊頌理想狀態下自由結合的婚姻觀念,對真正影響現實生活中婚戀實踐的因素探討太少,其所營造出的過于理想化的婚戀觀念,或許也是當時部分青年婚戀悲劇的誘因。
參考文獻:
[1][2]王伊洛.《新新新聞》報史研究[D].四川大學,2006.
[3]新新新聞.自由婚姻的真義[N].1931-3-14。
[4]陳蘊茜,葉青.論民國時期城市婚姻的變遷[J].近代史研究,1998,(06):198-222.
[5]督理四川軍務善后事宜公署秘字第161號訓令(給新津縣知事)[Z].新津縣檔案館檔案(卷號1),1924-12-29.
[6]婦女的兩個切身問題——婚姻與職業問題[N].新新新聞,1934-7-11.
[7]安縣離婚風盛——縣府婚姻案月必數見[N].新新新聞,1932-7-23.
[8]自由婚姻的真義[N].新新新聞,1931-3-14.
[9][10]婚姻問題之我見[N].新新新聞,1934-8-4.
[11]男子則妻與女子擇夫[N].新新新聞,1934-6-1.
[12]婦女的兩個切身問題——婚姻與職業問題[N].新新新聞,1934-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