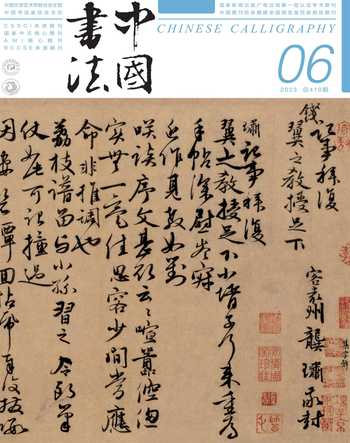《近代印人傳》與近代印學研究
朱天曙

關鍵詞:《近代印人傳》 近代印學 藝術流派 增訂本
香港馬國權先生《近代印人傳》一書修訂版經上海茅子良先生近年校訂,近日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這是近代印學研究的大工程,值得祝賀。
清代以來印人傳記的編撰
印人傳記的編撰始于明末清初的周亮工,其晚年所作《印人傳》,從文化的立場對印人做記錄,意義超越了印人本身。他飽含深情地對印人進行歌頌,把『印人』和『匠人』區分開來,肯定『印人』的文化地位和藝術地位,并首創了印人傳記的體例,開印人傳記先風,影響深遠。近代傅抱石曾說:『夫印章之學,向之目為技而小者。周秦以還,有史亦將三千年,然印人之見專錄,是書實其嚆矢。以予論之,其價值非惟空前,其用心又豈印人所限哉?』(傅抱石《讀周櫟園︿印人傳﹀》)傅抱石高度評價了周亮工《印人傳》一書的人文價值。筆者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感舊:周亮工及其︿印人傳﹀研究》一書中,曾對《印人傳》的歷史意義從四個方面加以討論:一是首創印人傳記,開印人傳記之風;二是保留大量明末清初印人生平和行跡的記錄;三是周亮工通過印章感舊,體現了明末清初文人集體的歷史和文化記憶;四是提出『此道與聲詩同』的印學思想,豐富了古代印章文化內涵。
周亮工《印人傳》之后,開啟了『印人有傳』的風氣。乾隆末年,汪啟淑撰成《飛鴻堂印人傳》八卷,繼周亮工未完成的傳記,又增加了《印人傳》未收的印人,體例也仿《印人傳》,因而又稱《續印人傳》。此傳匯集安徽、杭州及其在北京交往、聽聞的印人共一百二十九位,雖不像周亮工《印人傳》那樣描述印人和記錄與印人的直接交往,但也較完整地反映出明代后期到乾隆年間印人的活動及印風流變的情況。光宣年間,西泠印社的創始人之一葉銘,繼周亮工、汪啟淑之后,輯成《再續印人小傳》和《廣印人傳》二書。《再續印人小傳》三卷、補遺一卷為《廣印人傳》的前身,共收入元代至晚清印人六百零四人,時間跨度超過周、汪二人,但所錄印人過于簡略,明顯不及周、汪兩傳。《廣印人傳》共十六卷,補遺一卷,所輯印人上自元明,下迄同光印人,旁及女印人、日本印人,共一千八百余家。此外,馮承輝的《歷朝印識》《國朝印識》、黃學圯的《東皋印人傳》、阮充的《云莊印話》、張俊勛的《閩中印人錄》等專門記錄印人印事,或一時段,或一地域,各有特點。
一九九八年,馬國權先生在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近代印人傳》,繼承了清代周亮工《印人傳》以來的印人傳記傳統,初版收錄了從王石經、吳昌碩到吳樸、徐無聞等共一百二十五位近代印人。這次修訂版增加到一百四十人,并附錄《初版、修訂版文字對照表》,茅子良先生撰有《查證校核 力求專精》一文作為修訂版后記,也一并收錄在修訂版中。這部集近代印人傳記大成的著作,凝聚了馬國權先生潛心印學的畢生心血,也有茅子良先生潛心校訂之功,對近代印學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
近代印人的主要藝術流派和印學成就
正如馬國權先生在《近代印壇鳥瞰》一文中所說的那樣,近代印學,涵蓋辛亥革命后的一九一二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約八十余年的印章流派發展和印章理論研究。近代印壇的藝術流派,除明清以來的傳統古璽和秦漢印風之外,清代流行的『浙派』之風仍有延續。但在這一時期影響最大的,主要還是『吳派』『黟山派』『趙派』和『齊派』。根據《近代印人傳》書中所涉及的印人流派,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印人流派的發展脈絡。
以吳昌碩為宗師的『吳派』,以秦漢印風為體,將《石鼓文》書風入印,融入己意,古拙奇肆,別開生面。他的印風不僅影響了中國印壇,對于日本、韓國印壇都有影響。近代印人中,徐新周、趙云壑、趙石、陳衡恪、陳半丁、李苦李、樓邨、錢瘦鐵、王個簃、諸樂三、沙孟海、周梅谷、吳涵、吳邁、朱其石、鄒夢禪、鄧散木等,都是『吳派』的代表。以師承黃士陵印風為代表的『黟山派』,取兩周金文和漢金文變化而出,在平實中寓險峻,爽利中見古穆之氣。傳其一派的有李尹桑、黃少牧、鄧爾雅、鐘剛中、喬大壯、馮康侯、余仲嘉、張祥凝、傅抱石、孫龍父、羅尗子等印人。『黟山派』和『吳派』印風有顯著差別,其印風和當代審美多有合拍,影響至今不減。
趙之謙是近代『印外求印』的先導者,其篆刻實踐和藝術理念在近代影響深遠,傳其一脈者有錢式、朱志復、趙時棢、陳巨來、方介堪、葉潞淵、趙鶴琴、張魯盦、徐無聞、壽石工等。由于此派印風不如吳、黃、齊三家鮮明,因而傳其流派者除圓朱文外,也多未見鮮明的特色。近代印壇中,『齊派』印風在北京一地影響甚大。齊白石取法趙之謙和《三公山》、秦權的方法,大刀闊斧,單刀直入,膽敢獨造,為近代印風中面貌鮮明而獨特者。『齊派』傳人有賀培新、周鐵衡、姚石倩、劉淑度、陳大羽等,這批印人印風鮮明,開張跋扈,然也因少蘊藉而常受到世人的詬病。除了精彩紛呈的印人藝術流派之外,近代印壇在印譜編集、印史考證、印風研究、工具書編纂等方面,也都有突出的成就。
在印譜編纂上,羅振玉編有《罄室所藏璽印續集》《齊魯封泥集存》《赫連泉館古印續存》《隋唐以來官印集存》《凝清室古官印存》《貞松堂所見古璽印集》,黃賓虹有《濱虹草堂藏古璽印》,吳隱有《遯盦秦漢古銅印譜》,王光烈有《昔則廬古璽印存》,王獻唐有《兩漢印帚》,羅福頤有《待時軒印存》,高時敷有《樂只室古璽印存》等。此外,收藏家陳漢第輯有《伏廬藏印》、陳寶琛輯有《澂秋館印存》以及丁仁、高時敷、葛昌楹、俞人萃匯輯的《丁丑劫余印存》等。
在印史考證上,近代印人羅福頤先生晚年所著《古璽印概論》《近百年來對古璽研究之發展》兩書綜合探索,從文字、印紐制度等多角度對古璽印時代進行考證,還通過璽印和封泥的研究,補正官制和史志的缺失,從古璽角度推進了古史的研究。沙孟海先生《印學史》從印章起源、用途、品式和從米芾到近代印人流派的體系,對印學史精要論述,提出著名的『四輩』說,即米芾、趙孟頫和吾丘衍、王冕、文彭和何震,將印史年代提早了五百年。沙孟海先生發揮了黃賓虹等人的理論,提出『新安印派』說,推動了清代印學史的研究。
在印風研究上,近代印人王個簃《個簃印恉》、傅抱石《刻印源流》《中國篆刻史述略》、黃賓虹《印學概論》、王光烈《古今篆刻漫談》、陳師曾《槐堂摹印淺說》、馬衡《談刻印》、來楚生《然犀室印學心印》等都成為有代表性的經典之作。此外,潘天壽《治印談叢》、壽石工《篆刻學講義》、李健《金石篆刻研究》、王獻唐《五燈精舍印話》、容庚《雕蟲小言》、陳巨來《安持精舍印話》等著作,雖為講義或筆記,多有個人心得。除此之外,羅福頤《古璽文字徵》《漢印文字徵》等,不僅有助于古璽、漢印文字的研究,對印章創作來說,也多有參考。此外,方介堪《璽印文綜》、黃賓虹《賓虹草堂璽印釋文》、韓登安《明清印篆選錄》、吳隱《遯盦印學叢書》中葉銘《葉氏印譜存目》、柴子英《印學年表》等印學工具書的編纂,也都是近代印學的成果。
《近代印人傳》及其增訂本特色
馬國權先生是香港著名的書法篆刻家、理論家、文字學家,師從文字學家容庚先生。容庚先生在一九二一年曾撰有《東莞印人傳》,收錄自明代鄧云霄、袁登道至其弟容肇新等印人十九人。馬國權先生受容庚先生影響,留意閱讀印人傳記。他年輕時讀周亮工《印人傳》、汪啟淑《續印人傳》、葉銘《再續印人小傳》《廣印人傳》等,后隨容庚先生游學各地,得與近代印人來往,獲悉書本所沒有的印人軼事,資料積累漸多,進而萌生撰寫近代印人傳的想法。一九六三年起,他在教學之余,開始收集廣東地區從兩漢到明代的印學資料,編成《廣東古印集存》,同時編成《廣東印人傳》,收錄了豐富的明清至近代印人史事、生平和作品資料。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他在《廣東印人傳》基礎上,撰成六十余篇近代印人傳初稿,后陸續增補成書,書中收錄了傳記的寫作時間,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九七年。通讀全書,筆者覺得主要體現了三個方面的特色。
一是聚焦近代印人,補《廣印人傳》所未備。馬國權先生《近代印人傳》以辛亥革命后健在的印人為限,所錄一百四十人基本囊括了近代印壇的重要印人,補充了《廣印人傳》中未收的近代印人生平和文獻,成為繼周亮工、汪啟淑、葉銘三種印人傳以來的又一部印人傳記,填補了中國印學史近百年印人傳記的空白。《近代印人傳》在《廣印人傳》的基礎上,賡續前人,聚焦近代印人,拓展了印學史研究的范圍。《近代印人傳》與《廣印人傳》只錄人名的記錄方法不同,以印人傳記的形式,詳細記錄了印人的生平、藝術創作和學術研究的情況。
二是作者與近代印人和友生多有來往,征而有信。《近代印人傳》收錄的一百四十位印人中,如作者與王福庵、齊白石、馬公愚、沙孟海、容庚、羅福頤、葉潞淵、柴子英、何作朋、單曉天等印人都有直接往來,又與多位印人友生和家屬等保持密切聯系,獲得很多印人的一手資料,十分難得。如在吳樸傳中記載其『曾以稿本示余,朱墨爛然,自有印譜以來,無有逾于此者。瀕行贈余兩印,一作朱文小璽,一作漢鑄白文,俱文靜淵懿,余極珍之。』在馮文湛傳中,記載了《馮康侯印集》中的『文湛』印款,這些細微處都是一般印史中所不能詳細記載的。鄭逸梅先生在此書《弁言》中說:『君與傳主熟稔者,約占十之三四,即李不相識,一傳既成,輒就詢其后人及門生故舊,務求其翔實。』正因為如此,此書內容征而有信,嚴謹樸實而富有文獻價值。
三是評論簡練,圖版精良。馬國權先生《近代印人傳》寫作,文辭文雅雋永,評論簡練精準,將印人生平生動而準確地進行概括,不拖沓,不浮夸,對于印人的藝術成就和學術貢獻能作客觀的評述。如評印人寧斧成:『腐公之印,創造性至為突出,佳者確雄強蒼莽,氣魄過人,獨開新面。亦有篆法、章法均流于稍形怪異,未必遍邀眾堂者。』評印人陳巨來:『擬漢之作,白勝于朱,文字之增減揖讓,筆畫之并連殘損,俱經刻意經營,特見工巧,較汪關為渾穆,而比叔孺先生似又稍遜其淵雅。古璽以朱文小者為佳。』評印人余任天:『五十年代后期,自出機杼,以古隸入印,于印中較多之斜筆,能巧妙處理,求圓于方,方圓結合,故能剛健兼婀娜。先生曾在一九五五年創作自用印「余任天」一印跋中云:「畫家有潑墨惜墨,治印亦應潑朱惜朱,此印其庶幾乎?」以畫理闡印理,可稱獨有見地。』這類評論都是十分精當的,可見作者剪裁的功夫。《近代印人傳》所選印蛻圖版精良,選擇了印人較有代表性的篆刻作品,原大刊印,全書如一本近代印譜,可欣賞,可臨摹,同時結合印人傳記選讀,鄭逸梅說此書『評述其史事,采及其印論與印蛻,并及他人之評騭,圖文兼顧,對之如有親其謦欬者』,此言不虛。
上海茅子良先生與馬國權先生有多年交往,曾任《近代印人傳》一九九八年版的責任編輯。此次修訂,茅子良先生主要做了幾個方面的工作:按印人出生年月日重新編次,核補印人字號、室名、籍貫、代表作、書名、篇名、印款以及增補印人篆刻作品等,材料更加嚴謹,文字更加準確。如對初版中《吳昌碩傳》三處時間進行修訂,初版稱其『年廿九,赴杭州謁俞曲園先生』『卅四歲問畫法于任伯年』『年五十三出為安東縣令』,在修訂版中分別改為『年廿六』『卅六歲』和『年五十六』。《齊白石傳》中初版『十二歲學木工』『二十七歲拜文人胡自倬為師』『年四十,應夏午詒之邀北游陜西』,在修訂版中分別改為『十四歲』『二十六歲』『年三十九』,時間更為精確。又如《弘一法師傳》初版為『官費赴日本東京入上野美術專門學校學西洋畫』,修訂版改為『次年九月,私費考取東京美術專門學校學西洋畫』。《傅抱石傳》初版稱其『一九三五年學成歸國,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修訂版轉為『任中央大學教育學院簡任講師』等等。《近代印人傳》有初版和修訂版的出版,此次刊有修訂處相關文字對照表,為研究者深入研究近代印史提供了兩個文本,初版中有印人照片,修訂版因一些照片不夠清晰而刪去,但并不影響讀者在文字比較中鑒別和運用。
《近代印人傳》并不是近代印人的全部匯錄,亦有不少印人因各種各樣的原因,馬國權先生未能寫傳。僅舉一例,筆者的家鄉揚州近代著名印人蔡易庵、桑寶松先生即未收錄,筆者二十多年前在《書法研究》刊發文章研究過蔡易庵先生的印。二〇〇〇年九月,筆者在南京和馬國權先生相聚,提及《近代印人傳》中未收錄蔡易庵先生傳,即請來寧的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莫家良先生帶去筆者寫的介紹蔡易庵先生的文章,十月底即收到馬國權先生回信,稱:『金陵之行,得緣相晤,至幸。日昨,莫家良兄返港,帶下大作介紹蔡易庵前輩一文,謝謝。蔡老大名,前在丁吉甫先生《現代印章選集》見之,今得尊文,詳為論析,表彰往哲,用心良苦,至佩。弟遲日當據所述,草成傳略寄上。』次年六月,馬國權先生又復信:『手教及寄下《易庵印存》均已奉到,深以為謝。既詳其史事,又有二百余印,當可據以為小傳也。』可見,馬國權先生對蔡易庵先生之傳極為重視,惜二〇〇二年四月,馬國權先生即歸道山,未能見其所撰蔡易庵先生之傳,以為憾事。
梁啟超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書中提出要做『人的專史』,其中包括人物和專傳。他提出,要擇出一時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種學問、一種藝術的代表人物用作中心,把當時及前后的文學潮流分別說明,對于印人研究也是這樣。馬國權先生的《近代印人傳》選擇了近代印章藝術發展的代表人物加以記述和表彰,在近代印學研究中有著『中心』的意義。沙孟海先生在《近代印人傳》序中也說:『讀其書,識其人,同時觀賞其手跡,亦一快也。』我想,這部書不光是近代印人傳記的匯集,對于近代印學流派、印風和時代風格的研究,更是一部難得的必讀參考書和史料性工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