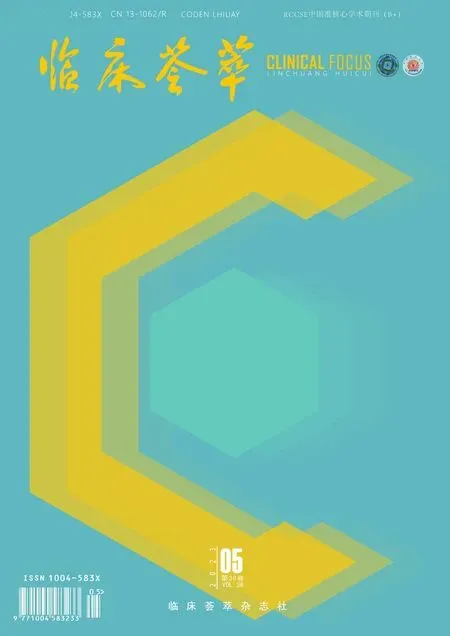瘙癢與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臨床預后的關系及風險預測
張 源, 周 娟, 黎文香, 劉金香, 湯小湄, 羅惠娟
(暨南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婦產科,廣東 廣州 510630)
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of pregnancy,ICP)是妊娠期最常見的肝臟疾病之一,它的特點是在妊娠中晚期出現無皮疹的瘙癢,伴血清總膽汁酸(total bile acid,TBA)升高,分娩后自動緩解[1-2]。一般來說,ICP在孕婦中是一種良性疾病,但它可導致不良的新生兒結局,如胎兒窘迫、羊水糞染(meconium-stained amniotic fluid, MSAF)、早產和宮內胎兒死亡[3]。TBA水平≥40 μmol/L的ICP患者胎兒風險增加[4]。國外研究者將僅TBA水平升高,不伴瘙癢和其他肝功能改變的患者定義為妊娠期無癥狀高膽汁酸血癥(asymptomatic hypercholanemia of pregnancy,AHP)[5]。目前,關于無癥狀ICP的研究還較少。一些研究人員認為它僅僅是ICP的一種特殊類型,應該同ICP一樣進行管理[6]。但也有人認為無癥狀ICP只是孕婦的一種亞健康狀態,不會增加懷孕風險,不需要特殊治療[7]。也有報道稱有或無癥狀的ICP具有不同的膽汁酸代謝,因此它們是兩種不同的疾病[8]。一直以來,臨床發現ICP是由于孕婦出現皮膚瘙癢后通過檢測TBA,并排除其他皮膚瘙癢和肝功能異常的情況得以診斷,因此,大多數此類患者都屬于合并瘙癢的ICP。由于TBA的測量已成為臨床產科檢查的常規,越來越多的患者被發現屬于無癥狀型的ICP[8]。如何定義無癥狀ICP目前仍然不清楚,國內關于無癥狀ICP的報道也較少,本研究通過比較有癥狀和無癥狀ICP與正常孕婦的產檢情況、臨床特征及胎兒預后,探討各組是否具有不同的臨床特征,評估瘙癢,TBA與圍產期發病率的相關性,以評價其在預測ICP預后中的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本次回顧性研究包括2012年7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暨南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分娩的32 633名孕婦。每位婦女在懷孕期間至少接受1次TBA檢測。
1.2納入及排除標準 診斷標準:根據中國婦產科學會《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診療指南(2015)》和英國皇家婦產科學會(2011)《產科膽汁淤積癥指南》[9],ICP的診斷標準包括:不明原因瘙癢伴血清空腹TBA水平升高(≥10 μmol/L)或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 ALT)、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partate transaminase,AST)輕度或中度升高或血清膽紅素升高;分娩后瘙癢和肝功能障礙恢復正常的。當患者無明顯臨床癥狀,僅空腹TBA升高(≥10 μmol/L),其他血清學指標無異常時,診斷為無癥狀ICP[5, 8, 10]。ICP組納入標準: 妊娠期血清空腹TBA≥10 μmol/L。排除標準為:臨床資料不完整,無法排除其他可能導致肝功能異常的妊娠并發癥,如活動性甲型、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艾滋病毒、梅毒、巨細胞病毒、弓形蟲或EB病毒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酗酒、HELLP(溶血、肝酶升高和低血小板)綜合征、皮膚疾病或膽道梗阻性肝炎。共有359例患者被診斷為ICP,其中104例為伴瘙癢癥狀ICP, 255例為無瘙癢癥狀的ICP。瘙癢癥狀可間歇性或連續發生,夜間明顯,輕、中、重度不等,分布在掌、足,有時伴發肢體軀干,伴有失眠,無皮疹。所有患者均接受隨訪,直至分娩后TBA恢復正常。對照組納入和排除標準:隨機選取同期分娩的,產檢TBA正常的孕婦。排除標準是孕期有妊娠并發癥或合并癥的孕產婦,見圖1。

圖1 研究對象篩選流程圖
1.3分組 收集完整的產檢和圍產期數據。根據診斷標準,將所有患者分為有癥狀ICP組和無癥狀ICP組。根據病程進一步分為早發型(妊娠28周前發病)和晚發型(妊娠28周后發病)2組。根據TBA水平的不同分為輕度(TBA≥10 μmol/L <40 μmol/L)和重度(TBA≥40 μmol/L)組。
1.4臨床觀察指標
1.4.1主要指標 產婦主要指標包括:瘙癢(在入院時和病程記錄中明確描述有或無瘙癢癥狀)、肝功能[包括ALT、AST、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 TBIL)、甘氨膽酸(glycocholic acid,GC)]、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分娩方式[包括正常分娩、剖宮產和陰道助產(包括產鉗和胎頭真空吸引)]。
胎兒/新生兒主要指標包括:羊水異常(包括MSAF和羊水過少)、早產(妊娠<37周,包括醫源性和自發性早產)、胎兒窘迫、新生兒窒息(pH<7.10, 5 min時Apgar評分<7)、胎兒宮內死亡(妊娠28周后的胎兒死亡)。
1.4.2次要指標 產婦的次要指標包括:分娩時的胎齡、分娩時的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妊娠次數和分娩次數以及診斷膽汁酸異常時的胎齡。
胎兒/新生兒的次要指標包括:分娩前臍帶血流量收縮壓/舒張壓比(systolic blood pressure/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S/D)、搏動指數(pulsitility index, PI)、阻力指數(Resistance Index, RI),新生兒體重和性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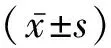
2 結 果
2.1一般資料比較 我院孕婦發生ICP的發生率為1.1%,其中無癥狀ICP較多(71.03%),其余為有癥狀ICP(28.97%)。3組在年齡、膽汁酸異常時胎齡、陰道助產率、性別比、胎兒窘迫率、羊水過少、新生兒窒息率等指標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3組間BMI、孕次、分娩次數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無癥狀ICP組孕次、產次明顯高于對照組;有癥狀ICP組BMI明顯低于對照組(P<0.05)。3組肝功能指標TBA、ALT、AST、TBIL、GC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與對照組比較,有癥狀ICP組各肝功能指標均顯著升高,無癥狀ICP組TBA、ALT、TBIL、GC顯著升高(P<0.05)。3組分娩前臍血流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均在正常范圍內;ICP組,尤其是有癥狀ICP組,臍血流值都在正常范圍的上限。有癥狀ICP或無癥狀ICP患者發生GDM、新生兒低體重和早產(醫源性和自發性早產)的風險均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有癥狀ICP組剖宮產率最高,其次是無癥狀ICP組,對照組最低(P<0.05)。有癥狀ICP組發生羊水異常(MSAF)的風險最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與對照組相比,無癥狀ICP組發生MSAF的風險無明顯升高。見表1。

表1 3組一般資料比較
2.2有癥狀ICP組與無癥狀ICP組臨床資料比較 大多數患者為輕度無癥狀ICP,占54.6%。重度無癥狀ICP在妊娠28周前確診的患者多于其他組(P<0.05)。重度組剖宮產率高于輕度組,輕度無癥狀ICP陰道分娩率最高,與其他3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盡管各組間總體早產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在醫源性早產組中,輕度無癥狀ICP組的早產率最低(P<0.05)。重度有癥狀ICP組羊水異常明顯高于其他組(P=0.025)。本研究中有2例胎兒宮內死亡: 1例為遲發性重度有癥狀ICP,妊娠至36孕周死胎引產,1例為遲發性輕度無癥狀ICP,妊娠至34孕周發生死胎,胎死宮內后發現膽汁酸升高,然而,組間胎兒宮內病死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此外,各組在胎兒窘迫和新生兒窒息方面差異也無統計學意義,見表2。

表2 有癥狀ICP組與無癥狀ICP組的臨床資料比較[例(%)]
2.3ICP圍產期發病率的危險因素分析 采用Logistic回歸預測圍產期發病率(包括胎兒窘迫、羊水異常、胎兒宮內死亡、剖宮產和新生兒窒息)。結果表明:瘙癢發生率、TBA值與圍產期疾病呈正相關(校正OR2.576、1.033; 95%CI分別為1.501~4.422, 1.020~1.046)。按TBA值分為0~9.999 μmol/L、10~19.999 μmol/L、20~29.999 μmol/L、30~39.999 μmol/L、≥40 μmol/L 5組。以0~9.999 μmol/L組為參考組,與其他4組比較。結果顯示,圍產期發病率以對照組最低(33.83%),TBA≥10 μmol/L時顯著高于對照組(TBA為10~19.99 μmol/L、20~29.9999 μmol/L、30~39.9999 μmol/L和≥40 μmol/L時發病率分別為65.16%、67.01%、53.85%、80.60%)。見圖2。
有癥狀ICP組和無癥狀ICP組圍產期發病率隨TBA值的增加而增加,其中有癥狀ICP組TBA≥40 μmol/L時發生率最高,增加12.047倍(無癥狀ICP組增加6.302倍)。見表3。

表3 ICP圍產期發病率的危險因素分析
3 討 論
目前,ICP引起瘙癢的原因尚未明確,有研究指出一些內源性化合物可能作為瘙癢的生化介質,次級膽汁酸可激活感覺神經上的 G 蛋白耦聯膽汁酸受體1(G protein coupled bile acid receptor 1, GpBAR1)刺激脊髓內瘙癢選擇性神經肽釋放,引發GpBAR1依賴性瘙癢反應[11],但無癥狀ICP患者次級膽汁酸未見升高,故可能無明顯瘙癢。西班牙的1項研究發現,大多數ICP患者屬于無癥狀ICP[8]。Lunzer等[7]研究表明只有48%的血清GC顯著增加的孕婦有皮膚瘙癢。當患者妊娠早期肝功能正常,妊娠期無瘙癢時,很可能忽略常規膽汁酸檢查,大量無癥狀ICP病例可能被漏診。如果考慮到遺漏的無癥狀患者,ICP的實際發生率可能更高。然而目前對于孕期TBA的檢測頻率暫時沒有臨床建議。在本研究中,無癥狀ICP占總ICP的71.03%,近一半的重度無癥狀ICP發生在妊娠28周之前。在過去的研究中發現,血清膽汁酸和妊娠早期出現瘙癢是早產的獨立預測因素[12]。以上結果提示,整個孕期應定期進行TBA監測,特別是高危孕婦,如有產科膽汁淤積癥史、原因不明死產、病毒性肝炎、雙胎或GDM病史的孕婦,以避免漏診無癥狀ICP患者,特別是嚴重早發型無癥狀ICP患者[13-15]。
本研究表明,有癥狀ICP或無癥狀ICP的孕婦合并GDM的風險都會增高,可能與胰島素抵抗和激素的變化導致孕期母體脂質代謝的改變有關[16]。因此,ICP也被認為是一種代謝性疾病[17-18]。有癥狀ICP患者發生早產和剖宮產的概率在所有組中為最高。雖然無癥狀ICP組僅TBA和GC升高,但剖宮產和早產(醫源性或自發性早產)的發生率均高于對照組。因此,無癥狀ICP也是一種增加圍產期發病風險的病理狀態,需要臨床醫生的重視。
預防圍產兒死亡是ICP孕期管理中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大多數研究支持妊娠37~38周后ICP患者可考慮積極分娩[19-22],但并非所有產科專業人士都同意積極治療的概念[23]。由于隨著產科質量的普遍提高,ICP圍產兒死亡率與整體圍產兒死亡率相比,并沒有明顯增高。一些研究表明,積極的治療可以降低圍產期嬰兒的死亡率,但也有研究提出不同意見[24-25]。由于缺乏來自隨機臨床試驗的證據來支持主動引產可以避免宮內胎兒死亡的結論,目前指南建議為患者提供知情決策指導的個體化管理,而不是常規實施主動管理方案[26-27]。醫務人員應向患者清楚地提供科學證據,包括現有管理方案的風險和好處,共同作出何時分娩的決定[9, 28]。本研究中,無論輕度或重度、有癥狀或無癥狀ICP,無征兆的宮內胎兒死亡都有可能的發生,但ICP組與對照組并無明顯差異。積極的治療,包括藥物治療,嚴格監護胎兒,及時發現羊水異常和(或)肝功能異常加重,及時終止妊娠,可能是本研究中各組胎兒窘迫和新生兒窒息率無差異的原因。
ALT在無癥狀ICP組中在正常范圍內,但高于對照組。由于血液稀釋,整個孕期的轉氨酶和膽紅素,正常上限比非孕期低20%[29]。本研究結果表明,有癥狀ICP患者的肝功能異常更常見,也更嚴重,而無癥狀ICP患者的肝功能也受到影響,但仍在代償范圍內。這些結果提示無癥狀ICP可能是一種輕微的產科膽汁淤積癥。與對照組相比,胎兒產前臍血流有所增高,尤其是有癥狀ICP組,但仍在正常范圍。因此利用胎兒臍血流預測ICP胎兒慢性缺氧仍十分困難。這些結果表明,胎盤血管的損傷可能還在代償范圍內或膽汁酸可能還存在其他損傷胎兒的機制。有研究報道膽汁酸對胎兒的直接損害能通過抑制肺表面活性劑的產生或直接損傷胎兒心肌,導致胎兒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甚至在子宮內死亡[30-31]。
值得注意的是,49.15%的嚴重無癥狀ICP病例發生在妊娠28周之前。有證據表明,早發性ICP與不良結局風險呈正相關[32-33]。重度無癥狀ICP和輕度或重度有癥狀ICP患者的剖宮產和早產率明顯增高,可能與醫源性的干預有關。
在分析圍產期發病率與臨床指標的關系時,本研究發現瘙癢、TBA濃度與圍產期嬰兒預后呈正相關。有癥狀ICP的圍產期發病率增加2.576倍。當TBA≥10 μmol/L時圍產期發病率顯著增加。TBA 30~39.999 μmol/L組圍產期發病率雖升高,但無明顯差異,可能與本組病例較少有關。當TBA≥40 μmol/L時,圍產期發病率明顯升高,這與其他研究一致[34-35]。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同的TBA水平下,有癥狀ICP組的新生兒風險明顯高于無癥狀ICP組,有時甚至高出數倍。這些結果表明無癥狀ICP的預后優于有癥狀ICP。在ICP患者中,輕度無癥狀ICP的預后最好,剖宮產和早產率也是各ICP組中最低的,可見TBA濃度和瘙癢與預后可能都有關系。
綜上所述,ICP是妊娠期的嚴重并發癥。無癥狀ICP在我國南方相對常見。有癥狀ICP與無癥狀ICP雖然臨床風險相似,但無癥狀ICP常表現為輕度ICP,有較好的圍產期結局。胎兒宮內死亡在有癥狀ICP和無癥狀ICP中都可無預警發生,因此,瘙癢不應成為診斷ICP的先決條件。妊娠期間應定期檢查TBA等肝功能指標,特別是高危孕婦,以防止誤診無癥狀ICP。雖然目前沒有胎兒監護的標準方法,但適當積極的產科干預可能減少不良圍產期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