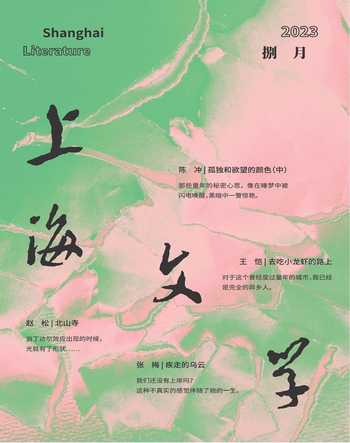命名的重要性
默音
剛走入《亞丁的羊》的世界,我想到的是《沙丘》,不是導演維紐瓦倫不知為何渲染了“二戰”德意軍隊審美的古怪電影,而是弗蘭克·赫伯特的原作。那與其說是科幻小說,更像是描述古老傳說的奇幻。擁有沙蟲的星球的生態成謎,男主角穿行于此刻與未來,漸漸分不清現實與預言。《沙丘》六部曲的節奏緩慢,我在中途挫敗,喪失了將其讀完的決心。好在《亞丁的羊》簡潔明快得多,短篇的“底”很快便展開在讀者眼前,圖窮匕見的瞬間,想必你會和我一樣感到釋然,又有些不忍。
若說內核,這個故事關于曾經輝煌的文明如何遺忘了自身的來路,其后代在沒有資源(最主要是缺水)的龍骨爾星上過著胼手胝足的生活,外星來客雖短暫地映照出他們的匱乏,并試圖給出解決之道,善意導致的卻是更大的不便。植樹、造廁所,這些朝向“文明”的努力并未顧及當地早已刻進每個人生存本能的禁忌,對原本就珍貴的水資源造成進一步侵蝕。類似的事情當然也在我們的生活圈外發生,讓人不禁試圖反思,“先進”的國家或地區幫助“后進”,所行之事有多少是自以為是,又有多少真正為當地人帶來福祉?
主人公亞丁是個女孩,和生活在沙化星球上的父母以及同伴們一樣,她有四只手。在她看來,外星來客是只有兩只手的殘疾,他關于未來生活的許諾也顯得空泛。他帶來的羊則是真實的。沒有人見過羊,那同樣是湮沒在傳說中的事物,而她認定他身邊的動物就是。
當我們目睹亞丁在羊的生命最后階段為拯救它做的種種努力,不難由此推斷出,在過去的十五年間,她如何艱難地從女孩長成少女。她和星球上其他人不一樣。和外星來客的短暫接觸間,她學會了不認命。無論是父母還是被稱作站長擁有對外通訊權的男人,在內心深處都沒把曾經停留在他們星球并帶來麻煩改變的外星人當回事。“我那個聯絡站早就不頂事了。”“外邊的人不管我們了。”他們并不費心去仰望天空,眼前只有今天明天,活一天算一天。亞丁則是不同的。她有羊。她期待看外面的世界。她想知道更多,也試圖改變。
作為讀者,我愿意多讀一萬字關于龍骨爾星的描述。請原諒我這個外來人不合時宜的好奇心。亞丁和她的羊,她的日子,那么磕磕絆絆又那么光彩照人。所謂的羊是她的命名,盡管外星人告訴過她那是什么。
世界不就存在于我們將其命名的時刻嗎?正是名字讓我們與外物有了連接。亞丁并沒有給她的羊取一個更有私人意味的像寵物的名字,而是用一個大類、一支早已消亡的種族為其命名。這背后藏著作者敏銳的直覺。當面對完全陌生的事物,我們總是試圖用自己原本知道的名詞來將其概括,如此便能消弭陌生,建立聯系。作為更接近“外星人”的讀者,你或者我,當然早已在細節中認出了亞丁的羊究竟是什么,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復雜的情感,想笑,又有些不忍。當亞丁在心里呼喊“十五歲的羊怎么會老”,隔著文字織就的時空阻隔,我們只能嘆息,無法告訴她更多的真相。
來自外星的勘測者李數用羊交換了亞丁身邊的一件小物品,彼時,他和她都不會想到,這項交換將改變許多星球的未來。科幻的澎湃感隱藏在龍骨爾星上一個女孩為羊掙扎的一天背后,李數和亞丁關于孤單的對話,想必在宇宙間的各個角落重復過無數次,此后同樣的對話還將不斷在此處和彼處響起。
而最終,孤單會愈合。當你從茫茫宇宙中遇到一個陌生的事物,并為之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