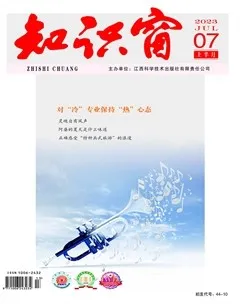只是用花作衣裳
木小易

這是前幾天偶然經過的一家店鋪——棉花記,一個很溫暖的名字,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走進店內,古樸典雅的裝飾叫我眼前一亮,一件件簡單純樸的衣服,都是純棉的材質,或灰,或白,或淺紫,沒有過多的修飾,只繡著一兩朵精致的花。一件件衣服空靈飄逸,像遠離塵世的仙子,靜靜地盛開在這個熙熙攘攘的塵世間。
我輕輕地撫摸著衣服純棉的質地,柔軟細膩。淡淡的顏色,微微的清香,舒適的觸感,天然的本質勾起了我久遠的回憶,回憶里是母親飛針走線的身影,親手縫制的棉鞋,還有盛開的潔白如雪、輕盈如云的棉花。
棉花是齊魯大地上常見的經濟作物,而我的老家就在齊魯平原的一個小村莊里。記憶中,每年的春末夏初,母親都會把幾天前泡發好的棉籽,一顆顆種植到翻好的土地里,細心地用薄膜覆蓋好,直到棉籽長出頂著兩片葉子的嫩芽。這時,有些葉子就頂破了那層薄膜,舒展著身軀,有些葉子還蜷縮著身子。母親會用一個細長的鐵鉤子,小心翼翼地幫嫩葉鉤破阻礙它生長的薄膜。母親低著頭,弓著腰,一天下來腰酸腿疼,眼也花,但不敢有絲毫的馬虎,因為她知道這一棵棵嫩苗不僅能換來豐厚的經濟回報,還能換來大人、孩子穿在身上抵御冬季嚴寒的棉衣褲。
一整個夏季,噴藥,除草,施肥……母親就這樣耐心地、細致地照料著這些棉花。到了開花的季節,一朵朵乳白色的花朵迎著朝陽次第開放,乳白的花瓣、淡黃的花蕊,放眼望去,連成一片,蔚為壯觀。
到了棉花收獲的季節,田野里到處都是花紅柳綠的身影,大家嘻嘻哈哈地在田地里摘棉花。棉花的采摘是有講究的,摘早了,棉花纖維尚未充分成熟,產量和品質不高;采摘過晚,會降低棉絮的纖維拉力,色澤也不好。
母親勤快地摘棉花,而我只是借著摘棉花的由頭來玩鬧,只求速度,不求質量,專揀和我身高差不多,開得大朵的棉花下手,葉子底下藏著的棉花總是被落下,最后都被后面的母親一點點收拾干凈。不一會兒,我就被母親呵斥著去休息,于是高興地躺在母親摘下來的堆成山的棉花堆上曬太陽,瞇著眼睛看藍天白云,腦海里暢想著自己的未來,是那么愜意和美好。這棉花軟軟的、柔柔的,帶著太陽的清香和母親的溫暖。
采摘下來的棉花被父母拉回家中,成片成片地曬在院子里,晾曬干透的棉花一部分被父母賣掉,一部分被紡成棉絮,留待冬天做被子、棉衣褲、棉鞋。
母親的手很巧,扯上一塊紅底白碎花的棉布,裁剪好尺寸,絮上新軋好的棉花,幾趟飛針走線下來,一件暖和的、柔軟的小棉襖就做好了。兒時,我最喜歡看母親做衣服和鞋子,不僅是為了看母親魔法般的手藝,更多的是借著機會去觸碰被軋成云朵般輕柔的棉絮,看著它們神奇地在母親手下變成漂亮的被褥、合腳的棉鞋。母親親手做的棉鞋、棉衣褲穿在身上,那種輕柔貼心的溫暖,是一輩子都忘不了的感覺。
如今,母親親手縫制的棉衣、棉褲、棉鞋都留存在久遠的記憶里。而棉花的天然、輕柔、純凈、舒適正在無聲無息地深入人心,就像現代詩人葉千華所作的《棉花》詩一樣:“花開不為人贊美,花放不求誰聞香。 只是獻花送溫暖,只是用花作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