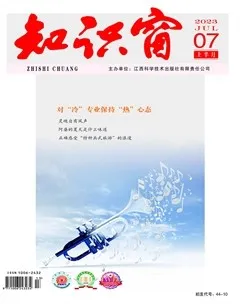正確感受“特種兵式旅游”的浪漫
黃小邪

繼21天練出馬甲線,3天學會一門外語,1部手機教你掌握編程后,一天逛8個景點睡3小時的“特種兵式旅游”火了。所謂“特種兵式旅游”,是在當下年輕游客,尤其是大學生中興起的一種集時間短、景點多、花費少等特色于一體的旅游方式。人們會在雙休日或短暫的假期出行,高效率游玩各大景點,且佐以美食、美景打卡心得分享,令諸多慣于朝九晚五與偶有假期的“同類”效仿。簡而言之,假期越短,玩得越狠。只要尚有余票,天涯海角,無遠弗屆。
“特種兵式旅游”不但成為流量密碼,而且衍生出一系列旅游后的修復指南,例如如何正確緩解疲勞,如何補充營養,如何預防腸道疾病……總之,有限的假期和賬戶余額并不能鎖住年輕人想要探索世界的心。
2023年初的青藏高原,一群踐行“青春沒有售價,硬座直達拉薩”的青年人,靠著“開局一個人,隊友全靠撿”的決心直奔藏區,硬是將原本44小時火車進藏的漫長旅程,變成一場不想下車的原地K歌活動。綠皮車廂內,素不相識的青年人一路歡歌,邂逅五湖四海的朋友。
但是很快,有人嘲諷:“怕是‘花唄干到拉薩。”言外之意,諷刺窮游。更有媒體評論:“蜻蜓點水式的‘特種兵式旅游,完全失去了旅游的初衷,是極為草率、粗糙、淺顯的‘光旅不游,無論是對當事者本人的時間和經費,還是對景區等方面的社會資源,都是一種浪費。”這些言論先不論對錯,但顯然失之偏頗。
在中國古代,無數文人墨客效仿孔子游學傳道,如果車、馬、驢都無,索性徒步出行。從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到唐代經歷長期流放也不忘游山玩水的柳宗元,乃至寫下60萬字游記的徐霞客,他們的窮游經歷未嘗不值得當下年輕人效仿。所以,對看似極盡壓榨自己的“特種兵”,我們不妨理解為他們在用自己的方式隔空致敬先賢。
2023年5月1日之前,表妹約我同游,計劃是先去濰坊放風箏,再去淄博吃燒烤,有票的話再去黃山走走。至于爬山大可不必,我們到達山腳看看就行,主打一個“我來過”。鑒于上周表妹剛利用周末從南京坐廉價航班去北京,在一天時間內逛了故宮,又在雍和宮拜了佛,在鳥巢吃了飯,在明城墻遺址賞過梅花,以及在天黑之前完成了學校布置的作業,所以我對她的周密規劃十分信任。但是不湊巧,我臨時出差,便失約了。假期結束后,我問及她的行程,被告知十分愉快順利,且在原計劃外,她通過社交平臺搭靠譜的順風車去太湖看了日落。這就是典型的“特種兵式旅游”。
“這樣能玩得盡興嗎?”我問。
“花少點錢,看日升月落,看大好河山,回來再繼續好好學習,這不就是盡興嗎?”表妹回答道。
至此,我對年輕人的豁達佩服得五體投地。是啊,為什么要狹隘地下定義?我們常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但讀書與行路,只要有價值,怎么讀,怎么走,是各人自己的事。
某旅行平臺數據顯示,2023年4月4日至5日,有62%的年輕游客選擇了夜間出發的航班和火車。“特種兵式旅游”是發展的必然,一方面,因為社交媒體的推動;另一方面,年輕人越來越注重體驗感。未必玩不起,而是日趨完善的社會環境、交通、社交媒體等提高了出行效率,年輕人日漸豐富、成熟的內心,也足矣懂得分辨自己要什么。
我也曾以“一個人行走的范圍,就是他的世界”為核心思想,以“效率最大化”為行動指南,坐2天的綠皮火車硬座去漠河,7天內踏足歐洲5個國家,在機場打地鋪完成環東南亞旅行,周末騎車去漁村看日出,再拼車回到公司完成演示文稿,甚至目前的合伙人也是幾年前在歐洲夜火車上“窮游”結識的當時正值“間隔年”的同齡人。直到今日,我依然愿意從繁雜的日程中抽出身來,選擇這樣的出行方式,且從不認為“特種兵式旅游”對成長有著負面的影響。
當然,也有一些年輕人想標新立異,最終陷入“盲從”的困境。但毋庸置疑,出去走走絕對比在家刷手機、玩游戲更佳。
“30小時往返650公里游6個景點”“33小時速游北京”“2天1夜玩轉新疆”“24小時吃遍全國各地美食”的動態均屬實。有人說,“特種兵”有著過人的體力與執行力,這樣的旅行很有趣;也有人說,走馬觀花的趕場旅行,除去遭罪,無意義。但旅行本就是獨立個體踏上旅程,探索世界、發現自己、尋找同類的過程。
旁人看到的種種“出格”之處,乃是旅行者創造條件,用自己的方式踐行心之所向,這其中包含了對自己的信任,對社會環境的信任,對大千世界的信任。
所以,偶爾做做“特種兵”又何妨呢?人生短短三萬天,哪用時時刻刻都要求沉浸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