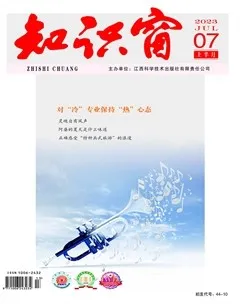細處即妙處
楊海亮

汪曾祺有一篇短篇小說,叫《鑒賞家》。文中的“鑒賞家”是葉三,一個水果販子。也許你不信,可讀完小說,你還不能不信。
例如,畫家季陶民畫完了畫,把畫釘在壁上,自己負手遠看。季陶民問葉三:“畫好不好?”葉三說:“好。”季陶民問:“好在哪里?”葉三答道:“紫藤里有風。”季陶民說:“唔!你怎么知道?”葉三說:“花是亂的。”季陶民大悅,提筆題了兩句:“深院悄無人,風拂紫藤花亂。”
又如,季陶民畫了一張小品—— 《老鼠上燈臺》。葉三說:“這是一只小老鼠。”季陶民問:“何以見得?”葉三答:“老鼠把尾巴卷在燈臺柱上。它很頑皮。”季陶民說道:“對!”
小說中的葉三只是一個賣水果的攤販,可干行當跟他懂不懂畫沒有必然聯系。他是確確實實把畫看了個仔細,知其然,還知其所以然。所以,葉三是個內行,是名副其實的“鑒賞家”。
不過,小說里的季陶民也是厲害的人。你想,那紫藤,如果不是風從中過,花豈是亂的?那老鼠,如果不是小巧玲瓏,哪兒有勁繞圈?可見,畫家的細微之處,也正是畫家的了得之處。
我不由想起熊亮的繪本。我陪兒子樂為讀《武松打虎》,讀著讀著,樂為說:“爸爸,你看,武松貓都沒有碰到老虎貓。”果然,畫面里,劈啊,戳啊,敲啊,打啊,都是武松貓的“假”動作。再往后看,是老虎貓與武松貓各自在后臺的炫耀。老虎貓說:“你們知道嗎?我的表情可都是裝出來的。我就這樣、那樣,這樣、那樣!”武松貓很不服氣地說:“我武松的本事也不小啊,我從來沒有真正打著他。你們仔細看,我一點兒都沒碰過他。”這么看來,都說小孩子最喜歡也最善于捕捉細微之處,這話還是有幾分根據的。
一般說來,繪本有好的故事和圖畫已經很不錯了。繪者還能在細微之處花心思,那就更難得了。恰恰是這細處,也是妙處,奇妙,巧妙,妙趣橫生,妙不可言。
不僅是畫畫,別的事情如果在一個“細”字上做足了功課,往往也是令人稱“妙”的。掃黑除惡題材的電視劇《狂飆》好評如潮,里面演反派的演員張頌文更是一夜之間廣為人知。劇中,張頌文扮演的角色最初是賣魚為生,被人欺負,弄得鼻青臉腫。據說,這里有一個細節是張頌文自己設計的。為了表現人物有多慘,他沒把臉弄得血肉模糊,而是借助一個紙團。在公安局做筆錄時,他臉上的血漬已經清理了,但鼻孔里還塞著紙團。張頌文說,塞鼻子的紙團不能一下子全紅,得慢慢紅。于是,我們看到劇中那個紙團從一半紅一半白,到慢慢浸染,再到完全紅透。你看,好演員就是這樣,無“微”不至,這樣演出來的人物自然接地氣,聚人氣。沒有熱愛,沒有細心,演員怎么能做到這樣?
《狂飆》中還有一個吃面的場景,張頌文也設計了不同的細節。這個角色從前是個魚販子,吃面時會用手抹嘴,會加辣椒,會多叫一碗,甚至會在不得不走時,再伸長舌頭嘬上一口,后來成了大老板,他用紙巾狠狠地擦拭筷子,用紙巾抹嘴,什么也不放,還愛吃不吃。所有的動作設計都合乎人物的身份、心理,無一處偏離,無一處作假。這樣的表演,實在令人嘆服!
“細節決定成敗”這個道理很多人都懂,可做起來時,人們往往以“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來搪塞,結果忽視細節。而真正把細節做好了,細處即妙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