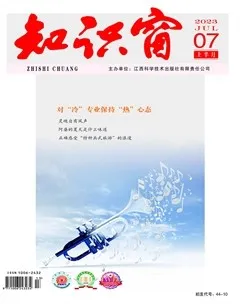平民春鮮第一魚
王偉

太湖流域孕育了一百多種淡水魚,常見的有“四大家魚”和鯽魚、鳊魚、鯉魚、白魚、黑魚、銀魚、鱖魚、黃鱔、梅鱭魚等,剩下的都是小眾魚類。小眾魚類中,既有數量稀少、難以加工的河豚,又有個小肉少、刺多易鯁的穿條魚,還有行動遲緩、食之無味的鳑鲏,但要論起最有個性的,非昂公魚莫屬了。
昂公魚扁頭闊嘴,黃膚無鱗,長約15厘米,重約150克,體表有不規整的黑斑,白天潛伏于水體底層,夜間浮游至水面覓食,背鰭和一對胸鰭各長著一根叛逆的堅硬尖刺,相貌甚是丑陋。昂公魚出水后,易受驚發怒,三根硬刺雄赳赳地挺立起來,嘴里發出“昂嗤昂嗤”的奇怪聲音,因此被上海人叫作“昂嗤魚”。然而,昂公魚的硬刺有微毒,刺緣有細密鋸齒,用手握魚多半會被刺傷,鉆心的疼痛直讓人整宿難眠。老手會把拇指和中指置于昂公魚的胸鰭下面,食指輕輕按在其背鰭側面,用手掌托住魚肚子,便可相安無事,所以南京人稱其為昂刺魚,不但音似,而且能意會,還能用來形容不好惹的人。
其實,昂公魚只是無錫人的叫法,其學名叫作黃顙魚,鲇形目鲿科黃顙魚屬。昂公魚適應能力極強,分布在從西伯利亞到中南半島的東亞水域。昂公魚在國內各地居然有兩百多種叫法,四川人叫黃辣丁,湖北人叫黃嘎子,湖南人叫黃鴨叫,廣東人叫黃骨魚,安徽人叫黃丫魚,山東人叫吱呀魚,東北人叫嘎牙子……如此多的別稱,恐怕沒有哪種魚能出其右。
刺頭歸刺頭,倒不妨昂公魚滋味鮮美。常規做法是一勺菜籽油熱鍋,倒入昂公魚與蔥花、生姜刺啦翻炒至魚皮焦黃,再倒入花雕酒和冷水,大火伺候,水燒開后改小火慢慢燉,十五分鐘后湯色乳白。捧碗在手,吮湯入口,滋溜一聲,味蕾生花,香入肺腑。很多年前,我在吳江鄉下見過農家秘制昂公魚拌菜飯,將洗凈開膛的昂公魚背刺釘在木頭鍋蓋背面,底下大鐵鍋燒飯,蓋上鍋蓋后大火煮沸,小火燜燒,柴火燒盡時掀開鍋蓋,上面只留下了完整的骨架,白花花的魚肉掉落白米飯上,澆上炒熟的蔬菜和蘿卜干一起拌勻,俄頃,魚香、飯香、菜香裊裊繞屋,還未開吃便令人胃口大開。而上海石庫門人家常用咸菜、豆腐和昂公魚一起燉,細細品,慢慢咂,平平緩緩,余味悠長,猶如阿姆娘正在耳邊低語。
老家高郵的汪曾祺曾在江陰讀過高中,也喜歡這道水鄉美味,他在《故鄉的食物》中這樣描寫:“昂嗤魚通常也是汆湯,虎頭鯊是醋湯,昂嗤魚不加醋,湯白如牛乳,是所謂‘奶湯。昂嗤魚也極細嫩,腮邊的兩塊蒜瓣肉有大拇指大,堪稱至味。”誠如其所言,昂公魚的精華在于這兩塊蒜瓣肉,上漿后滑炒,加青椒、荸薺、筍片,略施鹽,勾薄芡,滴上少許麻油后起鍋裝盤,色澤淡雅,嫩滑鮮美,格調高雅。
人間煙火味,最撫凡人心。《詩經·小雅·魚麗》中記載:“魚麗于罶,鲿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鲿指的就是昂公魚。把酒言歡,豈不快活?今日的江南,菜場里常有賣昂公魚的,以春秋兩季最多,滋味也最肥美,無愧于“平民春鮮第一魚”之稱。世間萬物唯有美食不可辜負,從童年到晚年,星星點點連線著我們成長的軌跡,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