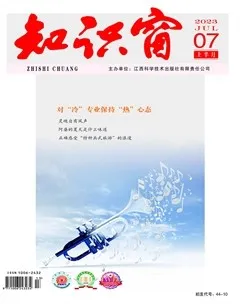聲聲慢
月下嬋娟

《聲聲慢》這詞牌有好幾個別名,《勝勝慢》《人在樓上》《寒松嘆》《鳳求凰》……無論曾為此填詞的名家有多么大的手筆,如賀鑄詞“殷勤彩鳳求凰”,得來“鳳求凰”;“韓松半欹澗底”,便名“寒松嘆”;吳文英寫“人在小樓”,便有“人在樓上”。私以為,綜上所述的所有名字,皆沒有“聲聲慢”這三個字來得美麗貼切、纏綿婉轉。
千年之后的我們早已不能再聽見光陰深處迤邐悠遠的吟唱,是如何一聲慢過一聲的曲折凄涼。唯有那些妙筆生花的文字,遺留下來的篇章,讓我們窺見,化百煉鋼為繞指柔的婉約詞,曾道盡多少兒女情長。
在可考證的記錄里,聲聲慢,最早見于北宋的晁補之筆下,這個剛懂事就會寫文章的神童曾令東坡居士擱筆贊嘆。一百多年后,由晁補之創作的《勝勝慢》,因為蔣捷的一首《聲聲慢·秋聲》,才最終變為《聲聲慢》。
黃花深巷,紅葉低窗,凄涼一片秋聲。豆雨聲來,中間夾帶風聲。疏疏二十五點,麗譙門、不鎖更聲。故人遠,問誰搖玉佩,檐底鈴聲?
彩角聲吹月墮,漸連營馬動,四起笳聲。閃爍鄰燈,燈前尚有砧聲。知他訴愁到曉,碎噥噥、多少蛩聲!訴未了,把一半、分與雁聲。
——宋·蔣捷《聲聲慢·秋聲》
雨聲,風聲,更聲,鈴聲,彩角聲,笳聲,砧聲,蛩聲,雁聲,這聲聲夾雜的凄涼秋聲,一聲聲斷人肝腸。
竹山先生蔣捷深懷亡國之痛,隱居不仕,氣節為人千古傳誦。這闋詞俱用“聲”字入韻,得名“聲聲慢”名副其實。傳說里,他為“聲聲慢”正名,而我總覺得他該是屬于“虞美人”的。蔣捷少年聽雨歌樓上的旖旎,壯年聽雨客舟中的漂泊,暮年聽雨僧廬下的蒼茫,人生的悲歡離合被他的《虞美人·聽雨》一一寫盡。又或者,蔣捷是屬于《一剪梅·舟過吳江》的,是那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的“櫻桃進士”,一片春愁,無一字不美,無一字不令人思歸。
而“聲聲慢”屬于誰呢?
當“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這十四個疊字浮現于腦海,你當會記起李清照清雋秀麗的名字。李清照,好像她身上任何一個名號都足以光耀后世:千古第一才女,詞國皇后,藕花神。她的少年時代是一曲活潑嬌憨的《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青年時代是與如意郎君情投意合的《點絳唇·蹴罷秋千》。《減字木蘭花·賣花旦上》里的“云鬢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是花面好看還是奴面好看?還有《丑奴兒·晚來一陣風兼雨》里的“笑語檀郎”,《醉花陰·薄霧濃云愁永晝》里的“人比黃花瘦”,《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中的“一種相思,兩處閑愁”。那些年,她信手拈來無數詞牌,闋闋都成為絕唱。后來,國破夫亡,她顛沛流離,無依無靠,晚景凄涼。她的人生從風月情濃的最美麗處陡然跌落,便四散成一曲《聲聲慢·尋尋覓覓》的憂愁與荒涼。
疊詞疊加的是李清照無以細訴的愁怨,舊時“云中誰寄錦書來”的大雁,再也捎不回來愛人的書信,滿地的黃花瘦盡年華。某年某月,她和他曾對坐窗前,賭書潑茶。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她還要獨自挨過多少這樣的辰光。
這世間,完美的是詩詞,千瘡百孔的是人生。那一曲“聲聲慢”,要怎樣的凄涼,怎樣的句句哀婉,才能夠唱盡李清照的血淚和相思。
聲聲慢,在這黃花深處的秋天,聽一夜細雨滴落梧桐,如聽一個多情哀怨的女子,為我們留下的斷腸詞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