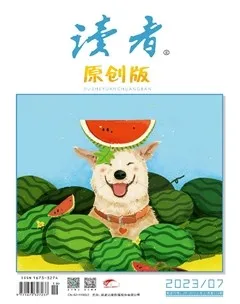削皮刀與被套
楊穎
小時候,在我的生活圈子內盛傳著這樣一個說法:成年后的我們將面臨一場“考試”—去男朋友家,對方的母親在和你打過招呼、讓你坐下后,會遞給你一個大蘋果、一把水果刀,潛臺詞是:“來,吃個蘋果吧!”
“考試”內容便是削蘋果。據說心靈手巧、秀外慧中的女孩兒,能削得又快又好,削下來的蘋果皮既薄又不會斷。一條長長的蘋果皮便成為標簽,成為有教養和“會過日子”的代名詞,也許在未來婆婆那兒,更是成就第一印象的關鍵。
我自然不精于此道。每次吃蘋果,我都是直接對著水龍頭沖沖便送入口中;即便要去皮,也不過拿著刀裝模作樣,這兒刨一塊兒,那兒刨一塊兒,把蘋果削得坑坑洼洼的。好幾次我都因此被大人訓斥—一只蘋果被你削得一半果肉都在皮上,以后怎么去相親,怎么上門?
是啊,怎么相親?怎么上門?
若干有憂患意識的同輩在家苦練削蘋果皮。她們總結了訣竅:左手要穩,穩穩握住蘋果,用大拇指按住蘋果柄的部位;右手要準,拿著刀,準確判斷皮與肉之間恰到好處的位置,一刀下去,屏息凝神,順時針削;左右手打好配合,左手轉動蘋果,右手隨之推動刀刃,一圈一圈,蘋果皮便如波浪,層層涌起,再均勻滑落。
一次,我見隔壁小姐姐拿不銹鋼勺子刮土豆皮,受到啟發。于是,無數個夏日下午,我們一起刮土豆,刮黃瓜,刮蘋果,刮任何可刮之物,為了口腹之欲,也為了“考試”。
成年后,當我在超市看到削皮刀時,松了口氣,有種老天開眼的感覺,雖然,此時的我,早已學會不在意任何對性別有設定要求的“考試”。后來,純為生活方便故,我成了各種削皮刀的愛好者。
我擁有的削皮刀如下:一個電動削皮器,包含3個刀頭,削皮、削片、削細絲,都能輕松駕馭;一把挖杧果的大勺,讓果肉和果皮瞬間完整分離;一把專為西紅柿去皮的;一把專為菠蘿卸去盔甲的。
手搖的、電動的、立式的、折疊的,我都用過。個中妙處,只能用四個字形容:如有神助。“神”是工具,是不斷進步的科技。用一句話來贊嘆:這真是人類最美好的時代!
與削皮刀給我帶來的幸福感類似,被套的發明為我兒時的鄰居王姨解決了人生大麻煩。
王姨于20世紀80年代末結婚。我還記得,婚禮前一個月,王姨便在新房里忙進忙出,貼喜字,擦洗家具和地面,王姨的同事、親屬也是絡繹不絕,大家喜氣洋洋。王姨的嫁妝中,光被子,娘家就準備了24床。
那時候,被子全靠手工縫。一層被里,一層棉胎,一層被面,四角拉平,中指戴上一枚頂針,再拿一枚大針穿針引線。一針一線,要圍繞被子四周轉一圈,為了不讓被里被面輕易分離,縫被子的人還要從中間再用線固定好幾道。總之,縫被子是個技術活兒,考驗手藝,考驗耐心。
王姨縫被子的水平和我削蘋果皮的水平不相上下,要么被里鋪得不夠勻,要么棉胎擺得不夠正,要么針扎得手流血,要么針腳歪歪扭扭,這兒鼓起,那兒線斷。
王姨能順利入洞房,要感謝所有親朋好友,她的被子是“百家針”縫完的。王姨的表姐縫完最后一針,咬掉線頭時,不無憂慮地對王姨說:“你以后咋辦?被子都不會縫……”
王姨瀟灑地甩了甩新燙的滿頭鬈發:“沒事兒!結婚來幫忙的就有這么多人,一個月換一次被子,大家輪著來幫忙,一年半就過去了……”
眾人錯愕之余,爆出大笑。沒想到,日后,王姨真的付諸行動,我經常見到來她家做客的熟人幫她縫被子。說句實在話,王姨沒有放棄過學習,別人縫被子,她坐小凳子上,跟在旁邊,一招一式地學,但整整兩年,技術沒有任何進步,當時幫忙布置新房的所有親朋好友在幫她縫被子這件事上已經輪完一遍,有的還不止一遍。
我在為王姨發愁時,在為削蘋果皮、縫被子等關于生活的細碎麻煩而感到恐懼時,忽如一夜春風來,被套全民普及了。
王姨一口氣買了四床被套,洗干凈后,在四樓陽臺用四根長竹竿將它們一一晾曬起來。她看被套的神情,如將軍閱兵。
后來的故事,我們都看到并經歷了。
當我套被套時,我總感慨不必被針扎就能裹著蓬松的被子睡個好覺。正如,我操作各種削皮刀,對癥下藥般“對果下刀”時,開心、愉悅。
我靠掃地機器人、洗碗機解放了雙手;靠按摩儀器放松了雙肩;靠語音軟件省去打草稿的時間;靠錯題打印機幫孩子整理筆記;靠可視門鈴,離家萬里監控家門口來過誰,快遞有沒有準時到;靠皮膚科日新月異的新科技抗衰老……我對眼前的一切十分滿意,慶幸我們能享受的生命的長度、寬度都是過去的人的幾倍。他們不可想象,他們終日勞作的大部分事,為之所花的時間,今天都被我們節省下來;生命長了,青春竟也延長了。
感謝科技的進步。
感謝它們帶給我的松弛感,目光所及的大部分問題都能解決,此刻不能解決的,假以時日也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