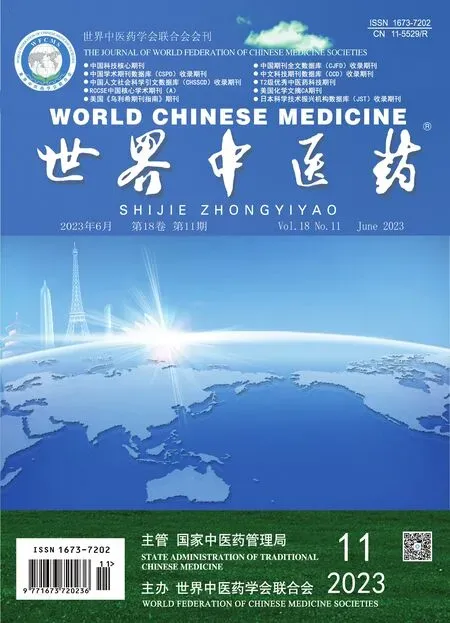基于《中國方劑數據庫》分析瘀毒證方劑藥物組合配伍特點
杜天依 孟閆燕 張 帆 姜眾會 歐陽嘉慧 彭菊琴 阿如娜 趙伶俐 李園白 高鑄燁
(1 北京中醫藥大學研究生院,北京,100029; 2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北京,100091; 3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藥信息研究所,北京,100700)
瘀毒一詞最早見于東晉張湛所撰《養生要集》。宋代《圣濟總錄》謂“毒熱內壅,則變生為瘀血”,論述了瘀毒之間的關系[1]。清代王清任對因毒致瘀的病機進行闡述,認為“蘊毒在內,燒煉其血,血受燒煉,其血必凝”[2]。陳士鐸認為真心痛可由火毒所致,在化瘀方中應用大量清熱解毒藥,體現了“毒”“瘀”病邪與冠心病證治的關系[3]。隨著歷代醫家對瘀毒認識的深入,瘀毒理論不斷得到充實、提高和發展,至明清時期日臻完善。陳可冀院士帶領的研究團隊基于長期臨床實踐,結合冠心病病理生理研究進展,提出了冠心病瘀毒致變理論,認為“瘀久化毒,因毒致變”是冠心病再發心血管事件的重要病機,為急性心血管事件的早期識別和防治提供了新思路[4-5]。目前,瘀毒理論認識已在臨床廣泛應用,而古代方劑文獻中對解毒、活血類藥物的應用規律有待研究。為此,本研究基于《中國方劑數據庫》,篩選治療瘀毒證的方劑,分析其藥物組合配伍特點與規律,為臨床活血解毒法治療相關疾病提供參考和研究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文獻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藥信息研究所建立的《中國方劑數據庫》,此數據庫囊括了國內歷代古籍與文獻中方劑,共計84 464首,是目前最大且權威的方劑數據庫[6]。
1.2 檢索策略 根據方劑的主治、功效,以瘀、毒、活血為主題詞進行檢索。
1.3 納入標準 篩選后納入主治中明確載有瘀血、瘀毒、熱毒等字樣的方劑,或功效中明確載有活血、祛瘀、散瘀、化瘀、破瘀、解毒、散毒、化熱毒等字樣者,或證候表現具有瘀毒證癥狀者均在收錄之列。
1.4 排除標準 排除方劑主治過于龐雜或組方用藥對瘀毒證缺乏針對性的條目。方劑出處不同,或藥物劑量不同,而名稱、組成和功效相同者,只保留其中的一方。
1.5 數據的規范與數據庫的建立
1.5.1 數據庫的建立 在數據整理、記錄和預處理后,建立治療瘀毒證方劑相關數據庫。對治療瘀毒證方劑所涉及的中藥及其功效分類進行頻次統計分析;應用關聯規則分析中的Apriori算法挖掘治療瘀毒證方劑高頻中藥組合之間的配伍關系。根據頻次從高到低排列每味中藥,取頻次排名前20位的藥物作為高頻藥物[9]。對藥物組進行統計分析,選取其中頻次較高的藥物組合,保證了數據的可靠性。
1.5.2 數據庫的規范 依據《中藥學》[7]與《中藥大辭典》[8]內容對中藥名稱予以規范,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中藥合寫或出現方劑名時進行拆分或補充,如將“乳沒”拆分為“乳香”“沒藥”,將四物湯、調胃承氣湯補全藥物;2)中藥別名或俗稱:如將“參山漆”歸為“三七”,“蟬退”歸為“蟬蛻”,“廣皮”歸為“陳皮”,“條芩”歸為“黃芩”。
1.6 數據分析 運用SPSS 14.2統計軟件的Apriori算法對高頻藥物進行關聯規則分析[10],設置最低條件置信度為80%,支持度為1.00。
2 結果
2.1 藥物使用頻次分析 本研究共納入治療瘀毒證的方劑176首,其中內服方劑123首,外用方劑53首。涉及中藥331味,藥物總頻次達1 780次。使用頻率排列前10位的中藥依次為:大黃、乳香、當歸、沒藥、赤芍、白芍、紅花、桃仁、麝香、金銀花;以活血化瘀藥、補虛藥和清熱藥占比最高。見表1。

表1 單味藥物的使用頻次和頻率
2.2 高頻藥物性味、歸經分析 四氣中,高頻藥物中溫性藥物使用頻次最高,微寒性藥物次之;五味屬性中,辛味、苦味藥物使用頻次最高;歸經屬性中排前5位的為肝經、心經、脾經、胃經和大腸經。
2.3 高頻藥物組分析 內服方劑中高頻藥物組有沒藥-乳香、桃仁-大黃等;外用方劑中高頻藥物組有沒藥-乳香、血竭-沒藥等。見表2。
2.4 關聯規則分析結果 分別得到內服、外用方劑中藥組合32組、17組。在內服方劑中,共計32組核心藥物,支持度最高的藥組有柴胡-黃芩-生姜、姜黃-五靈-烏藥、青皮-姜黃-烏藥、青皮-五靈-烏藥,支持度為1.53。外用類方劑分析顯示,核心藥物組合有17組,支持度最高的有蛇床子-血竭-蒼術、蛇床子-沒藥-蒼術、蛇床子-赤芍-蒼術、蛇床子-當歸-蒼術、蛇床子-紅花-蒼術組合,支持度為1.41。見表3~4。活血解毒方劑治療用藥以活血化瘀、療傷止痛、清熱涼血藥物為主。見圖1~2。

圖1 內服方劑藥物組關聯示意圖

表3 內服方劑藥物組關聯度(%)

表4 外用方劑藥物組關聯度(%)

圖2 外用方劑藥物組關聯示意圖
3 討論
3.1 藥有個性專長,方有和群妙用 本研究著重從藥物組成方面總結高頻藥物用藥及配伍規律,為瘀毒證的臨床治療提供參考。本次挖掘分析顯示頻次在前5位的中藥依次是:大黃、乳香、當歸、沒藥、赤芍。臨床應根據病情虛實、瘀毒偏重,合理選擇活血化瘀藥不同炮制品及煎煮方法,辨證配伍補血、涼血、解毒藥物,為活血解毒法臨床應用提供借鑒。
大黃具有活血破積、清熱解毒之效,在治療瘀毒證方劑中靈活多變。大黃煎服法有同煎、后下之分,炮制法有生用、酒洗、酥炒之異。大黃與他藥同煎,意圖緩下攻積,尤其適于胃氣不足、年老體弱者[11]。而大黃后下多見于祛瘀攻下之方,功在瀉實逐瘀,推陳致新。大黃生用通行胃腸結熱,有“欲速行、下行”之意。酒洗能加強其破血逐瘀之力,酥炒可緩其苦寒傷胃之弊。張桂睿[12]基于“陽明瘀毒”理論,以大黃牡丹湯論治頸動脈粥樣硬化易損斑塊獲得良效。藥理研究表明,大黃通過抗氧化應激、抑制內皮細胞增殖、調節腸道菌群失調等多途徑防治心血管疾病[13]。
當歸、赤芍均是治療瘀毒證方劑中的高頻藥物。當歸被稱作“補血圣藥”,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抗動脈粥樣硬化等作用[14]。赤芍具有清熱涼血,散瘀止痛的功效[14]。現代藥理證實其具有抗血栓和穩定微循環的作用[15]。當歸、赤芍兩藥配伍可見于王清任的“五逐瘀湯”。兩藥一溫一寒,相互制約,使祛瘀力專,避免出現過寒用久損傷陽氣,偏溫兼毒瘀毒內生的情況[16]。程江雪等[17]通過動物實驗證實,當歸配伍赤芍可通過調節炎癥介質水平改善熱毒血瘀證大鼠的凝血功能,體現了調和寒溫、去性存用,以達到涼血活血解毒的作用。
此外,金銀花-赤芍組合在治療瘀毒證的內服方劑中使用頻次較高,提示清熱解毒藥物與涼血祛瘀藥物聯用效果更佳。金銀花味甘性寒,具有清熱解毒之功。《本草拾遺》中記載其“主熱毒”。藥理學表明其具有顯著的抗炎、抗病毒的作用[18]。以金銀花為代表藥物的四妙勇安湯通過抑制炎癥反應,穩定動脈粥樣硬化易損斑塊,為清熱活血解毒法臨床應用提供新思路[19]。
3.2 毒有內外之分,藥有內外之用 “瘀毒”屬于中醫學“內毒”的范疇[20]。內毒即內生毒邪,系因臟腑功能和氣血運行失常使機體內的生理產物或病理產物不能及時排出,蓄積體內而化生[21]。“瘀毒”由“瘀”和“毒”組成,二者相互作用,交互影響。正所謂“無邪不有毒,熱從毒化,變從毒起,瘀從毒結也”。一方面,血液壅積留滯,不能及時清除,久則化熱成毒,形成瘀毒互結之勢;另一方面,熱毒之邪深入血分,損傷血脈,爍熾津液,破血妄行,而致血瘀。
若邪毒亢盛于內,瘀阻血脈,則可重用大黃、當歸、白芍等逐瘀通經,解毒止痛。桃仁-大黃作為內服方劑中的高頻藥物組合,也是張機治療瘀血病證的常用藥對[22]。桃仁味苦通泄,善泄血滯,祛瘀力強。唐容川認為大黃既是氣藥又是血藥,有止血不留瘀之妙。《傷寒論》的抵當湯、桃核承氣湯及《金匱要略》中的鱉甲煎丸、大黃蟄蟲丸等,都可見到該藥對的應用[23]。二藥配伍,藥少力專,剛柔相濟,專入血分,共奏破除血積、攻下瘀血之功。劉湘等[24]通過網絡藥理學證實桃仁-大黃介導多通路發揮抗凝、保護血管內皮的作用,達到活血解毒功效。
除了內科疾病,“瘀毒”也可見于在外科疾病范疇。若瘀痛在表難忍,毒熱外滯,則可重用乳香、麝香、白芷、血竭等活血止痛,消腫生肌。乳香-沒藥是外用方劑中高頻藥物組合,具有消腫止痛、化瘀通經的功效,二藥合用又名海浮散。現代藥理研究表明,乳香具有抗炎、抗氧化、調節糖脂代謝的藥理作用[25]。臨床上,乳香-沒藥配伍在各科應用獲得良好臨床療效[26]。此外,活血化瘀藥外用時常配伍味辛走竄、芳香開竅之麝香。麝香能夠調節血腦屏障的通透性,增強其他藥物的吸收,促使其發揮治療作用[27],進一步體現了中醫理論中“通則不痛”的觀點。
本研究分別選取內服、外用方劑中高頻藥物組合進行分析,發現內毒壅盛時治療偏向于清熱瀉火,涼血解毒;瘀毒趨于表時,治用解表祛風,散瘀止痛。熄風類和清熱類藥物應用較多,體現了瘀毒之邪易釀熱生風、發生變證的特點。綜合內外服方劑可知,在治療瘀毒證時主要應用活血化瘀藥物,輔以清熱藥物,同時注重補虛藥的補益作用,以達到祛瘀通絡、解毒涼血、益氣扶正的作用。其結果與《景岳全書》中提出治療血證的“治血、治火、治氣”三大治則一致。
3.3 活血常伴理氣,攻毒時輔化濕 關聯規則又稱關聯挖掘,依賴關系網絡反映藥物配伍的相關關系及緊密程度,根據屬性規律挖掘核心藥物組合[28]。應用關聯規則分別對內服、外用方劑進行數據挖掘,核心藥物組合主要包括:理氣藥+活血化瘀藥、開竅藥+活血化瘀藥+平肝熄風藥、清熱藥+活血化瘀藥+攻毒殺蟲止癢藥、攻毒殺蟲止癢藥+活血化瘀藥+化濕藥。以下選取置信度較高的幾個藥物組合進行闡述。
在內服方劑柴胡-黃芩-生姜組合具有和解少陽樞機、調暢表里氣機之功,是小柴胡湯的組成部分。柴胡辛散,透達表里樞機,黃芩苦寒,清解膽腑郁熱。二者合用,使郁火透發,內熱外透,邪氣得去。唐容川認為,治療血證時首推小柴胡湯調氣以活血化瘀。該方達表和里,升清降濁,體現了“寧氣即是寧血”的治則。張學新等[29]用其治療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后心絞痛,每獲良效。
外用類方劑核心藥物組合蛇床子-血竭-蒼術的支持度高。瘀血阻滯常引起水道不利,以致水濕停留。瘀血與水濕相結為患,久則瘀毒壅積,濕毒流注。蛇床子、蒼術二者味辛以祛風解表,味苦能燥濕健脾,性溫散寒化濕。血竭味甘咸,性平,中醫學認為其具有活血止痛、化瘀消腫、斂瘡止血等功效,可雙向調節活血與止血,并發揮心血管保護作用[30]。隨著臨床藥理研究的深入,蛇床子[31]、蒼術[32]、血竭[30]已被證實在心血管系統具有廣泛作用,其臨床藥理作用有待進一步研究。因此,活血化瘀藥臨床可與常與攻毒殺蟲藥蛇床子或祛濕藥蒼術相兼為用。
基于關聯規則分析結果,從功效方面分析發現,治療瘀毒證方劑,無論內服還是外用,都以活血化瘀、清熱解毒為大法,輔以理氣化濕、開竅熄風、攻毒止癢等治法,以達到更好的臨床療效。活血化瘀類藥物常與理氣活血或益氣扶正類藥物合用。若毒壅氣滯,血脈凝澀,日久本虛標實,當于治療瘀毒之時,加入一至二味行氣藥或扶正藥,如木香、柴胡、青皮或當歸、白芍、甘草等。這體現出氣血之間的相互為用的關系。正如《張氏醫通·諸血門》所述:“蓋氣與血,兩相維附,氣不得血,則散而無統,血不得氣,則凝而不流。”[32]
3.4 思考與展望 瘀毒理論與血瘀、毒邪致病相關[33]。臨床研究表明,活血解毒法在腫瘤、心血管、婦科等多系統疾病中療效確切[34-36]。數據挖掘技術通過客觀、全面地挖掘用藥規律,闡明配伍意義,為臨床提供診療思路,在中醫藥研究的多領域日漸深入[37]。本研究通過數據挖掘發現,活血化瘀藥、清熱藥、補虛藥在瘀毒證的治療中占有較大比例,常用藥物組合有大黃、乳香、沒藥、桃仁、烏藥、青皮、蛇床子、蒼術等。臨床治療瘀毒證以扶正祛邪為基本原則,根據疾病不同而有內治、外治之異,治法總以活血、解毒為主,并根據病性的虛實,分別予以涼血、益氣、溫陽、理氣之法。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中國方劑數據庫》主要基于古代文獻中有明確記載的方劑,而未納入臨床醫案及自擬方,缺乏從辨證規律挖掘臨證醫家診療思想[38]。其次,本研究利用頻次分析、關聯規則分析等數據挖掘方法,對于獲取頻率較高的數據效果更佳,對頻率較低數據的探究尚淺[39]。
本研究利用數據挖掘,以治療瘀毒證方劑為切入點,從局部功效、主治、藥對配伍到整體的多角度研究治療瘀毒證的藥類分析和用藥規律,探討其組配規律,驗證中藥在治療瘀毒證方劑配伍研究中的可行性與實用性,為臨床應用活血解毒法提供了依據。因文獻記載的藥物用量、服法禁忌、特殊煎煮等方面存在歷史時代差異,有待對藥物與方劑之間深層關聯進行深入挖掘分析。
利益沖突聲明: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