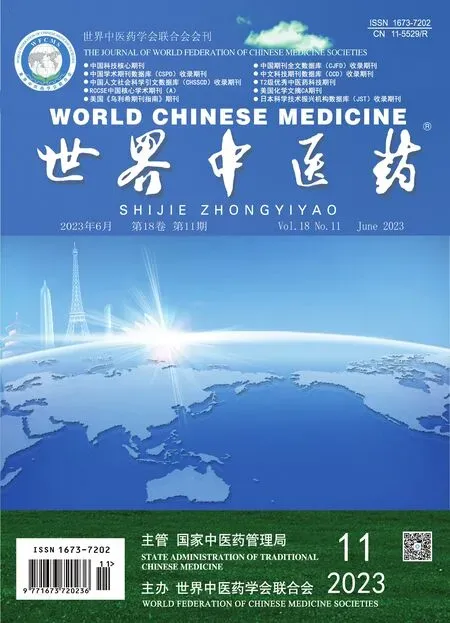基于數據挖掘研究名老中醫治療腹瀉組方的用藥規律
趙浩斌 翟雙慶
(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北京,100029)
腹瀉是指以日排便次數大于3次,或者日排便量超過200 g為主癥的疾病。從發病機制上可以分為滲透性腹瀉和分泌性腹瀉,從病情上可以分為急性腹瀉和慢性腹瀉。每年有5%~7%的人群患急性腹瀉,有3%~5%的人群患超過4周以上的慢性腹瀉[1]。一份有關北京腹瀉人群的調查顯示,北京每年會發生腹瀉18萬~19萬例,這其中大約有35%是感染性腹瀉(急性腸胃炎)[2]。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一份報告顯示,2017年腹瀉占全世界5歲以下兒童死亡的8%,每天有超過1 400例兒童死于腹瀉[3]。老年人群腹瀉的發病與免疫系統功能下降、年齡增長引起的腎功能下降及營養攝入不良有關[1]。在美國,相比于20~29歲的年輕人而言,慢性腹瀉在70歲以上的老年人中更為常見[4]。治療上,PEETERS等[5]提出善寧(Sandostatin?)是目前可以治療包括化療在內所引起的多種腹瀉的有效藥物。但對于老年腹瀉患病人群長期服藥可誘發多種不良反應。中醫藥以其獨特優勢在腹瀉治療中發揮重要作用[7]。
腹瀉根據其臨床癥狀表現屬于中醫“泄瀉”范疇。泄瀉始見于《太平圣惠方·治脾勞諸方》“胃氣不和,時有泄瀉”。《中醫內科學》定義泄瀉為:大便次數增多,糞質溏薄或完谷不化,甚至瀉出如水樣便為臨床特征的疾病[6]。可見,腹瀉符合其定義內涵范圍。其中“泄”與“瀉”都可以表示腹瀉,二者的差別只在于緩峻之勢。《黃帝內經》雖無明確“泄瀉”一詞,但提出了“濡瀉”“洞瀉”“飧泄”“鶩溏”“暴注”等描述不同癥狀的不同類型的泄瀉。名老中醫是當代中醫藥學術發展的杰出代表,代表了中醫藥發展水平現階段最高水準。重視名老中醫腹瀉治療經驗有助于提高中醫師臨床水平有助于推動中醫藥在腹瀉理論繼承和創新。名老中醫對泄瀉的治療有著獨到見解。例如,張大寧提出溫補腎陽、升發陽氣為治療大法[7];楊春波強調慢性泄瀉以脾胃濕熱為主病機,提出祛濕、清化、健脾腎和舒絡的治療法則[8];徐景藩提出溫清并用,補瀉兼施為用藥法則[9]。吳皓萌等[10]研究發現國醫大師在治療上重視脾虛,以恢復脾胃氣機為本,用藥上多以補脾益氣為主。
綜上所述,腹瀉是一種較為常見卻不容忽視的疾病。中醫從《黃帝內經》就開始對其進行分類和闡釋,研究名老中醫腹瀉治療經驗對《黃帝內經》理論的傳承發展具有非凡的意義,既是對《黃帝內經》與中醫藥核心理論的傳承研究,也是對名老中醫腹瀉治療經驗和學術思想的高度總結和升華,是中醫“守正創新”理念指導下的極具理論和臨床意義的中醫藥傳承發展研究。故本文將依托名醫傳承平臺上的有關數據,利用數據挖掘相關軟件,結合《黃帝內經》相關理論對名老中醫治療腹瀉用藥經驗和規律進行討論。
1 資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病例數據來源于2018年12月至2021年11月FangNet平臺收錄的西醫診斷顯示為腹瀉、中醫診斷顯示為泄瀉的病例。
1.2 診斷標準 根據《消化系統常見病功能性腹瀉中醫診療指南(基層醫生版)》,至少75%的糞便為稀便(糊狀便)或水樣便,不伴有腹痛和腸道器質性病變。患者就診前癥狀出現至少6個月,最近3個月符合功能性腹瀉診斷標準。
1.3 納入標準 1)符合功能性腹瀉診斷標準;2)年齡與性別不限;3)均為名老中醫臨床所開處方;4)患者癥狀及處方等資料信息完整。
1.4 排除標準 1)處方主要不是治療腹瀉;2)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炎癥性腸病、慢性菌痢、阿米巴腸病;3)由于手術和服用藥物引起的腹瀉,如藥物或藥物間相互作用引發的慢性腹瀉和膽囊切除術后的腹瀉;4)由原發疾病引起的腹瀉,如慢性胰腺炎和胰腺癌引起的腹瀉、糖尿病腹瀉和甲狀腺功能亢進、肝炎、肝硬化、肝癌等引起的腹瀉。
1.5 數據的規范與數據庫的建立
1.5.1 數據庫的建立 將入選的131首方劑和177味中藥錄入Microsoft Excel軟件中,利用Excel表格進行二分量數據轉換,方劑中出現的某味藥物記為“1”,沒有出現則記為“0”。
1.5.2 數據庫的規范 根據2020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11]和《中藥學》[12]對中藥名稱、分類、四氣五味和歸經等進行統一規范。例如炒白術統一規范為白術,煅龍骨規范為龍骨,棗仁規范為酸棗仁,云茯苓規范為茯苓、焦三仙拆分為山楂、神曲、麥芽等。四氣規范為寒、熱、溫、涼、平;五味歸為辛、酸、甘、淡、咸、苦、澀;藥物分類依據《中藥學》分為解表藥、補虛藥、利水滲濕藥等;歸經如肺胃三焦經則拆分為肺經、胃經和三焦經。
1.6 數據分析 本文采用頻數統計、關聯規則分析、系統聚類分析、因子分析以及復雜網絡分析,分別利用Microsoft Excel 2019、IBM SPSS Modeler 18.0、SPSS Statistics 26.0、Gephi 0.9.2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
頻次統計分析是對某一對象在整體中出現的次數和頻率進行統計和分析,并據此獲得相關信息的方法[13]。該方法目前在中醫藥數據挖掘領域常作為后續研究的基礎,其統計出的高頻藥物及其頻次,后續可以進行關聯規則、聚類分析或因子分析等。
關聯規則分析可以挖掘出一組數據中各項目之間的關系。支持度揭示了前項與后項在整個集合中同時出現的概率。置信度揭示前項出現時后項也會出現的概率。借助SPSS Modeler軟件,采用Apriori算法進行分析。為了獲取藥物的主要關聯規則,找到治療腹瀉藥物的核心配伍,將177味中藥全部納入,支持度最小值設置為20%,置信度最小值設置為90%,前項最大數為3。
聚類分析是對樣本或變量進行分析的一種統計方法,目的是根據事物本身的特性將相似事務歸類,被歸為一類的事物具有較高的相似性,而不同類間的事物有著較大差異[14]。運用SPSS Statistics 26.0對頻次不小于20的高頻藥物進行聚類分析,選擇系統聚類,采用組間聯結的方法,度量標準選擇Pearson相關性。
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從協方差矩陣或相關矩陣出發,根據相關性大小把原始變量分組,使得同組內的變量之間相關性較高,而不同的變量間的相關性則較低。每組變量用一個假想變量表示,將這個假想變量稱為公共因子,其能反映原始變量的主要信息[14]。
復雜網絡用來描述系統中個體之間的關系及系統的集體行為[15]。利用K-核心對核心藥物進行篩選,同時對篩選后的網絡圖以中介中心性和度值進行量化。其中K-核心是指在一個圖中,由多個節點組成的一組節點集,K表示這個節點集中每個節點的度都不小于K值。中介中心性數值的大小反映了經過某節點和邊的數量,說明該節點在整個網絡的重要性的大小,從而判斷是否充當了樞紐。度值等于1個節點和其他鄰接節點的個數[15],具備度中心的藥物與其他藥物直接配伍就越多。根據關聯規則中支持度≥20%,置信度≥90%建立復雜網絡模型并執行拓撲結構中的K-核心算法。
2 結果
2.1 頻次統計 在131首方劑中,共涉及177味藥物和18類藥物,總計2 032次,其中涉及國醫大師3位,全國名中醫3位和師承指導導師5位。藥物分為補虛藥(27味)、清熱藥(20味)、解表藥(17味)、理氣藥(16味)、收澀藥(15味)、活血化瘀藥(15味)、利水滲濕藥(11味)、祛風濕藥(9味)、化痰止咳平喘藥(9味)、消食藥(7味)、溫里藥(7味)、化濕藥(6味)、安神藥(6味)、平肝息風藥(5味)、止血藥(4味)、瀉下藥(1味)、驅蟲藥(1味)、開竅藥(1味)。見圖1。名老中醫在治療腹瀉時,多以補虛藥(570次,28.05%)、清熱藥(181次,8.91%)、解表藥(148次,7.28%)、理氣藥(239次,11.76%)、利水滲濕藥(193次,9.50%)、收澀藥(162次,7.97%)為主。同時將177味藥物全部納入四氣五味與歸經統計中,結果顯示,名老中醫用藥以溫(73次)、辛(78次)、苦(75次)、甘(78次),入肝(82次)、肺(71次)、脾(71次)、胃經(70次)為主要特征。見圖2~4。在177味藥物中,頻數大于20次的有32味藥物。見表1。其中頻數排名前5位的藥物分別是白術(110次,8%)、茯苓(97次,7.05%)、陳皮(89次,6.47%)、甘草(82次,5.96%)、黨參(74次,5.38%)。

表1 高頻藥物統計(頻次≥20次)

圖1 藥物分類統計

圖2 藥物歸經頻次

圖3 藥物五味統計

圖4 藥物四氣統計
2.2 關聯規則分析 共得到關聯規則104項,提取中藥個數為4的條目進行展示。見表2,圖5。

表2 4味中藥關聯規則(%)

圖5 關聯規則網絡展示
2.3 聚類分析 共分為6組聚類。見表3。

表3 高頻藥物聚類分析藥組提取
2.4 因子分析 結果顯示,KMO為0.703>0.7,Bartlett球形度檢驗P=0.000,各項之間存在較強的依賴性,可以進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旋轉方法使用凱撒正態化最大方差法,累計貢獻率72.91%,共提取9個公共因子。見表4。

表4 高頻藥物公因子信息
2.5 復雜網絡分析 結果顯示節點數為80,邊點數為1 767。選取排序前10位的中藥的度值和中介中心性數值列出。白術、甘草、白芍、茯苓、陳皮、黨參、薏苡仁是網絡的核心節點。見圖6。根據度值和中介中心性數值,白術無論在度值還是中介中心性方面均為第一,故白術是治療腹瀉的最為核心的藥物。見表5。

表5 藥物度值和中介中心性

圖6 復雜網絡K-核心展示(K=29)
3 討論
3.1 脾體陰而用陽 名老中醫治療腹瀉多以《黃帝內經》泄瀉相關理論為基礎進行辨證用藥。《黃帝內經》認為泄瀉歸于脾,《素問·臟氣法時論》曰:“脾病者……飧瀉,食不化。”張景岳(張介賓)認為泄瀉本于脾胃:“泄瀉之本,無不由于脾胃。”[16]根據《黃帝內經》,脾是體陰而用陽:脾屬濕土,應長夏,位居中,為陰中至陰,能夠升發布散清陽之氣。《素問·奇病論》曰:“五味入口藏于胃,脾為之行其精氣。”《素問·經脈別論》曰:“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若脾不運化水谷精微則聚而成濕。濕為陰邪,脾在體為陰,且脾主濕,故濕邪多易傷脾而為患。脾以升發布散清陽為用,助清陽之氣布散全身各處,而清陽之氣不升反陷則會出現泄瀉,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清氣在下,則生飧泄”。
3.2 以祛濕為綱要,多法并舉《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點明治療腹瀉當以祛濕為要:“濕盛則濡瀉”,《素問·至真要大論》提出用藥原則是“濕淫于內,治以苦熱……以淡泄之”。名老中醫治療腹瀉用藥經驗是以祛濕為綱要。
3.2.1 健脾祛濕 名老中醫治療腹瀉尤為重視健脾祛濕之法的運用。《素問·藏氣法時論》提出使用味甘、苦之品以健脾祛濕:“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泄瀉之,甘補之”。脾胃充足時,可以耐饑、飽、勞并平穩供養五臟六腑的能力被稱為“緩”[17]。從頻次統計分析可以發現名老中醫用藥以補虛藥為首,多甘溫之品,甘溫(平)補陽(氣),主入脾胃二經。高頻藥物的前5項藥物是白術、甘草、茯苓、陳皮、黨參,其中白術在使用頻率最高。關聯規則中支持度最高的前兩項的藥物是茯苓(補氣健脾、燥濕利水)、黨參(補脾益肺)、白術(補氣健脾、燥濕利水)。復雜網絡圖拓撲分析顯示名老中醫主要使用基礎方劑是四君子湯加陳皮。四君子湯能夠補脾益氣祛濕,伍陳皮(理氣健脾、燥濕化痰)可以健脾行氣祛濕。白術在復雜網絡的核心藥物中處于樞紐地位,這說明白術是名老中醫治療腹瀉的最為核心的藥品。白術味苦甘而性溫,張錫純認為白術最具土德,宜與多種藥物配伍,善于健脾,化痰和止瀉。研究表明白術能夠調節免疫、提高胃腸道功能、調節腸道菌群、促進腸道黏膜潰瘍恢復[18]。甘草,具有補、和、緩特性,與白術配伍可以補中益氣健脾。黨參替人參,味甘性平,伍白術補益脾土。茯苓配白術,一健一滲,水濕則有出路,水濕去則瀉自止。此外,高頻藥物中的黃芪能夠補氣升陽,山藥補益肺、脾、腎3臟之氣,兩藥與白術和甘草同用可以健脾益肺,升陽止瀉。此外核心藥物薏苡仁(利水滲濕、健脾止瀉)伍白術,加強健脾利水祛濕的效果。
3.2.2 清熱燥濕 根據頻次統計,苦寒藥物僅次于辛溫和甘溫之品。苦寒能清熱燥濕。《素問·至真要大論》認為急性腹瀉是由濕熱邪所致:“暴注下迫,皆屬于熱。”關聯規則中存在半夏→吳茱萸+黃連+甘草,F1和C1都有著類似的藥物組合,均以清熱燥濕為主:秦皮(清熱燥濕)、馬齒莧(清熱解毒)、黃連(清熱燥濕)。其中黃連伍吳茱萸是左金丸,其辛開苦降,既能清肝火,又能厚腸止瀉,再伍黃芪是因脾胃偏虛寒者以補脾氣[19]。黃連(清熱燥濕)苦降,半夏(燥濕化痰)辛開,二藥是半夏瀉心湯的組成,其既可以清濕熱,又可以推動脾胃升降樞紐恢復運轉。王燕平等[20]研究發現半夏瀉心湯治療慢性腹瀉相較于常規治療有更好的臨床療效和安全性。C2中葛根伍黃芩出自葛根芩連湯。葛根,“治瀉主藥”,具有升發清陽之功,黃芩清熱燥濕,兩藥同用,共奏清濕熱、升清陽、止瀉之效。惠華英等[21]研究發現,用葛根芩連湯治療濕熱證腹瀉小鼠,治療后P物質等指標含量都有明顯提高。
3.2.3 利水滲濕 利水祛除脾濕以恢復脾升清陽的機制。《黃帝內經》認為脾與膀胱關聯緊密,首先脾經與膀胱經在踹內相連,《靈樞·經脈》曰:“足太陽膀胱之脈……循髀外后廉下合腘中,以下貫踹內。”其次脾俞位于足太陽經上,經氣相通;另外《素問·經脈別論》認為水液在脾升清和肺宣降作用才能下入至膀胱,“飲入于胃……上輸于脾……下輸膀胱”。根據統計發現,利水滲濕藥物使用頻次多達193次。在關聯規則分析中存在白術→薏苡仁+山藥+茯苓;白術→薏苡仁+黨參+茯苓等藥對關聯。F4和C4中都含有山藥、蓮子、白扁豆、薏苡仁、砂仁,上述藥物是參苓白術散的藥物組成,該方能夠利水滲濕止瀉。張景岳[16]認為腹瀉治療以利小便為要:“治瀉不利小水非其治也。”研究表明參苓白術散治療慢性腹瀉患者能夠對腸胃運動產生明顯的抑制作用[22]。
3.2.4 佐消食導滯以除濕 《黃帝內經》認為飲食過飽可以損傷脾。《素問·藏氣法時論》提出脾病不可以飽食,飽食則會阻礙脾病的調養:“病在脾……禁溫食飽食。”《素問·生氣通天論》認為食積會損傷腸胃導致下利:“因而飽食……腸澼為痔。”水谷精微不化聚于體內既影響脾胃氣機又可以化濕生熱。在高頻藥物中,C6和F7皆出現了焦三仙的藥物組合。研究表明焦三仙促進消化液分泌、胃腸平滑肌收縮等[23]。這說明名老中醫在治療腹瀉時秉承《黃帝內經》“通因通用”之法,以消食導滯之法治療食積所生濕邪而達到止瀉之效。
3.2.5 除濕不忘理氣,重視調和肝脾 《素問·六微旨大論》認為氣機的升降運動是人體生命活動的關鍵,“升降息則氣立孤危”,若氣機失常則人體陰陽失衡。《靈樞·刺禁論》點明脾胃是人體氣機升降樞紐,濕邪黏滯易致氣機郁滯,樞紐不利,氣機不暢亦可致水液不化,濕邪內生,此謂“氣郁則生濕”[24]。首先,在頻次統計中,理氣藥(239次)同樣是名老中醫高頻用藥類別,且辛溫藥物居多,因為辛溫通陽能行氣散結,有助于調理脾胃升降,祛除濕邪。由復雜網絡圖的核心藥物和關聯規則可知,陳皮作為理氣藥常伍白術、茯苓等祛濕藥物,是名老中醫治療腹瀉時最常使用的理氣藥物。F9和C7均含枳殼。枳殼能夠下氣寬腸,行胸腹滯氣。其次,肝經是歸經中頻率最高的經絡。《黃帝內經》認為脾土受制于肝木,提出土得木達,以及過怒可以導致肝郁橫逆犯脾,脾虛清陽下陷而腹瀉。《醫方考·泄瀉門》解釋為脾虛肝實,木乘土所致。在C2和關聯規則中,白芍(柔肝止痛)作為核心藥物與白術、陳皮等配伍為痛瀉要方,該方可以調和肝脾,補脾土而瀉肝木,調氣止痛,肝脾和則清陽升而腹瀉止。根據F2可知,脾虛重者加人參伍白術,濕熱者加黃芩伍白術。最后,名老中醫在治療濕熱型腹瀉時尤其重視氣機的通暢。比如C1中柴胡配芍藥加強疏肝行氣解郁。腹瀉患者尤其濕熱腹瀉常會伴有明顯的腹痛。故在C1中加入白芍甘草湯,具有調和肝脾,酸甘化陰,緩急止痛之效。C2中包含的葛根和黃芩是葛根芩連湯的藥物組合,加入木香(行氣、健脾)和香附(疏肝解郁、理氣寬中)可以清濕熱的同時行氣活血止痛。類似的關聯規則中存在蓽茇(下氣止痛)與左金丸相伍。
3.3 以升陽為目的,善用風藥 名老中醫治療腹瀉用藥注重調節陽氣。陽氣以“通”和“升”為要。名老中醫用藥多入肝肺二經,其中解表藥居第3位(148次)。風藥多為解表藥。《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認為風木能克制濕土,風藥具有良好的固腸止瀉之效[25]。李中梓對此解釋為風藥上浮,可以助脾升清陽之氣,“氣屬于陽,性本上升……升、柴、羌、葛之類,鼓舞胃氣上騰,則注下自止”[26]。一方面,柴胡、防風、葛根等解表藥,質輕性升,味辛,有助于清陽之氣的升發。從統計中發現辛溫之品居多,而風藥之品多為辛溫,辛溫之品可以使陽氣通達,清陽之氣無礙于濕邪困阻,清陽升則濁氣降,脾胃氣機恢復正常則腹瀉止。在F7和C5中,防風(祛風解表,勝濕止痛)伍訶子(澀腸止瀉)發揮升陽澀腸止瀉功效。若因寒濕之邪阻滯中焦,加入砂仁以芳香醒脾止瀉。F6中木香(行氣,健脾)、葛根(升陽止瀉)和黃芪(補脾升陽)3藥相伍共奏健脾升陽祛濕止瀉之效。此外,C1中的黃芪伍柴胡可以促進少陽膽氣的升發,少陽之氣升發有助于全身清陽之氣的運行;另一方面,二者配伍可用于治療外感所致腹瀉,《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提出外感可導致腹瀉:“春傷于風,則生飧瀉。”外感表邪,肺失宣降導致大腸傳達失常,從而引發腹瀉。使用解表藥,解表使肺宣降功能恢復,陽氣宣布于體表則大腸傳達功能亦能恢復正常,此可謂“解表以實大便”。
3.4 止瀉固本,巧用收澀藥 腹瀉日久損傷胃氣,收澀藥及時澀腸止瀉留存正氣。其在統計中列第5位的藥物,在以清熱燥濕為主的C1藥物中則有石榴皮,F7和C5有訶子,F3和C3均有肉豆蔻,它們都具澀腸止瀉之效。《素問·標本病傳論》認為治療疾病的標本原則是本虛應先治其本:“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這也從側面證明名老中醫用藥在補虛健脾的同時不忘治標,適時利用收澀藥進行澀腸止瀉達到護顧胃氣之效。但腎為先天之本,“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素問·上古天真論》),腹瀉日久脾虛亦可以累及腎氣。《素問·藏氣法時論》認為凡脾病可以從太陰少陰二經進行治療:“脾病者……太陰陽明少陰血者。”《素問·水熱穴論》強調腎可以調控水谷糟粕的排泄:“腎者胃之關也。”故名老中醫采用脾腎雙補的方法治療腹瀉。藥物頻次統計中發現藥物多入脾腎二經,比如F3中出現補骨脂(補腎壯陽、溫脾止瀉)和肉豆蔻(溫中行氣、澀腸止瀉),二藥配伍為二神丸,一脾一腎,補益和收澀兼施,補腎陽,溫下元,除下焦陰寒溫中土、運脾陽止瀉。C3中則出現四君子湯加陳皮合二神丸,脾腎雙補的同時兼有行氣祛濕的療效。
3.5 思考與展望 名老中醫是以《黃帝內經》脾系為核心的相關理論治療腹瀉。法遵《黃帝內經》,以祛濕、升陽和止瀉固本為治療基本原則,其中健脾祛濕是核心,多用補虛藥、清熱藥、理氣藥、收澀藥、利水滲濕藥,藥物以溫性味辛、甘、苦為主要特征,涉及的基礎方劑主要有四君子湯、參苓白術散、芍藥甘草湯、左金丸、半夏瀉心湯、葛根芩連湯、二神丸等,核心藥物是白術、甘草、白芍、茯苓、陳皮、黨參。白術是名老中醫治療腹瀉時最為關鍵的核心藥物,也是最為符合《素問·藏氣法時論》經旨的藥物。由于脾體陰而用陽,祛濕和升陽是治療腹瀉一個過程的2個方面,祛濕實際目的是恢復“脾”升陽之用,同樣升陽才能免于濕邪為患,故臨床上應當將二者緊密結合運用,不宜將二者分而別之。
不過名老中醫尚未重視小腸在腹瀉治療中的價值。寒邪內舍于小腸會導致腹瀉,《素問·舉痛論》曰:“寒氣客于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后泄而腹痛矣。”小腸具有受盛化物和泌別清濁的作用,而如今小腸的功能多被整合到“脾”系中,最終形成以消化為主的復雜體系。臨床上小腸吸收異常所導致的如腹脹、腹瀉等癥狀也會被歸納為“脾”功能的異常[27]。此外小腸的部分功能可能也被歸于腎系。小腸連接脊柱和神闕處“后附脊……外附于臍上”(《靈樞·腸胃》),《素問·脈要精微論》則提出:“腰者腎之府。”同居下焦,位置鄰近。《靈樞·口問》提出小腸脹大可以牽引腰部作痛。治療時也多采用關元、神闕與小腸俞補腎益氣,故由于腎陽不足而致脾虛的慢性腹瀉亦有可能是小腸虛寒所致。當然,以上2個方面可能是由于《黃帝內經》臟腑分類方法的不同導致小腸的功能被分解歸到脾、腎2個藏象之中,但這并不利于未來中醫治療腹瀉方法的探索,因為腹瀉成因復雜,類型多樣,不能只從五臟論治。
利益沖突聲明: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