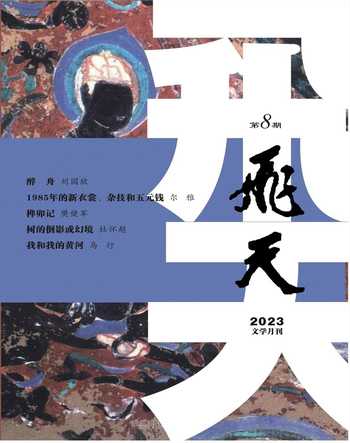復活
張世勤
1
我有個堂兄,叫顧鄉(xiāng)俊,高個,大眼睛,額頭很寬,臉膛很有棱角,早年在村里干體力活,最大的愛好就是下棋,勞作間隙或收工后的閑余時間,幾乎全部都用到下棋上去了,因此他的棋藝也修煉得沒的說,方圓幾里,他要說第二,沒人敢說第一。
后來,村里的年輕人陸陸續(xù)續(xù)外出,打開了一個通向外面的世界。一個很簡單的事實就是,到外面去掙錢要比從土里刨錢容易得多。接下來的那幾年,甚至一直到現(xiàn)在都是,種地已經(jīng)不掙錢了。除去地錢、種子錢、肥料錢,確實剩不下幾個渣,這人工錢還沒算進去呢!
于是,我堂兄顧鄉(xiāng)俊也跟在年輕人后面外出了。
村里最早走出去的幾批人大都是從收廢品開始,那時初到城里的他們,還茫然無措。我堂兄顧鄉(xiāng)俊也不例外,但他腦子好使,又年齡大點,大家都信任他,看中他跟外界的溝通能力,便推他當了頭。別人零收,由他匯總后統(tǒng)一向外賣。零收者不僅省了時間,整賣后效益明顯要高于單賣。于是大家慢慢地由原來的單打獨斗,逐漸發(fā)展成了以我堂兄顧鄉(xiāng)俊為頭兒的破爛幫。平日里大家搭伙一起吃完飯后,便四散下去,我堂兄顧鄉(xiāng)俊的任務則是去發(fā)現(xiàn)和聯(lián)絡產(chǎn)廢品多的單位,并將其拓展成獨家業(yè)務,固定下來,成為長戶。等長戶一多,有長戶打底,再加上大家零收,業(yè)務量肯定就有了保證。
有次,正當他在街上轉轉悠悠,東找西看時,破爛幫里的弟兄二貴打電話來,說現(xiàn)在他們在哪兒,讓他趕緊過去一趟。為什么要讓他過去呢,是因為有人在那地兒擺殘棋,所有挑戰(zhàn)者無一例外,都輸了。
這事,他得去。
擺殘棋的,是一個黑瘦的老頭兒。
他坐下,破爛幫的弟兄在他身后圍了一圈。
弟兄們嘴上不說,但心里都明白,這回肯定有好戲看了。
結果三場下來,每場眼看都要贏,到最后卻都輸了。
這很不應該啊,弟兄們無不悵然。
回到住處后,有脾氣直的弟兄還在埋怨,這事鬧的,還不如不讓你去呢!
也有的說,以后可別再在我們面前吹自己怎么會下棋了,看到了吧,連個在街上擺殘棋的老頭你都擺不平。
說話間,有人來了。一看,來者不是別人,竟是擺殘棋的老頭,手里還提著酒提著菜,說喝杯酒,認識一下。
顧鄉(xiāng)俊招呼弟兄們,大家坐吧。那架勢就像他知道老頭一定會來一樣。
破爛幫的弟兄們見頭兒不見外,也就一一落座。
老頭兒說,大家可以喊我老殘。
顧鄉(xiāng)俊說,這怎么行!
老頭兒說,沒事,我有點兒跛腳,不注意可能看不出來。其實,外人也大多這么喊。當然他們這么喊,也并不是因為我跛腳,而是因為我常年擺殘棋。
破爛幫的弟兄們還真沒在意老頭腿腳不利索,因為他們見到的老頭,都是在街上一直坐著的。
酒后,顧鄉(xiāng)俊一邊往外送一邊說,讓老人家見笑了,您應該也看出來了,我們就是一群收廢品的鄉(xiāng)下人,自稱破爛幫,租住的也是這么一個破落的大院。
老頭兒說,這沒什么,我就是想過來見見你,等有時間你再去街上,我給你說句話。
顧鄉(xiāng)俊說,這個好說,因為我的時間不用等,多的是。
臨別,老頭兒說,你如果覺得喊我老殘不禮貌,以后可以喊我老南頭。
顧鄉(xiāng)俊知道了老頭兒姓南。
2
二人第二次見面時,老南頭收了殘棋,跟他找了個僻靜處坐下來。
老南頭說,那天你明顯是讓我了。
顧鄉(xiāng)俊說,讓您看出來了。不過,我的棋藝也沒有我那幫破爛兄弟吹得那么高。
但你是能贏我的。
有這個可能。
但你選擇了放棄。
顧鄉(xiāng)俊沉吟了下說,我就是一收破爛的,手下還帶著一幫吃喝都困難的弟兄,在這清城人生地不熟的,我們沒有資格去逞這個能。
老南頭說,其實我早知道你。
呃?
你有個徒弟,二貴,年輕氣盛,又很好棋,但在我這兒輸了不少。我看出他沒多少錢,每次都是皺皺巴巴地掏出一些零票。我擺殘棋并非只為錢,主要圖有個事兒牽著,也算一樂,好打發(fā)時間。知道他的身份后,我把之前所贏想全部退還給他,他不要,而是提出了一個要求,讓我教他下棋。我以為棋藝高低對眼下的他來說一點也不重要,他更需要的應該是如何好好地去掙錢。當時,他就說到了你,說你的棋是如何如何厲害,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你下輸。下輸你有什么好?他說他想當頭兒。我說,你贏不了他。他說,你連見都沒見過他,你怎么知道我贏不了他?我說,因為你的心太小。他顯然沒明白我話的意思,他說,你錯了,也許我用不了多久就能贏他。我問為什么?他說,你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敢多動腦子了。為什么不敢多動腦子了呢,是因為你大腦里長過瘤子,做過一次手術,手術雖然成功,但瘤子還會繼續(xù)長。等再長起來,再需要動手術時,那可能就麻煩了。一般說,二次手術的成功率很低很低。
顧鄉(xiāng)俊說,二貴說的沒錯。
所以,那天我專門給他錢,讓他把你約過來。
你既然已經(jīng)知道我的身份,我就是一破爛王,那么您仍然屈尊見我能有什么意義呢?
因為我有點兒好奇。
好奇?
當然不是因為你的病。
那是……
有天,有個人在我這兒坐了一會兒,二貴正好也過來,看著那人驚了半天。那人走后,二貴說,簡直奇了,怎么跟我們頭兒長得一模一樣。
顧鄉(xiāng)俊說,中國人這么多,有兩個一模一樣的人也正常。
老南頭說,可是,那天那個在我攤上坐了一會兒的人,不是別人,而是我的親侄,南安度。實話說,那天當你在我對面坐下的那一刻,我的神思真的都有些恍惚了。哪是你坐在我對面,分明是我侄南安度坐在那兒。
3
再后來,清城的破爛幫解散了。
解散的理由當然很充分,揀破爛早期還行,如今清城經(jīng)過一輪又一輪的園林城、衛(wèi)生城、文明城的創(chuàng)建,城市面貌已經(jīng)大為改觀,已經(jīng)沒有太大揀破爛的空間了。何況,老揀破爛也讓村里后來出來的那些人有點瞧不起,因為后來出來的那些人,有靠賣力氣的沒錯,但大多已經(jīng)有技術,甚至有的已經(jīng)做起了不錯的生意,總之都已經(jīng)多了些體面,錢掙得也更多了些尊嚴。再退一步說,清城也算不得大城市,大家還是去往大城市的好,畢竟大城市機會多,空間大,也好見些世面。顧鄉(xiāng)俊給大家發(fā)了錢,另外每人還額外發(fā)了一筆。
幫是破爛幫,但大家的感情卻并不破爛,有好幾個人哭了。
有的說,這幾年大家相依為命,終究還是散了。
有的說,誰知道到大城市又會是什么樣子。
有的問顧鄉(xiāng)俊,我們走了,你怎么辦?
顧鄉(xiāng)俊說,上天有命,我就多活幾年,我手頭有點錢,可以在清城養(yǎng)老,也不排除另外找個養(yǎng)老的地方。
有人不解,說你能有多少錢?而且還給我們每人額外發(fā)了一筆,你哪來的錢?
顧鄉(xiāng)俊說,我是頭兒,這你們就不用管了。
4
我接到我堂兄顧鄉(xiāng)俊的電話,是一個下午,說第二天要到山上來。
堂兄是和二貴一起過來的。我以為堂兄過來,是要爬泰山,因為我在泰山管委會工作,想爬泰山自然很方便。但當我陪他們坐中巴到了中天門后,我堂兄就不再往上走了。說找個僻靜地方咱說個話吧。
堂兄讓二貴一個人繼續(xù)往上爬。
到一僻靜處,堂兄的第一句話是,泰山靈芝是不是能治腦瘤?
我說,泰山靈芝當然是好東西,它和泰山參、泰山何首烏、泰山穿山龍并稱為泰山四寶。要按傳說,那泰山靈芝神了,能治耳聾,能利關節(jié),能益精氣,能堅筋骨,能療虛勞。
你就說能不能治腦瘤吧?
要說也能治,因為它能安神解痙,沖解血粘,可以治療腫瘤、心血管疾病等,還有肝炎、哮喘、神經(jīng)衰弱、頻繁性感冒、皮膚褐色素沉積等,總之,貌似百病都能治。
堂兄說,那等我的病治好了,你就說是泰山靈芝發(fā)揮了作用。
我說,如果治好了,還需要我去說嗎,你自己不就可以?
堂兄一下沒了言語,可能也意識到邏輯上有些講不通。
我說,你怎么突然又說起了病?
堂兄說,我的病你是知道的,很多人第一次手術就完了,雖說我第一次手術算是很成功,關鍵是醫(yī)生說得也很明確,那就是這種病很討厭,良性的做過了也就沒了,惡性的做過后仍然會重新長,只要繼續(xù)長,那就隨時可能復發(fā),只是時間長時間短的問題。而且,只要是第二次復發(fā),就很難再指望手術的效果。也就是說,會有生命危險。
我說,你這病得實治,不能指望泰山靈芝,泰山靈芝要那么管用,那還要醫(yī)院干什么!
堂兄說,我當然不是來向你討要泰山靈芝的。
那是?
堂兄說,我這兒有個卡,里面有一筆錢,這筆錢不算是小數(shù),我如果治不好或不見了,那么由你把這筆錢交給顧顏。
顧顏是堂兄的獨生女。
我說,你現(xiàn)在感覺你的身體有情況嗎?
堂兄說,是,我感覺有情況,而且情況很不好。
我說,你既然還能自己來找我,那為什么不把錢直接交給顧顏呢?
堂兄說,我的情況你知道,她怎么肯要呢?
堂兄的第一次手術是成功了,但代價當然也不小,那就是花了不少錢。堂兄自己哪有那么多錢,顧顏參加工作并不太久,手頭同樣沒有多少錢。也就是說,一次手術就把堂兄花窮了,花怕了。自己的病暫時算是好轉了,但卻給顧顏留下了一份沉重的債務,這是堂兄最不愿意見到的,也是從此再也睡不好覺的原因。因此出院后不久,堂兄就隨年輕人出村了,而且其后不久,就向村里傳話說,在清城已經(jīng)有了個相好的,然后又不久便是很決絕地與堂嫂離了婚。
對他們的情況,村里人當然大都知道,堂兄與堂嫂從年輕時感情就一般。堂兄高個,大眼睛,額頭很寬,臉膛有棱有角,年輕時應該說還是很帥氣的,男人氣十足。堂嫂跟他一比,那就差遠了,個矮,五官一般,身材沒個型,皮膚很粗糙,而且脾氣不小,性格很倔強,老想著管控堂兄。因此,二人之間發(fā)生矛盾幾乎是家常便飯。堂兄在家里待不住,這也成了他迷上下棋的原因。在堂兄的影響下,我們村,甚至在周邊一帶,奕棋成風,聽說鎮(zhèn)里還因此搞過全鎮(zhèn)象棋大賽,也一度申報過象棋之鄉(xiāng)。但自從堂兄大腦長出了瘤子,下棋之風戛然而止。因為大家都怕了,什么走一步看三步,這動腦子的事可不是鬧著玩的,知道嗎,一不小心大腦里那可是要長出瘤子來的。顯然大腦長瘤子與下棋并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可大家那是寧可信其有,不去信其無的。
對于堂兄的離婚,村里人都沒太大感覺,有的可能認為他們早就該離了,有的可能認為都熬到現(xiàn)在了已經(jīng)沒有離婚的必要,有的倒是感覺挺好奇,堂兄竟然還能在清城有了相好的,有的甚至由此生發(fā)出了些羨慕,什么情況,長得什么樣呀,是不是年齡比堂兄還小不少啊。但對堂兄的離婚,顧顏是接受不了的,怎么著也不能離婚哈,因此撂下過狠話,你如果跟我媽離婚,我不會再認你這個爹。而這恰恰正是堂兄想要的結果,如此一來,他的病是不是還會復發(fā),還需不需要治療,治療費是多是少,這一切也就都跟顧顏無關了。
堂兄說,我直接給她,她不要是一回事,她如果問我這么多錢是哪來的,我該怎么回答她?
我說,是啊,你一個揀破爛的,哪來這么多錢?
5
其后不久,清城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那就是一個叫南安度的國有企業(yè)老板跳樓了。據(jù)傳,跳樓的原因是,南安度不知是被紀委還是被檢察院早就盯上了,一場風暴,山雨欲來,已經(jīng)風聲滿城,雖說可能不會是死罪,但少則十年多則二十年的牢獄之苦,恐怕他是逃不過的,這還得外加家庭破碎,身敗名裂。所以南安度選擇在這個時候跳樓,也算棋行一步,事出有因,合乎邏輯,一了百了。
南安度的跳樓,不過就是一則社會新聞,他愛跳不跳,甚至罪有應得,與其他人無關。但問題是,隨著南安度的跳樓,我堂兄卻突然失蹤了。我?guī)状未蛭姨眯值碾娫挘雴枂査牟∏椋驗樯洗螐纳缴匣貋頃r,就說已經(jīng)有些不好的感覺,馬上恐怕就要轉入治療了,那么到底真犯病了沒有,治療了沒有,在哪兒治療的,效果怎么樣,前景樂觀不樂觀。這一系列問題我都想知道。
堂兄的電話打不通,打二貴的,二貴的竟然也打不通。
過了幾天,一個陌生的電話打進來,一接,竟是二貴的,說剛換過手機號碼,問我在山上不。我說,在。
于是,二貴就來了。
我說,最近我一直在聯(lián)系你呢。
二貴說,我換電話號碼了。
我說,鄉(xiāng)俊也換了嗎?
二貴說,應該換了吧。
我說,換就是換,沒換就是沒換,怎么能說“應該”換了呢?難道說,你沒聯(lián)系他?他的情況你也不知道?
二貴說,沒聯(lián)系。
我說,最近村里人都在風傳,說顧鄉(xiāng)俊的病治好了,而且是吃泰山靈芝治好的。這段時間,我的電話都快被村里人打爆了,內(nèi)容幾乎完全一致,那就是想讓我也能給他們搞點泰山赤靈芝。我反復給他們解釋,泰山赤靈芝沒那么神,可他們不聽,說腦瘤都能治,還有什么不能治的,有個頭痛腦熱的,那還不是一瓣即好!而且還聽人說,曾在某車站偶然遇到過我堂兄,不僅病好了,氣色沒的說,而且看上去整個人連氣質都變了。只是有一點,不太認人,你喜出望外地跟他說話,他先是一愣,說半天話后卻問,你叫什么來著,我怎么一下記不起了?這是不是腦瘤后遺癥啊。
最后我說,我現(xiàn)在聯(lián)系不上他了。
二貴不說話。
我說,你今天為什么突然要找我呢?
二貴說,是關于那筆錢的事。顧鄉(xiāng)俊反復交待過我的事就這一件,要我監(jiān)督你做好落實。
我說,我很想聽聽,你們破爛幫的事,你們在清城的事,你和我堂兄顧鄉(xiāng)俊的事。
二貴吞吞吐吐地說了一些,前面的部分說的算比較細,后面的部分便只剩下了片言只語。
我覺得二貴一定是一個知道內(nèi)情的人。我簡單整了兩個小菜,要跟二貴喝兩杯。
二貴說,今天不喝,不喝。
我說,你不是很好酒嗎?
二貴說,今天不能喝,過會兒我就得走。
我特地拿出了一瓶茅臺,說,今天可是喝這酒。
二貴顯然動了心,說,這么好的酒啊!
一會兒工夫,二貴就有點沾酒了。我說,你剛才為什么特別強調今天不喝不喝呢?
二貴說,可能有人會盯著我。
我說,怎么會有人盯你呢?
二貴沒正面回答我,而是說,那天我和顧鄉(xiāng)俊到你這兒來時,其實不止我們兩個,另外還有一個人。
還有一個人?
是的,那人腿腳有點不好,你肯定沒注意。
我沉吟下說,沒注意。
二貴說,顧鄉(xiāng)俊現(xiàn)在已經(jīng)找不到了,我也不會在咱這一片待時間太久,我可能也要帶上家人到外地去。
我說,你打算去哪兒?
二貴說,我還沒想好。
去干什么?
也還沒想好。
那為什么非得一定要去外地呢?
因為我手里現(xiàn)在也有了一筆錢。
我說,我怎么突然覺得你們破爛幫仿佛一下都有錢了一樣?
二貴沒回答我。
這天,二貴醉酒,就住在了我這兒。半夜里,他突然爬起來問,我這是在哪兒?
我說,泰山啊。
他問,晚上能不能爬泰山?
我說,有不少游客是專門晚上爬的,有的是為了看日出,有的則純粹是為了體驗不一樣的景色。
二貴說,那我去爬山,我還沒上去過十八盤呢。
二貴是正當年,身強力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登十八盤肯定沒問題。
但那夜,出事了,年輕力壯的二貴從十八盤上一頭倒栽了下來,頭差點撞扁,人沒了。
這事出得蹊蹺,到底是他不小心自己摔下來的,還是被人推下來的,不得而知。
6
顧顏是好不容易考上學的,又是好不容易入了職的,這也是讓我堂兄唯一感到欣慰、驕傲和自豪的。也就是在顧顏入職不久,我堂兄大腦出現(xiàn)問題,做了第一次手術的。顧顏現(xiàn)在我們鄰縣檢察院工作,一身檢察制服讓她多出了些干練和英姿。顧顏已經(jīng)不是當年那個黃毛小丫頭了。
顧顏說,叔,你不來,我也要去找你的。
為你爹的事?
是。
我說,你不是跟你爹劃清界限了嗎?
顧顏說,那是說劃清就劃得清的嗎?我爸說我媽犟,他那才真叫犟。
我說,你爸犟嗎?他有他的苦衷。他的想法很簡單,當然也有點粗暴,不近人情,但你應該不會不知道他為什么要這么做。
顧顏說,現(xiàn)在說這些還有什么用!
我說,你相信你爸的病好了嗎?
不信。
你相信是泰山靈芝給治好的嗎?
不信。
如果說是真治好了,那他應該很高興然后一家人團圓才是,可他為什么選擇了失蹤。
顧顏看著我說,說明叔有自己的推斷。
我說,從二貴口中傳遞出來的不連貫信息看,我完全可以大膽揣測,事情大體或許是這樣的:南安度以開會名義讓司機送他去賓館,早在賓館房間里等著他來的就是你爸,當然可能還會有那個跛腳的人和二貴。二人互換服裝和身份證之類的證件之后,你爸出賓館,上車,去公司,上十樓,然后打開寬大的玻璃窗,從十樓跳了下來。反正,他認為他的病已經(jīng)沒得救,在繼續(xù)花下很多錢卻還是救不過來的情況下,不如做筆交易,給你留下一筆錢。
說著,我把我堂兄顧鄉(xiāng)俊給我的那張卡拿了出來,說,這是你爸讓我轉給你的。我沒查,但聽你爸說,里面的錢不是個小數(shù)。
顧顏拿著卡,捻來捻去,眼淚慢慢地花了一臉。
7
那天,離開顧顏時,顧顏只給我留下了一句話:相關政法機關已經(jīng)介入!
責任編輯 趙劍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