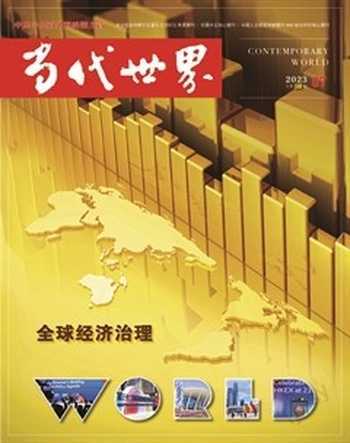大變局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重構與中國角色
【關鍵詞】全球經濟治理??大國競爭??體系重構??中國角色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特別是在新冠疫情及烏克蘭危機沖擊下,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發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現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合法性、有效性以及共同價值觀缺失等多重危機,“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大勢所趨”。[1]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主要是指國際社會在互動中建立起來的開展經濟合作、維護全球經濟秩序的組織框架和制度規則安排。制度先行是二戰結束以來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點,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制度框架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奠定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基調。然而,在外部因素沖擊下,制度體系固有的慣性使原有的制度安排無法合理反映行為體的觀念、權力和利益結構的新變化。這種矛盾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不斷演變,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興衰期。二戰后美國主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度是“最穩定的貨幣體系,也是真實經濟各項指標最好的時期”。[2]然而,隨著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相繼爆發,加之石油危機的沖擊,布雷頓森林體系最終以美國單方面宣布關閉“黃金窗口”宣告瓦解。
二是新自由主義制度的興衰期。新自由主義以及在該理念指導下形成的“華盛頓共識”是20世紀80年代以美英為首的西方國家制定內政外交政策的重要指南,也是主導冷戰后超級全球化的重要理論模式。冷戰結束后,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從冷戰時期的兩極分化走向統一,二十國集團(G20)被確定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論壇,具有真正全球性意義的治理體系得以形成。
三是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突變期。二戰結束以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經歷了多次嬗變,但大體上還是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基礎的多邊治理體系的改革。然而,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全球貿易持續低迷,能源危機、經濟失衡、公共衛生危機乃至地緣政治沖突等全球性問題頻發,逆全球化興起,經濟全球化進程嚴重受阻。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代表的曾經發揮重要作用的多邊治理機制逐漸衰弱,區域性合作機制與非正式合作機制加速發展。特別是2018年以來,中美關系出現重大轉變,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等推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全球經濟治理格局出現深刻調整,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重構。
當前,導致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快速演變的動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外部沖擊。外部沖擊往往是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突變的導火索,戰爭、經濟危機、科技革命、自然災害和公共衛生事件等突發性重大事件,往往容易引發國際制度的急劇變化,這種影響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負面的。例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七國集團作為全球金融體系最主要的治理機制已力不從心,G20升格為峰會機制,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平臺,標志著全球經濟南北合作共治模式的開始。但是,由新冠疫情引發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并未帶來應有的全球合作效應,反而助推了國家中心主義的高漲。美國以所謂“安全”為借口推行“小院高墻”“俱樂部式的偽多邊主義”,致使疫情前就已經深陷泥潭的WTO等多邊機制再遭挫折。烏克蘭危機持續發酵帶來的全球性安全挑戰進一步加速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重構。

2023年6月27日至29日,第十四屆夏季達沃斯論壇在天津舉行。圖為6月27日舉行的“通力合作,促進能源轉型”對話會現場。
二是結構性變化。大國行為體的觀念、權力和利益結構變化是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演變的內生動力。首先,制度是觀念的固化。近年來,冷戰思維回潮,美國對華認知和定位出現嚴重偏差,把中國當作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和最嚴峻的地緣政治挑戰,價值觀外交成為美國對華強化競爭與遏制的重要抓手。[3]美國積極推進所謂“以規則為基礎、以民主人權為價值原則”的國際經濟秩序,抓緊建立以意識形態劃線的排他性國際機制,制定具有針對性的國企競爭中立、監管一致性、勞工標準等邊境后規則,濫用貿易救濟、出口管制及經濟制裁等手段,以所謂“長臂管轄”為名將國內法律“武器化”,扭曲全球供應鏈,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進行制度擠壓。其次,制度是權力的結果。當存在壓倒性權力時,權力壟斷者會主導制度的設計、執行;當不存在壓倒性權力時,國家間權力博弈的均衡結果將決定制度變遷的方向。[4]當今世界多極化不斷發展導致現有的國際制度加速變遷。最后,收益考量是國家行為體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動力。國際制度分配效應對同一時期的不同國家行為體的影響是非中性的,對不同時期的同一國家行為體的影響也有所不同。既得利益者會強化制度并使制度合法化,利益受損者則會質疑甚至挑戰現有制度體系。美國等西方國家將國內債務擴張、貧富差距問題歸咎于全球化本身和自由貿易體系,轉向追求所謂的“公平貿易”為先導的貿易政策,實施強力干預市場的產業政策,推行“有原則的現實主義”和形形色色的“偽多邊主義”,使得全球經濟治理規則和制度的利益分配機制遭到嚴重扭曲。
三是非國家行為體的影響。非國家行為體是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演變的重要補充力量。二戰特別是冷戰結束后,跨國公司對一國經濟決策和外交談判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由于公眾對網絡平臺的依賴和政府在網絡空間治理效能的缺失,超級數字平臺企業的影響力從網絡治理范疇延伸至社會治理、國家治理。以歐盟數字競爭政策制定為例,根據歐洲企業觀察組織(Corporate?Europe?Observatory)和德國研究機構LobbyControl等調查機構發布的研究報告,在對歐盟機構進行游說的資金投入方面,科技企業目前已超過制藥、化石燃料、金融和化工行業而占據主導地位。根據這份報告,截至2021年6月中旬,612家公司、團體和協會每年花費超過9700萬歐元(1.144億美元),對歐盟的數字經濟政策進行游說。[5]科技和數字公司的游說工作主要集中在歐盟當時擬議的《數字市場法案》(DMA)和《數字服務法案》(DSA)。報告指出,在歐盟委員會就這兩項立法草案舉行的271次會議中,75%都有科技公司或其相關貿易團體的游說者參與。大型科技公司和整個數字行業的游說投入不斷上升,表明數字技術行業尤其是平臺企業在國際社會中擁有巨大并日益增強的影響力,數字平臺早已不是單純的反壟斷對象,而更可能成為塑造平臺經濟新規則和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的重要參與者。
美國主導的以新自由主義為導向的經濟全球化不斷走弱,取而代之的是以多元化、區域化和數字化為主要特征的再全球化。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演進則由過去的緩速、低烈度的漸變期過渡到快速、高烈度的突變期,其重構特征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治理形式的碎片化、分裂化和俱樂部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以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代表的多邊治理機制改革進程嚴重受挫,一度發揮過良好國際協調作用的G20也漸顯疲態。一方面,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過往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傳統多邊機制無法反映新興國家的發展訴求,其合法性、公平性及有效性飽受質疑,新興市場國家開始努力尋找破局點,如“一帶一路”合作機制、東盟峰會、金磚峰會等日益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多邊機制失靈困境和大國博弈加劇使一些發達國家走向構建以其為主導的區域主義、集團主義,如《美墨加協定》(USMCA)、《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以及“印太經濟框架”(IPEF)。美國等發達國家意圖重塑霸權地位而創建的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機制和新興市場國家為彌補全球經濟治理赤字而作出的各種嘗試,客觀上使當前全球經濟治理制度加速碎片化、分裂化。特別是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后,傳統的自貿協定退潮,二戰結束后以自由化為主要特點的多邊貿易治理體系,正在轉向以關鍵供應鏈為訴求的區域治理體系。[6]從特朗普政府時期開始,對華強硬漸成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和自由、保守兩派的共識。美國糾集所謂“志同道合”的國家組成“民主國家聯盟”以遏制打壓中國,試圖將中國從半導體等多個關鍵供應鏈環節剝離,加劇全球走向“脫鉤斷鏈”和“兩個平行世界”的風險。烏克蘭危機引發了嚴重的全球性能源危機,美歐與俄羅斯之間的制裁和反制裁不斷升級,助推了全球能源供應鏈的重組。
第二,治理觀念的意識形態化、安全化和工具化。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觀念,經歷了二戰結束后內嵌的自由主義到冷戰后的新自由主義;如今新自由主義走不通了,意識形態化、安全擴大化下的新干預主義又開始興起。2023年4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地位》的演講,高調推出以遏制中國發展為主要內容的“新華盛頓共識”。“新華盛頓共識”的提出,意味著過去美國主導的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基礎,倡導貿易和金融自由化、減少國家干預的舊“華盛頓共識”的破產,也表明美國在對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反思的基礎上,意圖通過加大政府干預以擺脫所謂對中國的依賴,重塑產業政策、經濟安全利益及國際經濟秩序。早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就將貿易政策“武器化”。2020年生效的《美墨加協定》包含了針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毒丸條款”,規定三國可以隨意認定并排斥“非市場經濟國家”。此外,美國主導簽署的《美韓自由貿易協定》和《美日貿易協定》均采納了“毒丸條款”,意在將中國排斥在所謂的高標準協定之外。近年來,隨著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加劇,拜登政府又將國際科技交流合作意識形態化和陣營化,全力遏制打壓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創新發展能力。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修訂《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并多次對包括“特別指定國民清單(SDN)”在內的經濟制裁進行擴充,以初級制裁及次級制裁為要挾,禁止美資企業與被列入清單的中資企業交易。拜登政府于2022年頒布的《通脹削減法案》,旨在通過向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國家的公司提供貸款或補貼,來削弱中國在綠色能源等領域的主導地位。[7]《芯片與科學法案》則通過產業補貼、出口管制清單、實體制裁、“研究安全”條款以及“中國護欄”條款等手段,加快關鍵產業鏈的本土化及友岸化進程,對中國芯片行業進行全面封鎖,將中國排除在全球供應鏈之外。

2023年3月2日,印度新德里,二十國集團外長會舉行全體會議。

第三,新型領域治理規則的分立化。當前世界正處于從工業經濟邁向數字經濟的歷史機遇期,數字產業、新能源等領域成為大國博弈的前沿陣地,各國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選擇了不同的治理規則、范式,均致力于將本國的治理方式推廣成為全球規則和標準。在跨境數據流動規則層面,美國利用其在數字經濟和信息技術領域的全球領先優勢,極力推崇跨境數據自由流動政策。2018年簽署的《美墨加協定》的第19章是迄今為止自由貿易協定(FTA)中關于跨境數據流動最為詳盡的條款,其規定“任何締約方不得將金融機構或跨境金融服務提供者所采集的金融數據本地化存儲,作為在境內開展業務的前提條件”。歐盟則強調在單一數字市場內維持高標準隱私保護的前提下促進數據跨境流動。以俄羅斯、印度、巴西為代表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則采取了嚴格限制數據流動的本地化政策,如俄羅斯2015年修訂了《個人數據法》,印度2018年出臺了《個人數據保護法案(草案)》。在算法治理規則層面,由于境內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平臺企業,歐盟更強調權利保護、境內競爭秩序和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如歐盟《數字市場法》對大型數字平臺“守門人企業”進行了額外義務設定,要求其搜索排名不得有意偏向自營產品,必須對自營產品和第三方產品一視同仁。[8]因考慮對算法內容的監管或與支持言論自由的憲法精神相悖,更為防止與算法相關的立法限制阻礙本國數字企業在全球范圍內擴展業務,美國一貫堅持“基于言論自由和市場自由”的算法治理,算法治理規則更傾向于算法保密。
當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方興未艾,大國競爭日趨激烈、傳統地緣政治回歸,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面對波譎云詭、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建設和改革,為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第一,積極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維護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的多邊體系。國家理性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結合體。[9]當前逆全球化思潮持續涌動,美國加快塑造“在岸外包”“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三位一體的供應鏈保障體系,以提升自身關鍵供應鏈的韌性與安全。[10]美國在經貿領域極力排斥中國,致使傳統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失序”危險,其合法性和有效性難以維持。為此,國際社會更需要在價值與利益的大碰撞中尋求新的平衡點。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一貫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高舉真正的多邊主義旗幟,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贏得國際社會廣泛認同與支持。2023年4月5—7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中法兩國承諾將共同推動世界安全與穩定、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11]中法兩國在維護和重塑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秩序上的共同立場,無疑是對美國主張的經濟“脫鉤論”的有力回擊,為當前處在裂變中的全球治理機制注入更多穩定性和確定性。

2023年4月5日,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伊維拉在瑞士日內瓦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表示中國為加強多邊貿易體制發揮重要作用。

2023年7月2日,在意大利羅馬的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總部,與會者慶祝屈冬玉(中)勝選連任。
第二,堅定維護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以制度型開放引領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一方面,要推動改革WTO爭端解決機制,恢復其爭端解決功能。入世20多年來,中國一直是WTO規則的遵守者和擁護者,“不改變WTO基本原則”“維護WTO的主渠道作用”等是中國一貫的基本立場,未來中國應當推動爭端解決機制向快速、高效、簡潔的方向改革,推動WTO議題范圍擴容、建立緊急狀態下貿易協調機制以及引入線上便利化手段等。另一方面,面對愈發嚴峻的外部經濟環境,中國需持續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以更高水平的“外循環”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截至2023年6月,中國簽署并生效的自由貿易協定共19個,其中與發達國家簽訂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含升級版)有6個,包括瑞士、冰島、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和韓國。正在談判中的自由貿易協定共10個。[12]作為制造業大國,中國與歐盟、東盟以及周邊、區域和次區域等市場都有著密切的經濟聯系,中國與歐盟、東盟等在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都有相近的立場。除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優化創新法治環境、規范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程序等手段外,中國積極對接國際先行規則,充分發揮中歐經濟合作的“壓艙石”作用,繼續深化《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與“中日韓+東盟”經濟一體化,必將在不同的經濟議題上形成多層次朋友圈。
第三,抓住數字經濟等新增長點,為全球數字經濟新規則提供“中國方案”。早在2016年擔任G20杭州峰會輪值主席國時,中國便牽頭制定和發布了全球首個由多國領導人共同簽署的數字經濟政策文件《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標志著世界數字經濟發展正式進入全球經濟治理議程。2020年,中國發起《全球數據安全倡議》,呼吁國際社會共同應對數據安全風險挑戰。目前全球尚未形成統一的規則和各國相互協調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數字鴻溝”等全球性問題依然突出,中國在積極探索適合自身數字化發展規范和原則的同時,為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更多公共產品。一方面,充分發揮中國市場優勢和數字技術領先優勢,塑造數字經濟規則的“中國標準”。充分發揮在5G、5.5G、6G移動通信和數字支付服務、跨境電子商務等領域的比較優勢,積極借助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自由貿易區網絡,共同制定并形成數字經濟國際規則體系。另一方面,著力推動“數字絲綢之路”機制化建設,打造區域數字經濟交流合作平臺。中國現已與17個國家簽署“數字絲綢之路”合作諒解備忘錄,與23個國家建立“絲路電商”雙邊合作機制,與周邊國家累計建設34條跨境陸纜和多條國際海纜。中國將在夯實“數字絲綢之路”的“硬聯通”、加快“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上,持續提升“軟聯通”水平,推動數字政策溝通、規則對接、標準兼容等深層次合作,優先與數字基礎較好并同中國簽署“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合作諒解備忘錄的經濟體達成數字經濟協定。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制度型開放與全球經濟治理制度創新研究”(項目批準號:20&ZD061)、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全球治理與人類命運共同體重點實驗室和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2022年度特別委托項目(項目批準號:?GD22TWCXGC1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1]?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383頁。
[2]?向松祚:《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不對稱性和不穩定性——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什么崩潰?》,載《金融博覽》2014年第7期,第10頁。
[3]?岳圣淞:《圖式演繹、敘事重構與冷戰后美國對華價值觀外交》,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23年第4期,第158頁。
[4]?陳偉光、韓雪瑩:《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趨勢研判》,載《開放導報》2022年第5期,第20頁。
[5]?“The?Lobby?Network:?Big?Tech’s?Web?of?Influence?in?the?EU,”?June?2023,?https://corporateeurope.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8/The%20lobby%20network%20-%20Big%20Tech%27s%20web%20of%20influence%20in%20the%20EU.pdf.
[6]?王中美:《新干預主義背景下全球經濟治理的變革》,載《國際經貿探索》2022年第5期,第89頁。
[7]?Internal?Revenue?Service:?“Inflation?Reduction?Act?of?2022,”?May?2023,?https://www.irs.gov/inflation-reduction-act-of-2022.
[8]?趙海樂:《數字經濟中的算法治理:美歐路徑差異與中國策略》,載《國際經貿探索》2023年第5期,第107-120頁。
[9]?馬克思·韋伯著,林榮遠譯:《經濟與社會: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5-13頁。
[10]?陳積敏:《美國構建“三位一體”供應鏈安全體系》,載《中國投資(中英文)》2022(ZB),第74頁。
[11]《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聯合聲明(全文)》,外交部,2023年6月,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4/t20230407_11056239.shtml。
[12]?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2023年6月,http://fta.mofcom.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