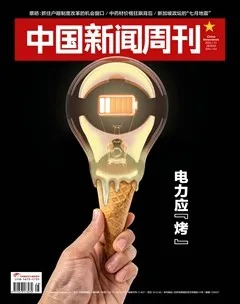金融反腐提速
張馨予

圖/視覺中國
7月15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消息,光大集團股份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唐雙寧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這一消息在業內并不算意外——在唐雙寧五年半前退休時,就有傳言稱其是背著處分“落地”。
年初以來,金融系統內已有多名中管干部接受審查調查,唐雙寧是其中之一。顯然,2023年金融反腐持續提速。
《中國新聞周刊》梳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披露信息發現,截至7月24日,金融系統內的省管及以上級別干部已有60多人接受審查調查,40多人被處分。60多人中,除了中管干部多人,還有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國企和金融單位干部40多人,省管干部10多人。
今年1月10日,二十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公報公布,特別提到了下一階段黨風廉政工作的重點領域,其中就提到金融領域。西南政法大學金融法治研究院院長王煜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一輪金融反腐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工作向縱深發展的體現,標志我國的反腐敗工作向深水區推進。
銀行業仍是反腐重點
銀行業依舊是今年金融反腐的重點區域。今年以來被查的60多名金融系統內省管及以上級別干部中,有30多人來自銀行。這與我國銀行業的重要性和特點有著緊密關系。
中共北京市委黨校政治學教研部副教授王塵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我國,銀行在金融業中發揮的作用非常關鍵,作為金融業的核心機構之一,在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利益牽扯面廣。
據官方數據,2022年末,我國金融業機構總資產為419.64萬億元,其中,銀行業機構總資產為379.39萬億元,占有金融資產的比例超過90%。
另外,金融反腐也出現了鏈條化的趨勢,即同一金融機構前后有多名干部被查。今年多位被查的中管干部中,有兩位來自光大集團——7月15日被查的唐雙寧和4月5日被查的李曉鵬均曾任光大集團股份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一職,且是前后任。
而此前,光大系統已有多人落馬,成為腐敗“重災區”。包括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行政總裁陳爽,中國光大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朱慧民和原黨委委員、副總經理黃智洋,光大銀行原黨委副書記、副行長張華宇,光大銀行深圳分行原副行長鄒建旭,光大銀行南寧分行兩任原黨委書記、行長蘇樹德和周江濤,光大城鄉環保有限公司原總經理陳鵬等。
《財新》曾報道,在2021年10月中央第五巡視組進駐光大集團之前,有舉報信指控李曉鵬搞小圈子和山頭文化,過度提拔河南籍干部,大肆招聘河南人。上述被查的光大系統人員中,鄒建旭、黃智洋、周江濤、陳鵬和張華宇都是河南籍干部,其中張華宇和李曉鵬是同鄉,也是河南銀行學校同一級的同學。
此前亦有金融領域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近些年光大集團被查人員,除了多是李曉鵬下屬,也多與唐雙寧關系密切。
此外,中國建設銀行深圳市分行也有多人被查。3月23日和24日,中國建設銀行深圳市分行資深專員趙芝然和該行原黨委副書記、副行長易景安先后被查。而在2022年4月,該行原黨委書記、行長王業,原黨委副書記、副行長張學慶和原風險總監韓鳳林接受調查。同在去年4月,招商銀行原黨委書記、行長田惠宇被查,他此前曾任中國建設銀行深圳市分行黨委書記、行長。2022年7月,曾任該行信貸審批部副總經理、風險管理部授信審批中心副總經理的李保奇被查。
在王塵子看來,中國建設銀行深圳市分行前后多人被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隨著我國加大對金融業務的監管力度,單獨作案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而現代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相互關聯,業務鏈環環相扣,任何環節出現腐敗問題,都可能傳染至其他環節。另外,金融圈相對較小,容易形成裙帶關系,腐敗可能在同學、朋友和親屬間傳遞,導致金融腐敗的親緣案件較多。
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廉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暉則指出,這也意味著金融領域的查辦策略可能做了調整,拓展了案件查辦的廣度和深度,強調“以案帶案”,查“案中案”,因此金融領域腐敗案件的數量自然也就增加了。
金融腐敗如何運作?
根據專家的總結,結合已曝光的案件,金融腐敗有三種傳統類型,分別是利用職務便利獲取腐敗利益、利用審批權力謀取腐敗租金、利用內幕信息攫取腐敗收益。
利用職務便利獲取腐敗利益是金融腐敗案件中極為常見的類型。《中國新聞周刊》梳理發現,今年以來,幾乎所有受到黨紀黨務處分的金融系統干部的通報中,都提到利用職務便利或職權影響謀取利益的情節。
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武長海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利用職務便利獲取腐敗利益的行為,多發于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及重要崗位人員,他們主管、經手、管理公共財產,某些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便利,通過非規范交易、偽造單據、假借戶頭、收入不入賬等方式,直接收受他人名為手續費、勞務費、傭金等的現金或實物,或者間接為親屬、朋友等利益相關人從事金融活動提供資金便利。
第二類傳統類型的金融腐敗是利用審批權力謀取腐敗租金,這在金融腐敗案件中同樣常見,通常也是建立在“利用職務便利”的基礎之上。
“腐敗總是與相對稀缺資源的壟斷權相伴而生”,經濟學家吳敬璉曾說,面對稀缺資源,當配置資源的權力沒有受到有效的約束時,就會為權力尋租提供機會,引起嚴重的腐敗問題。
銀行等金融機構掌握著信貸審批等權力,近年來屢屢發生的銀行系統腐敗,很多都是“關鍵少數”利用審批權力開展腐敗。國家開發銀行原黨委書記、董事長胡懷邦這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國家開發銀行是國家出資設立、直屬國務院領導、支持中國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發展、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國有開發性金融機構。反腐專題片《零容忍》顯示,2015年,華信能源有限公司向國開行申請48億美元的巨額貸款授信,而這不符合黨中央國務院對于國開行的定位。此前,黨中央國務院啟動深化國開行改革工作,明確要求國開行進一步聚焦服務國家戰略,進一步壓減商業性項目。
胡懷邦作為國開行“一把手”,從“華信系”掌門人葉簡明處收受了數千萬元賄賂,用“一把手”的權力強力推動,把華信的業務包裝成、解讀成一種政策性業務,使得國開行批準了這筆巨額貸款。隨著葉簡明在2018年涉嫌違法被調查,“華信系”迅速隕落,國開行面臨著巨額貸款難以收回。
除了銀行等金融機構,金融監管機構也可能利用審批權力謀取腐敗租金。王塵子解釋說,金融監管部門對金融市場準入和機構業務范圍實行較為嚴格的管理和限制,如果某些領導的審批權伸縮區間過大,就有機會通過拒絕批準、提出不合理要求、故意拖延審批時間等方式謀取私利。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利用審批權力謀取腐敗租金的案件中,是金融機構高層、企業主和監管人員三方“貓鼠一窩”,金融監管部門充當“內鬼”。
山西金融系統曾在2020年迎來一場反腐風暴,山西省農村信用社、城市商業銀行、駐晉銀行、金融企業、金融監管部門等多個系統都被卷入風暴之中。
不法企業“德御系”2006年成立融資擔保公司,隨后又注冊、收購了60余家公司。多年來,山西省多家農信社、城商行等金融機構共20名公職人員收受“德御系”財物,為“德御系”多筆違規融資貸款大開綠燈,“德御系”違規融資貸款達兩千多億元。
在“德御系”不斷膨脹的過程中,監管部門也在被圍獵中失守。調查顯示,陽泉市商業銀行原黨委書記、董事長李首明先后為“德御系”關聯企業累計違規融資上百億元。2017年,國家審計署審計發現陽泉市商業銀行出現違規經營票據業務問題,李首明為逃避處罰,打聽到時任山西銀監局黨委書記、局長張安順有一個愿望是退休后開茶樓,于是送給張安順500萬元用于開辦茶樓。張安順隨后擅自將對陽泉市商業銀行的處罰降低,從沒收銀行2000余萬元、對董事長個人罰款50萬元、吊銷執業資格,降為對銀行罰款100萬元,對董事長個人罰款10萬元。
金融腐敗案件中,還有一類是利用內幕信息攫取腐敗收益。安徽省委原常委、常務副省長陳樹隆案是這類金融腐敗案件的典型。
陳樹隆曾被吹捧為安徽的“股神”。其落馬后,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檢監察室工作人員指出,陳樹隆表面上打著招商引資、金融創新等幌子,給他選中的一些上市的公司或者私營企業大量的政策優惠、財政扶持,在背后利用職權購買原始股、炒作股票,以此獲取暴利。
福建省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查明,2009年至2015年,陳樹隆作為相關股票的內幕信息知情人員,在內幕信息敏感期內買入上述股票,累計成交金額共計人民幣1.21億余元,非法獲利共計人民幣1.37億余元。
王塵子指出,金融行業專業性強,信息不對稱現象較為突出,金融系統內,銀行業、保險業、監管部門等的從業人員都可能利用內幕消息獲利,“腐敗交易的內容既可能是政策性信息,也可能是經營性信息;腐敗交易主體既可能是企業和行業公職人員,也可能是某領域的公職人員之間;從現實表現看,腐敗交易方式既可能是官員自己或其親屬介入市場獲利,也可能是向他人泄露信息尋租或受賄”。
新型腐敗
近幾年,金融領域的腐敗還出現了一種新趨勢,即從傳統型腐敗升級為新型腐敗。毛昭暉認為,新型腐敗是貪腐者為了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種“腐敗變異”,職務犯法犯罪構成要件不清晰,在罪刑法定的司法原則下較難認定,具有極大的逃逸機會。
今年2月23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官網發布文章《堅決打贏反腐敗斗爭攻堅戰持久戰》指出,要加大對“影子股東”“影子公司”“政商旋轉門”“提前筑巢”“逃逸式辭職”等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的查處力度。
在今年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的金融腐敗案件中,有多個涉及“影子公司”“影子股東”。其中的運作邏輯,在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黨委副書記、行長孫德順案中有著清楚的體現。
根據反腐專題片《零容忍》披露的細節,孫德順安排兩名老部下作為代理人,開設了兩家投資平臺公司,兩家公司前臺的法人,實際只是為孫德順代言的“影子”。一方面,孫德順在中信銀行利用公權力為企業老板批貸款。與此對應,這些老板有的以投資名義,將巨資注入他實際控制的平臺公司,有的則為平臺公司送上優質投資項目或投資機會。平臺公司用這些老板提供的資金投入那些老板提供的項目,以錢生錢,和老板們共同獲利分紅,形成利益共同體。
《零容忍》披露,兩家平臺公司是孫德順的核心經營團隊,是遮蔽在他身前的第一層“影子”,在平臺公司之下又設立了十多家項目公司作為第二層“影子”,項目公司和行賄企業并不直接交易,而是雙方各自再成立空殼公司作為第三層“影子”,多層影子公司層層嵌套。交易主體本身已經魅影重重,資金往來又偽裝成各種貌似合法的金融產品、股權投資協議。
“影子公司”“白手套”之外,近幾年的金融腐敗案件中,政商“旋轉門”和銀企“旋轉門”也十分多發,而這類腐敗往往伴隨著“提前筑巢”和“逃逸式辭職”。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在今年1月刊發文章指出,銀企“旋轉門”腐敗中,提前編織權力網、“期權式腐敗”等特征明顯。

比如在中國農業銀行某二級分行一起職務犯罪案件中,涉案人員因違紀違法問題線索被上級行紀委調查,萌生離職念頭。他找到多名曾在授信用信等方面接受過自己幫助的商人老板,表露離職經商意愿,希望他們屆時能給予經濟上的幫助,相關商人老板也承諾即使該涉案人員不再擔任該分行行長,以后也會給予他經濟上的好處。
新型腐敗的出現,王塵子指出,是因為金融市場交易日趨復雜,資本運作更趨智能化和復雜化,金融腐敗很可能被合規合法的表面形式所掩蓋。另外,金融領域的專業化特點很強,隨著金融創新不斷發展,銀行、保險、信托、證券、基金等機構推出大量金融創新產品,新型腐敗可能打著金融創新產品的名號實施。
毛昭暉認為,隨著中央不斷加大反腐敗力度,腐敗者也開始學習和轉型,“毫無疑問,金融領域部分貪腐的‘精英,握有更多資源、資本,所以會逐步轉向新型腐敗,金融創新也為他們提供了更大的貪腐空間”。
如何治理金融腐敗?
如今,金融反腐已經成為當前反腐敗工作的重點之一。王塵子指出,我國抑制金融腐敗主要有六大支柱:金融機構自身的自律監督,金融監管機構的外部行業社會監管,由財稅、審計等構成的外部社會監管,紀檢監察機關的專責監督,公檢法機關的法律監督,以及社會監督。
今年以來,作為六大支柱之一的自律監督被重點強調。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文提出“破除‘金融精英論‘唯金錢論‘西方看齊論等錯誤思想,整治過分追求生活‘精致化、品味‘高端化的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即是重申金融從業者自律的重要性。
審計監督的力量也越來越被強化。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曾在4月發文表示,尤其涉及“影子股東”“影子公司”“政商旋轉門”等新型和隱性腐敗的問題線索時,要優先考慮借助審計力量。武長海說,不少沉淀多年的金融腐敗,都是借助審計的力量挖出來的。
而作為“最后一道防線”的金融監管機構的外部行業社會監管,王煜宇指出,當其出現腐敗,比金融交易腐敗更具系統性、體制性、隱蔽性和破壞性。今年接受審查調查的60多名金融系統內的省管及以上級別干部中,有近10人來自監管機構,其中朱從玖在金融監管系統工作逾20年。
在王煜宇看來,我國現行金融監管機構由于在數目上大大少于監管對象,在監管信息獲取上大大弱于監管對象,在監管收益(特別是個人工資收入)上大大低于監管資金,很容易被監管對象俘獲,監管機構相對于監管對象的專業性和獨立性無法保障,屬于俘獲性金融監管制度。這不僅不能有效遏制金融監管腐敗,反而可能為金融監管腐敗推波助瀾。
解決這些問題,她認為需要規范金融監管權力的行使,包括明確金融監管權力的具體內容和實施主體,完善金融監管程序性法律制度建設,完善“監管”金融監管的約束問責和激勵評估機制。同時,要加強金融監管機構的獨立性,因為金融監管的獨立性是金融監管制度得以實現的前提,“維護金融監管的獨立性,是金融監管制度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反腐的六大支柱之外,還有不少專家都提出應加強科技應用,這在新型金融腐敗的治理上更具現實意義。中國證監會原紀委書記、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原辦公室主任黎曉宏等人在所著的《金融反腐論》一書中提到,加強金融系統反腐工作,要善于收集數據、分析數據、挖掘數據、理解數據、運用數據,打造“數字化”反腐鐵籠。
該書指出,企業或個人經濟行為的表現根植于其關聯關系,而關聯關系就像DNA(脫氧核糖核酸)一樣,其特征決定了企業或個人未來行為,并最終演化為不同的關聯風險。通過對風險定量分析,可以發現和預警金融風險和腐敗行為。而大數據基因圖譜技術可以鑒定企業經濟行為,得出金融風險的類型和程度。
此外,該書還提出可以建設大數據金融腐敗預警框架和金融腐敗預警核心指標體系。以大數據金融腐敗預警框架為例,采用多元異構、跨域關聯,基于全量數據,利用關聯圖譜技術,通過股權控制、高管關系、資金往來、社交信息等,可以描繪目標企業、法人的社會經濟利益網絡拓撲圖。不同時點企業及個人的社會經濟利益關系不同,通過大數據動態實時監測,可以描繪監測目標的風險狀態,高維度俯視風險起源、傳導、爆發、處置的全流程。
“現在是數字化的時代,金融產業本身就是高度技術化和信息化的產業,或者說其本身就是一個信息產業。”王煜宇認為,將數字信息科技應用于監管,將在很大程度上消解金融產業信息不對稱、權責不對等的問題,為治理金融腐敗帶來可期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