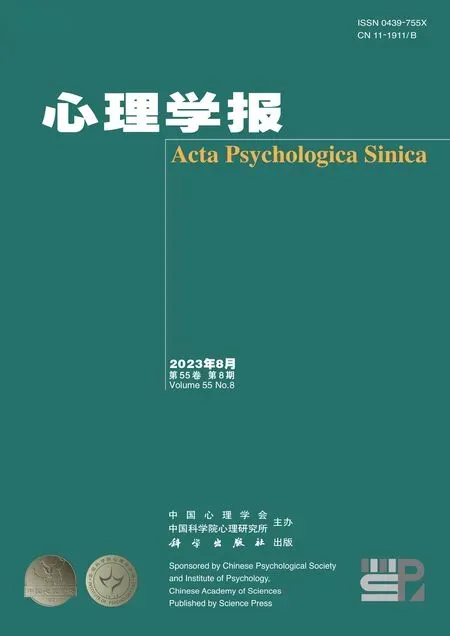教導何以有方?教師辯證反饋對大學生團隊創造力的作用機制*
張建衛 周愉凡 李林英 李海紅 滑衛軍
教導何以有方?教師辯證反饋對大學生團隊創造力的作用機制*
張建衛1周愉凡2李林英3李海紅4滑衛軍1
(1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北京 100081) (2青島大學師范學院, 山東 青島 266071) (3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北京 100081) (4山東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濟南 250014)
采用實地問卷調查和縱向現場實驗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從社會信息加工理論視角探討了教師辯證反饋對大學生團隊創造力的作用機制。結果發現: 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創造力呈正相關關系; 團隊信息深加工中介了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 精熟氛圍在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信息深加工關系間起正向調節作用, 而績效氛圍在二者間起負向調節作用; 教師辯證反饋能夠通過團隊信息深加工對團隊創造力產生有條件的、正向的間接影響, 當精熟氛圍水平高、績效氛圍水平低時, 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間接促進作用更為顯著。研究從理論上提出教師辯證反饋并實證探索其對團隊創造力的作用機制, 從團隊創新層面上豐富和深化了“教育與發展”這一經典理論范疇, 并為促進大學生團隊創造力發展提供了實踐啟示。
教師辯證反饋, 團隊創造力, 團隊信息深加工, 精熟氛圍, 績效氛圍
1 問題提出
隨著科技創新環境不確定性和任務復雜性的不斷增強, 團隊日益成為大學生科技創新活動的重要載體, 團隊創造力正在成為高校創新教育的重要內容, 教師反饋在團隊科技創新活動中的關鍵性作用日益凸顯。近年來反饋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 有效反饋能夠增進個體及團隊的創造力(Mavri et al., 2020; Rupert & Kern, 2016)、執行功能(王元等, 2020)、內部動機(Koka & Hein, 2005)和積極整合行為(王永麗, 時勘, 2003)等。目前學者根據反饋效價、反饋意圖及反饋焦點等, 將反饋分為積極和消極反饋(Zhou, 1998)、信息型和控制型反饋(Ryan, 1982)、任務焦點和特質焦點反饋(Smither & Walker, 2004)等類型。不過, 上述反饋劃分趨于機械單一, 難以反映出社會情境的復雜性及動態性特征, 更無法體現反饋的質量水平, 且反饋結構及其后效也缺乏多方法綜合驗證。此外, 大多數研究仍集中于組織行為領域, 鮮見針對教育尤其是高校創新教育領域的反饋研究。基于此, 辯證反饋從理論和實踐層面上彌補了已有反饋研究的不足。教師辯證反饋是反饋理論在創新教育領域的拓展和深化, 是一種體現教師辯證思維并遵循學生發展規律的信息反饋活動, 能夠反映出真實情境下更為全面復雜、動態變化的信息反饋活動。教師辯證反饋活動中所蘊含的全面性、發展性認知方式和指導性信息, 可對團隊創新實踐發揮引領、組織和激發作用, 從而提升團隊創造力水平。
本研究從社會信息加工理論視角出發, 揭示教師辯證反饋對大學生團隊創造力的作用機制。社會信息加工理論強調社會環境中釋放出的信息對人的認知行為產生的影響(Salancik & Pfeffer, 1978), 人們通過理解加工特定社會信息來決定后續行為表現。那么, 教師辯證反饋作為一種社會環境信息, 可能對學生團隊信息加工產生顯著影響。團隊信息深加工是團隊成員開展信息與觀點交換的重要認知過程(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4), 而倡導信息交換與整合的重要他人指令則會提升團隊信息深加工水平(Kooij-de Bode et al., 2008; Stasser & Titus, 1985)。同時, 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信息深加工的促進作用可能會受到團隊情境因素尤其是團隊動機氛圍的制約。社會信息加工理論還指出組織特征等背景因素在信息加工過程中的重要作用(Boekhorst, 2015; Salancik & Pfeffer, 1978), 團隊動機氛圍是反映團隊內部特征的背景因素, 體現出團隊成員對成功標準的共同感受, 會對團隊成員認知與行為產生影響(Nerstad et al., 2013), 據此推斷團隊動機氛圍是教師辯證反饋影響團隊信息深加工的重要邊界條件。為此, 本研究基于社會信息加工理論探索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作用機制, 并揭示團隊信息深加工的中介效應和團隊動機氛圍的調節效應。
1.1 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
教師辯證反饋是指教師自覺開展的、向學生提供具有變化性、關聯性和整合性特征, 能夠全面反映學生表現并促進學生成長發展的信息活動。教師辯證反饋主要包括全面性和發展性兩個維度, 全面性維度既包含反饋效價的矛盾統一性, 又包含反饋內容的多維性; 發展性維度既包括反饋取向的現實性和可行性, 又包括反饋指向的未來性和挑戰性。教師辯證反饋以學生能力素養發展為導向, 主要目標是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和持續發展, 其與組織情境中以產值或績效為導向的上級反饋存在顯著區別。教師辯證反饋與學生團隊創造力發展緊密關聯。具體而言, 在高校創新教育情境中, 團隊創造力是團隊成員在團隊領導者帶領下, 通過團隊協作產生具有新穎性、獨特性社會價值的科學成果的智能品質或能力(劉玉新等, 2013)。在大學生科技創新過程中, 教師作為專業導師與團隊領導, 是構成團隊社會信息的主要來源(e.g., Ali et al., 2023)。社會信息加工理論認為環境信息為團隊提供了用以構建事件的重要線索(Salancik & Pfeffer, 1978), 據此教師辯證反饋作為一種環境信息能夠為學生創新行為提供啟示與指引, 在團隊科技創造活動中發揮關鍵性作用。
首先, 教師辯證反饋能對團隊創新方向和過程進行指導, 提高團隊創新能力和創意水平。社會信息加工理論認為, 社會環境信息為團隊態度和取向提供了應然性期望, 進而影響團隊將行為進行合理化的過程(Salancik & Pfeffer, 1978)。教師辯證反饋涉及積極與消極反饋的內容, 而積極與消極反饋均與某種規范、標準或期望密切相關。根據社會信息加工理論, 教師辯證反饋會對團隊行為表現產生影響。一方面, 教師辯證反饋包含了對團隊優點進行肯定的信息, 有助于激發團隊的成就感知和內部動機(Fodor & Carver, 2000), 進而促進創造力發展(Zhou, 1998); 另一方面, 教師辯證反饋有助于發現團隊創新過程中的問題和不足, 促使團隊全面分析當前狀態與目標水平之間差距, 推動團隊知識學習與能力提升。同時, 教師辯證反饋所體現的辯證思維藝術能夠啟發團隊成員多視角發現問題與整合信息, 激發團隊產生有價值的創意(Nisbett et al., 2001)。其次, 教師辯證反饋能夠增進團隊成員間開放交流, 推進創意共享與實施過程。創新具有雙元性和辯證性, 既包含探索式創造活動又貫穿利用式創新活動, 團隊在此過程中常出現任務間或成員觀點間的矛盾與沖突(Bledow et al., 2009), 而教師辯證反饋則能啟發成員接納創新中的矛盾性, 引領團隊有效應對沖突和壓力, 從而推動高水平創意產生與實施(Han et al., 2021)。最后, 教師辯證反饋的發展性取向, 能夠幫助團隊樹立學習目標導向, 促進團隊合作和內在成長(Son & Kim, 2016), 提高團隊創造效率與質量。據此提出假設:
假設1: 教師辯證反饋正向影響團隊創造力。
1.2 團隊信息深加工的中介作用
團隊信息深加工是指團隊成員間開展信息和觀點交換并對個體層面觀點進行處理, 將有關結果反饋給團隊并進行討論與整合的過程(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4)。這一過程特別強調信息分享與觀點涌流, 既倡導團隊信息收集的廣度, 又注重團隊信息處理的深度。基于社會信息加工理論, 教師辯證反饋作為社會環境信息源為團隊認知加工提供了豐富線索。由于教師辯證反饋包含辯證性思想及發展性指導內容, 有助于促進團隊信息分享、交換、反思和整合等信息深加工過程, 而團隊信息深加工又能幫助團隊進一步發現新信息和新觀點, 促進團隊創造力發展(Huang & Liu, 2021)。
一方面, 教師辯證反饋驅動團隊信息深加工。首先, 教師辯證反饋能夠增強團隊信息多樣性, 促進團隊信息深加工。教師辯證反饋通過指導團隊成員從多渠道、多層面采集信息, 并倡導團隊運用辯證性思維對信息進行系統加工, 有助于培養團隊開放式和多樣化認知框架。當團隊內部持有不同觀點時, 重要他人引導大家對不同觀點展開交流與討論, 從而促進成員間相互理解, 對信息進行更系統的整合加工(Harvey, 2015)。其次, 教師辯證反饋能夠激發團隊認知需求, 提升團隊信息深加工水平。高認知需求團隊傾向于認為當前情境是模棱兩可、存在矛盾的, 為了更明晰地解釋當前情境, 大家會付出更多努力對多方面信息進行搜索、討論與整合(Cacioppo et al., 1996)。教師辯證反饋以辯證思維為基礎, 強調廣泛存在的矛盾性與關聯性, 有助于激發團隊認知需求, 推動團隊展開深度信息處理活動(Huang & Liu, 2021)。
另一方面, 團隊信息深加工又促進團隊創造力提升。其一, 團隊信息深加工助推團隊獲得豐富的信息資源, 為團隊創造力發展奠定基礎。團隊信息深加工鼓勵團隊成員分享知識經驗, 并為其提供實現團隊目標的機會, 使成員認識到自身信息的獨特性, 增強彼此間信息共享意愿, 從而幫助團隊掌握豐厚的信息資源(Gong et al., 2013)。創造力成分理論認為信息資源是創造力的重要構成(Amabile, 2012), 尤其是在信息深加工水平較高的團隊中, 成員能夠連接和豐富之前未連接的想法并生成新知識與新觀點, 推動團隊創造力發展。其二, 團隊信息深加工促進團隊作出高質量決策, 提升團隊創造力。信息深加工既是團隊成員自由闡述個人想法和觀點的過程, 也是成員學習和評估他人觀點的過程, 有助于洞悉彼此所獲信息的共同性和差異性, 使團隊在決策時能夠有效匯聚和處理各種有益信息, 產生新穎而有益的團隊決策, 將團隊多樣化信息處理轉化為高水平團隊創造力(Breugst et al., 2018)。據此提出假設:
假設2: 團隊信息深加工在教師辯證反饋和團隊創造力關系間起中介作用。
1.3 團隊動機氛圍的調節作用
社會信息加工理論指出, 團隊內部環境信息能夠傳遞出對成員某些特定行為的期望, 從而影響團隊成員行為(Ali et al., 2023)。據此推斷, 承載內部環境信息的團隊動機氛圍可能會影響團隊創新過程。團隊動機氛圍是指團隊成員通過對團隊規范、程序和實踐的感知, 從而形成對現有成功和失敗標準的共同感知(Nerstad et al., 2013), 包括精熟氛圍和績效氛圍。具體而言, 精熟氛圍是指鼓勵成員學習成長、自我提升、任務掌握和合作的團隊氛圍(Nerstad et al., 2013), 可能促進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信息深加工的正向作用。在高精熟氛圍的團隊中, 鼓勵合作與積極的社會互動(?erne et al., 2014), 為信息和知識的交換與整合奠定了基礎, 且該氛圍強調團隊成員的自我發展與能力提升, 成員多以自我超越為目標, 傾向于進行更多的知識共享交流, 從而提升自身能力水平(Nerstad et al., 2018)。在此過程中, 團隊成員易產生更強的內部動機(Buch et al., 2017), 更可能思考與采納教師辯證反饋中的有益信息, 增強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信息深加工的正向作用。
作為團隊動機氛圍的另一維度, 績效氛圍是指強調成員間比較與競爭, 追求外部結果的團隊氛圍(Nerstad et al., 2013), 易削弱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信息深加工的促進作用。高績效氛圍的團隊聚焦于成員間社會比較和競爭, 推崇能力水平的外部評價, 成員易將同伴視為競爭對手, 追求出人頭地而非內在成長和團隊協作, 更傾向于隱藏知識信息, 從而為自己謀取競爭優勢和勝出機會(?erne et al., 2014)。加之, 成員因害怕信息共享使自身失去競爭優勢而產生防御定向, 會進一步阻礙彼此學習和信息交流(李浩, 呂鸞鸞, 2019)。此時, 雖然教師辯證反饋中蘊含著有助于團隊信息交流或合作的信息, 但成員難以對教師反饋信息進行充分思考和吸納, 易阻抑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信息深加工的正向影響。據此, 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 團隊精熟氛圍在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信息深加工關系間起正向調節作用, 即當精熟氛圍水平更高時, 二者間的正相關關系更強。
假設4; 團隊績效氛圍在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信息深加工關系間起負向調節作用, 即當績效氛圍水平更高時, 二者間的正相關關系更弱。
精熟氛圍和績效氛圍可能調節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信息深加工的關系, 進而影響團隊創造力。在團隊互動中, 成員可能同時感知到不同水平的精熟氛圍和績效氛圍, 二者會共同對團隊動機或行為產生影響(Buch et al., 2017)。具體而言, 精熟氛圍水平高時, 團隊成員更注重技能學習與自我超越(Nerstad et al., 2013), 此時更容易重視教師辯證反饋信息, 表現出較高的知識與信息加工水平, 進而促進團隊創造力提升。與此同時, 若團隊績效氛圍水平低, 團隊內部更不易出現成員間的社會比較和競爭, 有利于團隊產生信息分享意愿(?erne et al., 2014), 進一步強化教師辯證反饋通過團隊信息深加工對團隊創造力產生的促進作用。由此, 當團隊精熟氛圍強、績效氛圍弱時, 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間接促進作用尤為顯著。據此提出假設:
假設5: 教師辯證反饋通過團隊信息深加工對團隊創造力產生有條件的、正向的間接影響, 即當精熟氛圍水平高、績效氛圍水平低時, 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間接促進作用更為顯著。
綜合上述, 本研究的理論模型如圖1。為此開展兩項研究: 研究1通過對參加科技創新大賽的大學生團隊進行實地問卷調研, 探討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作用機制, 以此增強研究的外部效度; 研究2采用縱向現場實驗法對全模型進行檢驗, 通過多時點、多來源采集數據, 考察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因果影響, 以此提升研究的內部效度和生態效度。

圖1 理論模型
2 研究1: 實地問卷研究
2.1 研究方法
2.1.1 研究對象
在“X杯全國大學生機器人創新大賽”現場開展問卷調研, 研究樣本為全國各地大學生科技創新團隊, 每個團隊確保至少有3名成員填寫問卷。樣本選取遵循以下原則: 其一, 團隊有明確的指導教師, 能對團隊進行反饋與指導; 其二, 團隊是科技創新團隊, 旨在培養團隊成員的科技創新能力, 激發成員創新性想法或實踐操作、優化創意的操作過程、改進裝置的實用性等; 其三, 團隊任務需成員協作完成, 成員間保持溝通、交流與協作; 其四, 團隊目標具有一致性, 如在本次機器人創新大賽中獲得一定成績。此次研究樣本及情境與教師辯證反饋和學生團隊創造力密切相關。調研程序分為兩步: 一是現場調研, 研究者深入大學生機器人創新大賽現場, 向創新團隊解釋調研目的、問卷保密性和匿名性以及問卷作答的注意事項, 并開展問卷施測; 二是回收問卷, 研究者與團隊負責同學約定時間地點回收問卷。
研究者向87個團隊發放了365份問卷, 回收80個團隊共335份問卷, 剔除空白作答、直線作答(如所有題目都選擇同一個答案)及無意義規律作答(如按照“S”形選擇答案)等無效問卷后, 最后收到來自全國34所高校的78個科技創新團隊(有效團隊樣本回收率為98%)、306名成員(有效個體樣本回收率為91.3%)的樣本數據。樣本構成如下: 一是團隊樣本。來自“原985高校”團隊14個(17.9%), “原211高校”團隊16個(20.5%), 其它高校團隊48個(61.5%); 團隊性別構成0~25%男生團隊1個(1.3%), 26%~50%男生團隊2個(2.5%), 51%~75%男生團隊18個(23.1%), 76%~100%男生57個(73.1%); 平均團隊規模為3.92人(= 0.75)。二是個體樣本。男生274人(89.5%), 女生32人(10.5%); 專科生48人(15.7%), 本科生255人(83.3%), 研究生3人(1.0%); 大一80人(26.1%), 大二164人(53.6%), 大三40人(13.1%), 大四19人(6.2%), 研一2人(0.7%), 研三1人(0.3%); 理科48人(15.7%), 工科251人(82.0%), 人文社科4人(1.3%), 其他學科3人(1%)。
2.1.2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大多選用在國內外權威期刊上發表并被廣泛使用的問卷, 由教育學、心理學專業專家結合大學生團隊科技創新情境進行了轉譯、回譯及修正。除特殊提到的量表外, 各量表題項均采用李克特5點量表測量, “1~5”分別表示“非常不符合~非常符合”。
(1)教師辯證反饋。采用周愉凡(2022)開發的教師辯證反饋問卷, 包含發展性與全面性兩個維度, 共9個題項, 如“指導教師提示我們: 既要創新又要遵守規范”。采用Amos 24.0對該問卷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模型擬合結果良好(χ2/= 5.09, RMSEA = 0.07, CFI = 0.99, TLI = 0.98)。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4, 發展性與全面性維度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93和0.89。
(2)動機氛圍。采用Nerstad等(2013)開發的動機氛圍量表, 包含精熟氛圍6個條目(如“在我們團隊, 鼓勵成員之間合作并相互交換想法”)和績效氛圍8個條目(如“在我們團隊, 鼓勵成員之間的競爭”), 精熟氛圍和績效氛圍維度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5和0.79。
(3)團隊信息深加工。采用Kearney等(2009)開發的團隊信息深加工問卷, 共4個題項, 如“我們團隊的成員通過公開分享自己的知識來實現彼此之間的互補”。在本研究中, 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9。
(5)團隊創造力。采用劉玉新等(2013)編制的研究問卷, 共12個題項, 包含團隊知識學習、團隊創意形成、團隊創意實施、團隊創意產生4個維度, 如“我們團隊能產生大量新穎、獨特的創意”。在本研究中, 該量表的總Cronbach’s α系數為0.94, 各分維度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9、0.76、0.84和0.86。
(6)控制變量。本研究對人口統計學變量和理論模型相關的變量進行了控制, 以排除其對研究變量關系的潛在影響。首先, 研究表明團隊高校背景、團隊性別構成(Bodla et al., 2018)以及團隊規模(Hülsheger et al., 2009)均可能對團隊創造力產生影響, 由此本研究選取團隊高校背景(團隊所在高校的類別)、團隊性別構成及團隊規模作為控制變量。此外, 還對與理論模型相關的變量加以控制。研究對與教師辯證反饋密切相關的變量, 即團隊與指導教師的接觸頻率及教師對團隊的反饋頻率進行了控制, 采用如下兩個條目對上述變量進行了考察: “您所在團隊和指導老師接觸的頻率”, “指導老師對團隊表現進行反饋的頻率”, 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方式, “1~5”分別表示“從來沒有~總是”。
2.1.3 統計方法
研究采用Amos 24.0、SPSS 27.0和Process宏程序進行統計分析。首先, 采用Amos 24.0和SPSS 27.0對所有變量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以評估本研究的變量間的區分效度、收斂效度和同源方法偏差。其次, 使用SPSS 27.0進行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最后, 運用SPSS 27.0和Process宏程序對數據進行分層回歸分析, 對間接模型及有條件的間接模型進行假設檢驗。
2.2 研究結果
2.2.1 效度分析與共同方法偏差
區分效度檢驗。采用Amos 24.0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 以考察各主要變量間的區分效度。本研究比較了理論模型(教師辯證反饋、精熟氛圍、績效氛圍、團隊信息深加工和團隊創造力)與其它4個競爭模型的擬合效果。結果發現, 理論模型各項指標擬合良好(χ2= 3.35, SRMR = 0.09, RMSEA = 0.08, CFI = 0.84, TLI = 0.83), 且明顯優于其它競爭模型(見表1), 表明本研究核心構念內涵明晰, 且各構念間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研究采用自我報告方法進行大學生團隊數據收集, 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問題。由此, 本研究從程序設計和統計檢驗兩個方面對數據進行了控制, 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對研究結果的影響。首先, 在問卷設計過程中采用匿名填寫、插入互斥題目、隨機編排題目、將易受社會稱許性影響的條目以具體的認知與行為進行表征等; 在問卷施測過程中, 向作答者說明該問卷的保密性和僅用于學術研究的目的, 以確保數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其次, 在統計檢驗方面, 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和“Harman單因子檢驗”。第一, 對問卷所有核心變量的條目進行主成分因子分析, 共萃取出5個因子, 累計解釋總變異量為78.7%, 最大特征根解釋方差占總方差解釋量的17.2%, 遠小于40%的合格標準。第二, Harman單因子檢驗結果顯示, 單因子模型中各擬合指數均較差(χ2/= 6.98, SRMR = 0.14, RMSEA = 0.14, CFI = 0.51, TLI = 0.48)。綜合上述, 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2.2.2 團隊數據聚合分析
由于個體數據是嵌套在團隊中的, 由此需將個體層面數據聚合到團隊層面, 并檢驗數據聚合合理性。根據Bliese (2000)的建議, 采用2個指標檢驗各變量聚合的可靠性, 即組內一致性系數wg和組內相關系數ICC (1)和ICC (2)。結果顯示, 教師辯證反饋、精熟氛圍、績效氛圍、團隊信息深加工、團隊創造力5個變量的wg中位數分別為0.98、0.92、0.96、0.94和0.98, 均高于0.7的評價標準; 上述5個變量的ICC (1)值分別為0.68、0.51、0.35、0.38和0.51, 均高于0.12的經驗標準; ICC (2)值分別為0.89、0.78、0.68、0.71和0.80, 均高于0.4的經驗標準。由此可以判斷, 本研究所有變量在團隊層面聚合合理可行。

表1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
注:= 78; DF代表教師辯證反饋, MC代表精熟氛圍, PC代表績效氛圍, TIE代表團隊信息深加工, TC代表團隊創造力。
2.2.3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各變量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矩陣如表2所示。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創造力顯著正相關(= 0.69,< 0.01), 與團隊信息深加工顯著正相關(= 0.63,< 0.01); 團隊信息深加工與團隊創造力顯著正相關(= 0.82,< 0.01)。數據結果初步支持了研究假設。
2.2.4 假設檢驗
采用層次回歸分析和Hayes開發的Process宏程序中的Bootstrap法對假設進行檢驗。將團隊高校背景、團隊性別構成、團隊規模、教師接觸頻率和教師反饋頻率作為控制變量, 各統計分析均對上述變量進行了控制, 下文將不再贅述。在假設檢驗前, 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問題, 對自變量和調節變量即教師辯證反饋、精熟動機氛圍和績效動機氛圍進行了中心化處理。
假設1提出, 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創造力間呈正向關系。如表3模型1所示, 教師辯證反饋能夠顯著正向影響團隊創造力(β= 0.64,< 0.001), 該結果支持了假設1。
假設2預測, 團隊信息深加工在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創造力關系間起中介作用。由表3模型2、3可見, 教師辯證反饋顯著正向影響團隊信息深加工(β= 0.61,< 0.001), 將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信息深加工共同納入回歸方程時, 團隊信息深加工對團隊創造力正向影響顯著(β= 0.61,< 0.001), 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回歸系數值雖略有降低但仍顯著(β = 0.27,= 0.007)。由此說明, 團隊信息深加工部分中介了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創造力的關系, 假設2得到支持。
根據Hayes (2013)的建議, 采用偏差校正非參數百分位Bootstrap法進一步對假設2進行檢驗, 設定重復抽樣次數為5000, 置信區間水平為95%, 若置信區間不包含0, 則間接效應顯著。結果顯示, 教師辯證反饋通過團隊信息深加工影響團隊創造力的間接效應為0.37, 標準誤為0.10, 95%置信區間為[0.20, 0.60], 不包含0, 該結果再次支持了假設2。
假設3提出, 精熟氛圍正向調節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信息深加工的關系, 當精熟氛圍水平較高時, 二者間的正相關關系更強。由表3模型4可見, 教師辯證反饋與精熟氛圍的交互項顯著正向預測團隊信息深加工(β= 0.42,< 0.001), 假設3得到支持。為了更精確地解釋精熟氛圍的調節效應, 繪制了調節效應圖(見圖2)。當精熟氛圍水平較高時(+1), 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創造力顯著正相關(simple slope高 = 0.75,= 6.80,< 0.001); 當精熟氛圍水平較低時(?1), 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信息深加工正相關不顯著(simple slope低 = 0.15,= 1.76,= 0.084), 該結果進一步支持了假設3。
假設4預測, 績效氛圍負向調節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信息深加工的關系, 當績效氛圍水平較高時, 二者間的正相關關系更弱。由表3模型5可見, 教師辯證反饋與績效氛圍的交互項顯著負向預測團隊信息深加工(β = ?0.27,= 0.005), 假設4得到支持。為了更精確地解釋績效氛圍的調節效應, 繪制了調節效應圖(見圖3)。當績效氛圍水平較高時(+1), 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信息深加工正相關不顯著(simple slope高 = 0.28,= 1.82,= 0.07); 當績效氛圍水平較低時(?1), 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信息深加工顯著正相關(simple slope低 = 0.48,= 5.49,< 0.001), 該結果進一步支持了假設4。

表2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結果
注:= 78;*表示< 0.05,**表示< 0.01。

表3 層次回歸分析結果(研究1)
注:= 78;*表示< 0.05,**表示< 0.01,***表示< 0.001, 表中報告數據均為標準化回歸系數。

圖2 研究1: 教師辯證反饋與精熟氛圍交互影響團隊信息深加工

圖3 研究1: 教師辯證反饋與績效氛圍交互影響團隊信息深加工
假設5提出, 精熟氛圍和績效氛圍調節了教師辯證反饋通過團隊信息深加工影響團隊創造力的間接效應, 即精熟氛圍水平高、績效氛圍水平低時, 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間接促進作用最強。采用Edwards和Lambert (2007)調節路徑分析技術進行分析(結果見表4), 該方法能更加準確反映變量間關系的調節和中介性質。當精熟氛圍強(+1), 績效氛圍弱時(–1), 間接效應值最大(間接效應 = 0.93,= 0.21, 95% CI = 0.55, 1.35), 該結果支持了假設5。

表4 有條件的間接效應檢驗結果 (研究1)
研究1通過對參加比賽的科技創新團隊進行問卷調研的方式對本研究的理論模型進行了檢驗, 但有學者認為問卷研究難以驗證變量間的因果關系, 且團隊創造力易受到無關因素的干擾, 加之本研究采用自評方式對團隊創造力進行測量, 由此可能帶來共同方法偏差等問題(Podsakoff et al., 2003)。為了進一步提升研究的內部效度及減少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將通過研究2縱向現場實驗研究對理論模型進行檢驗, 從而提高研究的內部效度和生態效度。
3 研究2: 縱向現場實驗研究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試與研究設計
采用單因素(高教師辯證反饋vs. 低教師辯證反饋)組間縱向現場實驗設計檢驗研究假設。該實驗持續12個周, 被試在第3、6、9周受到共3次實驗干預, 在第3、6、9、12周分別提交實驗任務, 在第1、4、7、10周接受問卷調查。數據收集包含兩個方面, 一是主試根據被試提交的實驗任務, 對其團隊創造力進行評分; 二是通過問卷調研從被試處獲取其他變量(教師辯證反饋、團隊信息深加工及動機氛圍等)數據。
來自北京某財經高校117名本科生(均來自某心理學公共課班級), 其中男性占29.9%, 女性占70.1%; 年齡小于等于20歲的占45.3%, 21至25歲的占54.7%; 理科占17.1%, 工科占0.9%, 人文社科占68.3%, 其它學科占13.7%。所有被試隨機組成團隊(每個團隊3人), 并將所有團隊隨機分配到兩個實驗條件(高辯證反饋條件19個團隊, 57人; 低辯證反饋條件20個團隊, 60人)中的一種。作為回報, 被試做完實驗后將獲得課程學分。
3.1.2 實驗任務
參照Hu和Adey (2002)有關科學創造力的測量方法, 并基于Wallas (1926)提出的創新過程四階段模型(準備、醞釀、啟發、驗證)及對大學生科技創新團隊的訪談結果, 設計了包含4項任務(每個任務為期兩周)的團隊科學創新作品設計項目, 通過讓學生協作完成為期近3個月的紙橋搭建任務來測量團隊創造力。該項目的主要目標為, 團隊運用紙張材料設計并搭建出創意新穎且性能良好的橋梁。該項目含如下4項任務: 任務1, 紙橋模型預想。即團隊對紙橋的功能、實現方法和創意等進行預想和描述, 并提交一份報告, 包含設計目的、設計思路、設計創意和紙橋制作科學原理等部分; 任務2, 紙橋設計方案。即團隊對紙橋的具體設計進行描繪與解釋, 并提交一份報告, 包含設計圖和設計圖解釋等部分; 任務3, 紙橋基本模型。即團隊制作紙橋初始模型, 并提交一份報告, 包含作品名稱及寓意、設計性能、實物展示及解釋(對實物拍攝照片, 并拍攝3分鐘視頻講解)等部分; 任務4, 紙橋最終模型。即團隊對紙橋模型進行最終修改與完善, 并提交一份報告, 包含作品簡介、設計性能及創意、實物展示及解釋(對實物拍攝照片, 并拍攝3分鐘講解視頻)等部分。
3.1.3 實驗程序
本研究為期近3個月, 在4個時間點進行數據收集(如圖4所示)。具體而言, 在時間點1 (第1周), 主試介紹實驗任務, 被試填寫前測問卷。主試向被試講解實驗流程、主要目標、具體要求和4項主要任務, 同時給被試布置任務1, 要求被試在兩周后提交任務1; 被試填寫前測問卷, 主要包含基本人口學信息、控制變量。兩周后, 各團隊提交任務1。在時間點2 (第4周), 各團隊提交任務1的一周后, 主試對各團隊任務完成情況進行高/低辯證反饋并布置任務2, 被試填寫問卷, 主要包含辯證反饋操縱檢驗。兩周后, 各團隊提交任務2。在時間點3 (第7周), 各團隊提交任務2的一周后, 主試對各團隊任務完成情況進行高/低辯證反饋并布置任務3, 被試填寫問卷, 主要包含辯證反饋操縱檢驗、精熟氛圍與績效氛圍問卷。兩周后, 各團隊提交任務3。在時間點4 (第10周), 各團隊提交任務3的一周后, 主試對各團隊任務完成情況進行高/低辯證反饋并布置任務4, 被試填寫問卷, 主要包含辯證反饋操縱檢驗和團隊信息深加工問卷。兩周后, 各團隊提交任務4。
3.1.4 實驗操縱
本研究參照Harrison和Dossinger (2017)、Hoever等(2018)以及Kim和Kim (2020)等人有關反饋的實驗操縱方法, 同時基于辯證反饋的概念內涵及其兩個核心維度(發展性與全面性)編制而成。主試根據團隊前三個任務(紙橋設計預想、紙橋設計方案、紙橋基本模型)的表現, 從多方面(如設計目的、設計思路、設計創意和制作原理等)對團隊進行反饋。在高辯證反饋條件下的團隊, 分別接受三次高辯證反饋干預, 即每次針對團隊表現的反饋內容均是辯證反饋; 在低辯證反饋條件下的團隊, 分別接受三次低辯證反饋干預, 即每次針對團隊表現的反饋僅有少于一半的內容屬于辯證反饋。下面以任務1為例作一說明。
在高辯證反饋條件中, 教師會從設計目的、設計思路、設計創意和制作原理四個方面對團隊表現進行評價, 且上述評價均屬于辯證反饋, 體現了辯證反饋中全面性和發展性等要素。茲舉例如下: 其一, 設計目的方面, 你們組認真理解了任務要求, 并根據要求規劃出相應的目標, 遵循循序漸進原則, 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很好地將任務要求與過程進展進行了結合, 希望你們能夠根據要求進一步規劃出具體可行又富有創意的目標。其二, 設計思路方面, 結合相關知識, 對紙橋的承重結構及橋面進行了科學的初步設計。但紙橋的具體構造仍較為模糊,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對紙橋設計進行完善, 在設計過程中豐富自己的知識面, 提高自身的思維能力。其三, 設計創意方面, 設計較為新穎, 尤其是“兩側的拉索在形狀上酷似鳥的羽翼”, 該設計具有一定的創新性。但不對稱結構的穩定性仍值得商榷, 大家需在兼顧創新性的同時, 注重方案的可行性。希望你們在下一步的設計中能夠有所突破, 如結合各自的專業特色或感興趣的事物, 設計出富有創意且牢固的紙橋。其四, 制作原理方面, 該部分較好地將紙橋的制作原理進行了闡述。希望你們能夠多學習紙橋構建相關知識, 甚至也可以將看似不相關領域中的知識進行遷移, 設計出富有創意的紙橋。

圖4 縱向現場實驗流程圖
注: F為反饋(Feedback),S為問卷測查(Survey)。
在低辯證反饋條件中, 教師仍從設計目的、設計思路、設計創意和制作原理四個方面對團隊表現進行評價, 僅有一個或兩個方面的評價屬于辯證反饋。在下面例子中, 只有關于設計思路和設計創意的評價屬于辯證反饋, 體現了全面性和發展性等特征。其一設計目的方面, 你們組認真理解了任務要求, 并根據要求規劃出相應的目標, 兼具了承重性和美觀性。其二, 設計思路方面, 結合相關知識, 對紙橋的承重結構進行了科學的初步設計, 但紙橋的具體構造仍較模糊。其三, 設計創意方面, 你們的設計考慮了承重和穩定性, 但缺乏創意。其四, 制作原理方面, 可以看出大家認真查閱并學習了與該任務相關的知識, 對這些知識進行了加工與整合, 較好地將紙橋的制作原理進行了闡述。
3.1.5 變量測量
(1)操縱檢驗工具。本研究采用與研究1相同的9條目問卷對被試所感知到的教師辯證反饋水平進行測量。在本研究的三次問卷測查(S2、S3、S4)中, 該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94、0.90、0.91, 組內一致性系數wg中位數分別為0.97、0.96、0.95, 組內相關系數ICC (1)分別為0.30、0.27、0.26, ICC (2)分別為0.55、0.57、0.59, 上述wg值、ICC (1)值和ICC (2)值分別大于0.7、0.12和0.4的標準, 表明把個體層面數據聚合為團隊層面數據是合理可行的。采用三次教師辯證反饋測量均值作為該變量的最終數值。
(2)動機氛圍。采用Nerstad等(2013)開發的動機氛圍量表, 包含精熟氛圍6個條目(如“在我們團隊, 鼓勵成員之間合作并相互交換想法”)和績效氛圍8個條目(如“在我們團隊, 成員之間的競爭是被鼓勵的”), 精熟氛圍和績效氛圍維度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9和0.60,wg中位數值分別為0.95和0.97, ICC (1)值分別為0.49和0.35, ICC (2)值分別為0.74和0.62。
(3)團隊信息深加工。采用Kearney等(2009)開發的團隊信息深加工問卷, 共4個題項, 如“我們團隊的成員通過公開分享自己的知識來實現彼此之間的互補”。在本研究中, 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1,wg中位數值為0.95, ICC (1)和ICC (2)值分別為0.25和0.49。
(4)團隊創造力。在團隊每次任務完成后, 由三位經過培訓、不了解實驗條件和研究假設的博士研究生對團隊創造力進行評價, 其中任務1評價分數反映了干預前團隊創造力水平, 任務2~4評價分數反映了干預后團隊創造力水平。基于O’Quin和Besemer (2006)的創造性產品分析矩陣與Hu和Adey (2002)的創造力結構, 本研究采用新穎性、解決度、精細與綜合性、科學性4個維度共計11個題項作為團隊創造力的整體指標, 示例題項如“該作品的新奇性”。三位評分者采用Likert 7點計分方式對每個團隊的創新作品進行獨立評價, “1~7”分別表示“非常低~非常高”, 團隊創造力最終得分為三人評分的平均值。評分者一致性系數wg中位數值分別為0.94, 組內相關系數ICC (1)為0.71, ICC (2)為0.88, 評分者內部一致性和信度良好, 表明評分者之間評分聚合的合理性(James et al., 1984)。將任務2、3、4的團隊創造力得分均值作為該變量干預后的分值。
(5)控制變量。基于本研究中創新作品設計項目的特點, 對性別、年級、專業、動手操作能力和相關經驗(Yates & Twigg, 2017)進行了控制, 其中動手操作能力和相關經驗的測量條目分別為“您的動手操作能力如何”和“您之前做過和紙橋相似的模型嗎”, 采用Likert 5點計分方式, “1~5”分別表示“完全沒有~經常”。
3.2 實驗結果
3.2.1 操縱檢驗
操縱檢驗。采用獨立樣本檢驗對兩組實驗條件下(高辯證反饋vs. 低辯證反饋)的教師辯證反饋結果進行分析。結果顯示, 高辯證反饋條件下, 被試在第1、2、3次報告的教師辯證反饋表現值(= 4.32,= 0.32;= 4.14,= 0.26;= 4.14,= 0.29)均顯著高于低辯證反饋條件下表現值[= 3.64,= 0.38,(37) = 6.03,< 0.001, Cohen’s= 1.94;= 3.42,= 0.31,(37) = 7.87,< 0.001, Cohen’s= 2.52;= 3.49,= 0.40,(37) = 5.79,< 0.001, Cohen’s= 1.86]。該結果表明, 該實驗對教師辯證反饋操縱有效。
3.2.2 假設檢驗
假設1提出, 教師辯證反饋能夠正向預測團隊創造力。采用協方差分析、獨立樣本檢驗和單因素方差分析法, 分析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作用效果。
首先, 分析干預前(任務1)的團隊創造力是否會對干預后團隊創造力產生影響, 以排除團隊創造力基準水平對實驗結果的影響。一方面, 通過獨立樣本檢驗發現, 干預前(任務1), 兩組實驗條件下(高辯證反饋 vs. 低辯證反饋)團隊創造力得分差異不顯著[(37) = ?0.35,= 0.075]。另一方面, 協方差分析結果顯示, 干預前的團隊創造力對干預后(任務2、3、4)的團隊創造力水平均不存在顯著影響[(1, 36) = 0.65,= 0.818, ?2= 0.37;(1, 36) = 1.35,= 0.259, ?2= 0.55;(1, 36) = 1.21,= 0.339, ?2= 0.34]。據此, 可排除團隊基準創造力對實驗結果的影響。
其次, 采用獨立樣本檢驗分析干預后高辯證反饋條件和低辯證反饋條件下團隊創造力差異。結果顯示, 在任務2、3、4中高辯證反饋條件下團隊創造力水平均顯著高于低辯證反饋條件[高= 5.15 (= 0.39),低= 4.34 (= 0.68),(37) = 4.56,< 0.001, Cohen’s= 1.46;高= 5.49 (= 0.56),低= 4.34 (= 0.52),(37) = 6.70,< 0.001, Cohen’s= 2.13;高= 5.59 (= 0.56),低= 4.38 (= 0.40),(37) = 7.77,< 0.001, Cohen’s= 2.49]。
最后, 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中的Tukey HSD法, 對兩種實驗條件下任務1至任務4的團隊創造力變化狀況進行分析, 見圖5。在高辯證反饋條件下, 分析結果顯示任務4的團隊創造力稍高于任務3的團隊創造力但差異不顯著(= 0.921), 顯著高于任務2的團隊創造力(= 0.029), 也顯著高于任務1的團隊創造力(< 0.001); 任務3與任務2的團隊創造力差異不顯著(= 0.129), 但顯著高于任務1的團隊創造力(< 0.001); 任務2的團隊創造力顯著高于任務1的團隊創造力(< 0.001)。在低辯證反饋條件下, 任務1、任務2、任務3和任務4中的團隊創造力間不存在顯著差異(> 0.05)。上述結果表明, 在高教師辯證反饋條件下, 不同任務間團隊創造力會出現顯著差異, 而在低辯證反饋條件下, 不同任務間團隊創造力差異不顯著。

圖5 不同任務下高辯證反饋與低辯證反饋條件組團隊創造力水平
綜合上述結果, 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1得到支持。
對假設2至假設5進行檢驗, 結果顯示: 教師辯證反饋通過團隊信息深加工影響團隊創造力的間接效應為0.12, 標準誤為0.05, 95%置信區間為[0.01, 0.37], 不包含0, 該結果支持了假設2; 教師辯證反饋與精熟氛圍的交互項顯著正向預測團隊信息深加工(= 0.93,= 0.34,= 2.75,= 0.009), 假設3得到支持; 教師辯證反饋與績效氛圍的交互項對團隊信息深加工的負向相關關系不顯著(= –0.80,= 0.68,= –1.17,= 0.482), 假設4未得到支持; 調節路徑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 當精熟氛圍水平高(+1), 績效氛圍水平低時(–1), 間接效應值最大(間接效應 = 0.36,= 0.19, 95% CI = 0.06, 0.83), 該結果支持了假設5。

表5 有條件的間接效應檢驗結果(研究2)
4 總體討論
教師辯證反饋作為一套蘊涵豐富、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學策略和育才藝術, 對促進大學生團隊創造力發展具有重要價值。本文基于社會信息加工理論視角, 探討了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作用路徑(以團隊信息深加工為中介變量)和邊界條件(以動機氛圍為調節變量)。研究1通過實地問卷調查發現, 教師辯證反饋能夠顯著正向預測團隊創造力, 團隊信息深加工在二者間起中介作用, 上述過程還受到團隊動機氛圍的調節作用。研究2通過縱向現場實驗研究支持了研究1的主要假設, 顯著提升了本研究理論模型的解釋力。
4.1 理論貢獻
首先, 深化了已有反饋理論研究, 拓展了“教育與發展”理論范疇。一方面, 提出并界定教師辯證反饋的理論內涵及其作用結果是對已有反饋理論的深化拓展。已有學者指出, 反饋既要使創造性工作者明晰當前問題“困境”, 又要啟迪其探尋“出路”, 并發現事物間的新關聯(Hargadon & Bechky, 2006; Harrison & Rouse, 2015)。然而, 以往反饋概念內涵難以同時包含上述指導性意義, 教師辯證反饋則從理論層面上彌補了已有反饋界定不足, 其蘊含的辯證性與發展性思想有助于促進團隊創造力發展, 進一步深入探究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作用機理并同時拓展了反饋理論空間。另一方面, 教育與發展關系是發展與教育心理學領域的經典理論范疇。維果茨基的最近發展區理論指出, 教學要引領學生發展, 教師要注重挖掘學生潛能并幫助其實現由實際發展水平到潛在發展水平的躍遷(Vygotsky, 1980)。據此, 教師辯證反饋恰能體現發展性視域和辯證性思維, 既能評價學生現有能力素質水平, 又能指出學生潛在發展空間, 還能指導學生運用辯證思維和方法實現自我突破。我國學者在闡述教育與發展關系時指出, 教師要求只有高于學生原有水平并經過學生主觀努力后能夠達到, 才是最合適的教學要求(朱智賢, 林崇德, 2002), 這一觀點指明了實現“最近發展區”目標的明確路徑。教師辯證反饋能夠根據學生自身發展特點與狀態, “因材施教”地對學生提出發展性目標和差異化要求, 從而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和持續成長。加之,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演進, 科技創新的復雜性和挑戰性對團隊協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團隊創造力的重要意義愈加凸顯(Aggarwal & Woolley, 2019)。教師辯證反饋一方面能夠促使學生從更加多元、對立、整體、聯系和發展的視角進行前沿探索和問題解決, 有助于提升創造力的質量水平, 另一方面又十分關注學生內在成長和能力素質提升而非社會比較與競爭, 有助于增進團隊協作效率和效果。由此, 本研究從創新教育入手, 揭示了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積極影響, 從團隊科技創新層面上豐富和深化了教育與發展關系范疇, 并開拓了教師辯證反饋的后效研究。
其次, 豐富了創造力理論研究, 拓展了團隊創造力前因。隨著信息技術背景下科技與教育和產業的耦合發展水平不斷提升, 科學創造周期縮短且科技創新迭代加速, 團隊協同優勢和團隊創造力的研究價值愈加凸顯(張建衛等, 2017)。大學生是建設創新型國家和科技強國的生力軍, 其團隊創造力是推動國家科技創新發展的重要動力。然而梳理創造力研究軌跡可發現, 或是基于個體水平探討一般性創造力(Guilford, 1950; 林崇德等, 2009; Sternberg, 1985; 吳湘繁等, 2022), 或是基于團隊水平探討組織創造力(王端旭, 薛會娟, 2011; Woodman et al., 1993), 鮮有探討教育情境中的團隊創造力發展研究(James & Drown, 2012)。本研究基于高校科技創新教育情境, 探究了大學生團隊創造力的形成機制, 促進了高等教育情境下團隊創造力的理論構建。此外, 已有學者呼吁應考察外部環境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 以找尋激發團隊創造力的有效路徑(Zhao et al., 2021)。本研究探討了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及作用機制, 既從團隊水平和教育教學層面上拓展了創造力理論研究, 又揭示了外部環境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 回應了已有學者的研究呼吁, 豐富了團隊創造力前因研究。
此外, 基于社會信息加工理論, 從團隊信息處理視角提出了團隊信息深加工這一中介機制, 有助于揭示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創造力之間的理論“灰箱”。以往有關反饋與團隊創造力關系的文獻, 鮮見對二者間的過程機制進行考察。團隊信息處理過程對團隊創造力至關重要(Hülsheger et al., 2009), 本研究發現教師辯證反饋能夠增進團隊信息深加工, 促使團隊成員對不同信息與觀點進行交流討論, 提升團隊信息的搜索、討論、加工與整合水平(Cacioppo et al., 1996), 進而推動團隊創造力發展。本研究揭示了團隊信息深加工在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創造力之間的中介作用, 這一發現不僅從團隊層面上拓展深化了個體層面上“知識領會是教育和發展之間的中間環節” (林崇德, 2013)這一理論命題, 而且回應了Hoever等(2018)關于開展真實情境下團隊信息深加工與團隊創造力關系的呼吁。加之, 本研究除了表明教師辯證反饋通過團隊信息深加工對團隊創造力產生作用之外, 還揭示教師辯證反饋與動機氛圍等環境因素的交互作用能夠通過團隊層面因素傳導于團隊創造力上, 該結果為未來探究教師辯證反饋與其他環境因素交互作用于團隊創造力的復雜機制提供了理論啟示。
最后, 本研究還在社會信息加工理論框架下探索了團隊動機氛圍的調節效應, 揭示了教師辯證反饋影響團隊創造力的邊界條件。研究表明, 精熟氛圍能夠正向調節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信息深加工的影響, 而績效氛圍則負向調節二者間關系, 并且精熟氛圍與績效氛圍的調節作用會通過團隊信息深加工影響團隊創造力。雖然在實驗研究中績效氛圍在教師辯證反饋與團隊信息深加工關系間的負向調節作用并未得到支持, 但在真實情境下的問卷研究結果支持了上述調節作用, 這可能是由于實驗研究未能涉及社會比較、人際競爭等情境意涵, 各團隊內部的績效氛圍水平相對較低, 使該因素難以發揮其調節作用。本研究通過對不同動機氛圍調節作用及聯合調節效應的考察, 揭示了教師辯證反饋影響團隊創造力過程的邊界條件, 驗證了精熟氛圍和績效氛圍的調節效應, 即高精熟氛圍和低績效氛圍條件下, 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間接促進作用更顯著, 這一研究結果與Buch等(2017)的研究發現相一致。通過探究不同環境因素間的共同作用豐富了社會信息加工理論體系, 并拓深了社會信息加工理論在高等教育學尤其是創新教育領域的應用空間。
4.3 實踐啟示
本研究對高校創新教育及教師日常教育教學活動具有多方面實踐啟示。首先, 增強教師辯證反饋。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和實驗研究交叉驗證發現, 教師辯證反饋對大學生團隊創造力具有積極影響。一方面, 教師要注重提升自身辯證思維水平。辯證思維是教師在教育教學活動中展現的重要思維能力, 不僅能夠引領教師展開更豐富的辯證反饋, 還會對學生創造力起到促進作用(Paletz et al., 2018)。教師可通過參與辯證思維培訓、反饋尋求、研討交流、元認知訓練等方式, 不斷提升辯證反饋意識、能力和藝術。另一方面, 教師要樹立“以學生為中心”的價值理念。面對紛繁復雜的創新情境和學生間個體差異, 教師要全面理解和把握學生發展特征及團隊創新規律, 善于運用“反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矛盾原理, 推動實現學生發展核心素養的普遍性與獨特性相結合、對立性與統一性相轉化。
其次, 提升團隊信息深加工水平。本研究發現, 團隊信息深加工不僅能夠中介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作用效應, 也能傳導教師辯證反饋與動機氛圍對團隊創造力的交互效應。為此, 在教師層面上, 需注重增進大學生團隊信息深加工。教師可通過激發團隊認知需求, 引導成員主動探索科技創新前沿, 對科學問題進行辯證性和系統性思考, 培養團隊對任務和環境信息的搜索、思考和整合能力(Huang & Liu, 2021)。在學生層面上, 需注重強化團隊內部信息與觀點的共享與交流, 提高專業和人際熟悉度。具體而言, 當團隊成員熟悉他人的工作和專業知識(即專業熟悉度)時, 更有可能聆聽和思考他人的觀點; 當團隊成員對彼此情形更為了解(即人際熟悉度)時, 則可能避免在觀點沖突時產生敵對情緒和敵意歸因, 上述兩種熟悉度均能提升團隊信息深加工水平(Maynard et al., 2019)。
最后, 營造團隊精熟氛圍, 弱化團隊績效氛圍。研究發現, 精熟氛圍能夠增強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積極影響, 而績效氛圍則會削弱這一積極作用, 而且這兩種動機氛圍能夠同時發揮作用, 即精熟氛圍水平高而績效氛圍水平低時, 會顯著增強教師辯證反饋的積極作用。故此, 對于教師或團隊領導而言, 一方面要著力營造團隊精熟氛圍, 鼓勵成員開展合作與知識共享, 為團隊樹立學習目標導向, 促進團隊成員追求內在成長和能力提升; 另一方面, 要注意弱化團隊績效氛圍, 在反饋交流中弱化成員間社會比較, 降低團隊內部競爭損耗水平, 當發現團隊存在不良競爭、互相攀比現象時, 應及時進行正向引導, 促使團隊成員彼此融合、互學共進。
4.3 研究局限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不足尚待進一步完善。其一, 在研究模型方面, 中介路徑與調節機制仍有待探究。本文從團隊信息加工角度出發, 僅考察了團隊信息深加工的中介作用。然而, 外界環境對學習者的影響不僅涉及信息加工因素, 還包含了能力、情緒情感、動機等因素, 如已有研究發現內部動機與領域內相關技能(Thanh & Thuan, 2019)均能在反饋和創造力間起中介作用。此外, 本研究基于社會信息加工理論, 主要考察了動機氛圍這一調節因素, 但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作用可能還會受團隊自身因素如目標導向(He et al., 2016)、團隊凝聚力(Joo et al., 2012)及關系認同(徐珺等, 2018)等影響, 未來研究可對上述因素作用進行探究, 以豐富教師辯證反饋的作用路徑。
其二, 在研究設計上仍有待完善。一方面, 現實情境中, 團隊的信息深加工水平和教師辯證反饋程度可能存在雙向影響。因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究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及作用機制, 此時團隊信息深加工在二者關系間起重要的傳導作用, 故而未對信息加工偏好等團隊特征對教師辯證反饋水平的影響進行探究, 未來可深入探討團隊特征對教師辯證反饋水平的影響。另一方面, 在縱向現場實驗設計中, 研究2采用單因素實驗設計, 雖然對調節變量(動機氛圍)進行了問卷測量, 但仍存在一定不足。研究2采用實驗研究對理論模型進行檢驗, 并通過對教師辯證反饋的多次操縱, 考察了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然而, 因該實驗是在真實教學環境中開展, 誘發績效氛圍有悖教育原則, 故未對動機氛圍進行操縱, 可能難以深入反映動機氛圍變化對結果變量的影響。未來研究可通過實驗室實驗等方法對動機氛圍進行操縱, 以探究其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
其三, 在研究方法層面, 本研究雖然采用綜合性研究方法(問卷研究與實驗研究相結合)以確保研究的內外效度, 但仍存在一定局限。就研究1而言, 由于該研究對象為參加比賽的大學生科技創新團隊, 受條件所限, 難以采用多時點方式進行變量測量, 雖然本研究進行了程序性控制和統計分析, 但仍有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未來可采用多時點測量方式提升數據精度。此外, 由于團隊信息深加工與團隊創造力存在概念內涵交疊, 即團隊創造力中的知識學習維度涉及團隊內部知識和技術的分享、交流與整合, 這與團隊信息深加工所反映的團隊內部信息處理過程存在一定程度的重疊, 致使研究1中二者相關系數較高。未來研究可以選擇其它測量工具對本研究的理論模型進行驗證。在研究2中, 雖然在12個周內追蹤了4次團隊創造力變化狀況, 研究結果能夠反映出短期內團隊導向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情況, 但因追蹤時程較短, 難以揭示教師辯證反饋的長時距動態作用軌跡, 未來可進行更長尺度的追蹤研究, 以細致刻畫教師辯證反饋對團隊創造力的動態影響。
致謝: 衷心感謝兩位匿名評審專家的專業指導和寶貴建議; 同時感謝鄭文峰、付萌萌、姜蘊珊、楊文亞、冷鈺冰、王洛賓和劉入瑗等同學在資料整理方面提供的幫助。
Aggarwal, I., & Woolley, A. W. (2019). Team creativity, cognition, and cognitive style diversity.,(4), 1586?1599.
Ali, A., Wang, H., & Boekhorst, J. A. (2023). A moderated mediation examination of shared leadership and team creativity: A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erspective.,(1), 295?327.
Amabile, T. (2012)..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Bledow, R., Frese, M., Anderson, N., Erez, M., & Farr, J. (2009). A dialectic perspective on innovation: Conflicting demands, multiple pathways, and ambidexterity.,(3), 305?337.
Bliese, P. D. (2000). Within-group agreement, non-independence, and reliability: Implications for data aggregation and analysis. In K. J. Klein & S. W. Kozlowski (Eds.),(pp. 349?381).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Bodla, A. A., Tang, N., Jiang, W., & Tian, L. (2018). Diversity and creativity in cross-national teams: The role of team knowledge sharing and inclusive climate.,(5), 711?729.
Boekhorst, J. A. (2015). The role of authentic leadership in fostering workplace inclusion: A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erspective.,(2), 241?264.
Breugst, N., Preller, R., Patzelt, H., & Shepherd, D. A. (2018). Information reliability and team reflection as contingenc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and team decision quality.,(10), 1314?1329.
Buch, R., Nerstad, C. G., & S?fvenbom, R. (2017). The interactive roles of mastery climate and performance climate in predicting intrinsic motivation.,(2), 245?253.
Cacioppo, J. T., Petty, R. E., Feinstein, J. A., & Jarvis, W. B. G. (1996). Dispositional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motivati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individuals varying in need for cognition.,(2), 197?253.
?erne, M., Nerstad, C. G., Dysvik, A., & ?kerlavaj, M. (2014).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Knowledge hiding, perceived motivational climate, and creativity.,(1), 172?192.
Edwards, J. R., & Lambert, L. S. (2007).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 A gene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using moderated path analysis.,(1), 1?22.
Fodor, E. M., & Carver, R. A. (2000). Achievement and power motives, performance feedback, and creativity.,(4), 380?396.
Gong, Y., Kim, T. Y., Lee, D. R., & Zhu, J. (2013). A multilevel model of team goal orientation,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creativity.,(3), 827?851.
Guilford, J. P. (1950). Creativity., 5(9), 444?454.
Han, G., Bai, Y., & Peng, G. (2021). Creating team ambidexterity: The effects of leader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collective team identification.40(2), 175?181.
Hargadon, A. B., & Bechky, B. A. (2006). When collections of creatives become creative collectives: A field study of problem solving at work.,(4), 484?500.
Harrison, S. H., & Dossinger, K. (2017). Pliable guidance: A multilevel model of curiosity, feedback seeking, and feedback giving in creative work.,(6), 2051?2072.
Harrison, S. H., & Rouse, E. D. (2015). An inductive study of feedback interactions over the course of creative projects.,(2), 375?404.
Harvey, S. (2015). When accuracy isn’t everything: The value of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to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in teams.,(1), 35?61.
Hayes, A. F. (2013).. New 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He, Y., Yao, X., Wang, S., & Caughron, J. (2016). Linking failure feedback to individual creativity: The moderation role of goal orientation.,(1), 52?59.
Hoever, I. J., Zhou, J., & van Knippenberg, D. (2018). 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teams: The contingent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dback on the creativity of informationally homogeneous and diverse teams.,(6), 2159?2181.
Hu, W., & Adey, P. (2002). A scientific creativity test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4), 389?403.
Huang, C. Y., & Liu, Y. C. (2021). Influence of need for cognition and psychological safety climate on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and team creativity.,(1), 102?116.
Hülsheger, U. R., Anderson, N., & Salgado, J. F. (2009). Team-level predictors of innovation at work: A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spanning three decades of research.,(5), 1128? 1145.
James, L. R., Demaree, R. G., & Wolf, G. (1984). Estimating within-group interrater reliability with and without response bias.,(1), 85?98.
James, K., & Drown, D. (2012). Organizations and creativity: Trends in research, status of education and practice, agenda for the future. In M. D. Mumford (Ed.)(17?38). Academic Press.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Joo, B. K., Song, J. H., Lim, D. H., & Yoon, S. W. (2012). Team creativity: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learning culture, developmental feedback and team cohesion.,(2), 77?91.
Kearney, E., Gebert, D., & Voelpel, S. C. (2009). When and how diversity benefits teams: The importance of team members’ need for cognition.,(3), 581?598.
Kim, Y. J., & Kim, J. (2020). Does negative feedback benefit (or harm) recipient creativity? The role of the direction of feedback flow.,(2), 584?612.
Koka, A., & Hein, V. (2005).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teacher feedback on intrinsic motiv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2), 91?106.
Kooij-de Bode, H. J., van Knippenberg, D., & van Ginkel, W. P. (2008). Ethnic diversity and distributed information in group decision making: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elaboration.,(4), 307?320.
Li, H., & Lv, L. (2019). Influence of prevention focus and motivational climate on knowledge hiding in enterprises.,(4), 245?255.
[李浩, 呂鸞鸞. (2019). 防御定向, 動機氛圍對企業中知識隱藏的影響.(4), 245?255.]
Lin, C. (2003)..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林崇德. (2013).(p. 95).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Lin, C. (2009)..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林崇德. (2009).. 北京: 經濟科學出版社.]
Liu, Y., Zhang, J., Yang, S., & Ma, B. (2013). Research and cultivation of team scientific creativity amo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ostgraduates., (8), 34?39.
[劉玉新, 張建衛, 楊世榮, 馬奔. (2013). 理工科研究生團隊科學創造力的研究與培養.(8), 34?39.]
Mavri, A., Ioannou, A., & Loizides, F. (2020). Design students meet industry players: Feedback and creativity in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DOI: 10.1016/j.tsc.2020.100684.
Maynard, M. T., Mathieu, J. E., Gilson, L. L., R. Sanchez, D., & Dean, M. D. (2019). Do I really know you and does it matter? Unpac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iarity and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in global virtual teams.,(1), 3?37.
Nerstad, C. G., Roberts, G. C., & Richardsen, A. M. (2013). Achieving success at work: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Motivational Climate at Work Questionnaire (MCWQ).,(11), 2231?2250.
Nerstad, C. G., Searle, R., ?erne, M., Dysvik, A., ?kerlavaj, M., & Scherer, R. (2018). Perceived mastery climate, felt trust, and knowledge sharing.,(4), 429?447.
Nisbett, R. E., Peng, K., Choi, I., & Norenzayan, A. (2001).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2), 291?310.
O’Quin, K., & Besemer, S. P. (2006). Using the creative product semantic scale as a metric for results‐oriented business.,(1), 34?44.
Paletz, S. B., Bogue, K., Miron-Spektor, E., Spencer-Rodgers, J., & Peng, K. (2018).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from many perspectives: Contradiction and tension., 267?308.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Y., & Podsakoff, N. P.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5), 879?903.
Rupert, T. J., & Kern, B. B. (2016).. Bingley: Emerald.
Ryan, R. M. (1982). Control and information in the intrapersonal sphere: An extension of 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3), 450?461.
Salancik, G. R., & Pfeffer, J. (1978). A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to job attitudes and task design.,(2), 224?253.
Smither, J. W., & Walker, A. G. (2004).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rrative comments related to improvement in multirater feedback ratings over time?,(3), 575?581.
Son, S., & Kim, D.Y. (2016). The role of perceived feedback sources’ learning-goal orientation on feedback acceptance and employees’ creativity.,(1), 82?95.
Stasser, G., & Titus, W. (1985). Pooling of unshared information in group decision making: Biased information sampling during discussion.,(6), 1467?1478.
Sternberg, R. J. (1985). 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creativity, and wisdom.,(3), 607?627.
Thanh, B. T., & Thuan, L. C. (2019). Mediating mechanisms linking developmental feedback with employee creativity.,(2), 108?121.
van Knippenberg, D., de Dreu, C. K., & Homan, A. C. (2004). Work group diversity and group performance: An integrative model and research agenda.,(6), 1008?1022.
Vygotsky, L. S. (198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llas, G. (1926).. NY: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Wang, D., & Xue, H. (20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and team creativity.(1), 122?128.
[王端旭, 薛會娟. (2011). 交互記憶系統與團隊創造力關系的實證研究.(1), 122?128.]
Wang, Y., Li, K., Gai, X., & Cao, Y. (2020). Training and transfer effects of response inhibition training with online feedback o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executive function.,(10), 1212?1223.
[王元, 李柯, 蓋笑松, 曹逸飛. (2020). 基于即時反饋的反應抑制訓練對青少年和成人執行功能的訓練效應和遷移效應.,(10), 1212?1223.]
Wang, Y., & Shi, K. (2003). The impact of supervisor’s feedback on workers’ behavior.,(2), 255?260.
[王永麗, 時勘. (2003). 上級反饋對員工行為的影響.(2), 255?260.]
Woodman, R. W., Sawyer, J. E., & Griffin, R. W. (1993). Toward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2), 293?321.
Wu, X., Chen, Y., Yan, R., & Guan, H. (2022). Core self- evaluation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A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self-consistent theory.(9), 243?253.
[吳湘繁, 陳赟, 嚴榮, 關浩光. (2022). 基于自我一致性理論視角的員工創造力產生機制研究.,(9), 243?253.]
Xu, J., Shang, Y., & Song, H. (2018). Supervisor developmental feedback and creativity: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1), 69?78.
[徐珺, 尚玉釩, 宋合義. (2018). 上級發展性反饋與創造力: 一個被調節的中介模型.,(1), 69?78.]
Yates, E., & Twigg, E. (2017). Developing creativity in early childhood studies students.,, 42?57.
Zhang, J., Ren, Y., Zhou, J., & Zhao, H. (2017). The mechanisms of how leader empowering behavior influences undergraduates’ team scientific creativity.,(5), 56?63.
[張建衛, 任永燦, 周潔, 趙輝. (2017). 領導授權行為對大學生團隊科學創造力的作用機制.,(5), 56?63.]
Zhao, H., Zhang, J., Heng, S., & Qi, C. (2021). Team growth mindset and team scientific creativ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role of team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and leader behavioral feedback.,, 100957, DOI: 10.1016/j.tsc.2021.100957.
Zhou, J. (1998). Feedback valence, feedback style, task autonomy, and achievement orientation: Interactive effects on creative performance.,(2), 261?276.
Zhou Y. (2022).(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周愉凡. (2022).(博士學位論文). 北京理工大學.]
Zhu, Z., & Lin, C. (2002).(pp. 471?472).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朱智賢, 林崇德. (2002).(pp. 471?472). 北京: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
How to teach resourcefully? The mechanism of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on team creativity of college students
ZHANG Jianwei1, ZHOU Yufan2, LI Linying3, LI Haihong4, HUA Weijun1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2Normal College,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3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4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reflects teachers’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accord with college students’ development rul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oost students’ team creativity. Less attention, however, has been given to the influence of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on team creativity. Therefore, we expect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on team creativity and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To test our hypotheses, we conducted a field survey and a longitudinal field experimental study. The results overall provided support for our theoretical model and showed that (1)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eam creativity; (2) team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and team creativity; (3)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and mastery climate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eam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such that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and team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was stronger when mastery climate was high rather than low; (4) performance climate also played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and team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such that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and team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was weaker when mastery climate was high rather than low; (5) the indirect effect of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on team creativity through team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by mastery climate and performance climate, such that when mastery climate was higher and performance climate was lower, the positive indirect effect is stronger, and vice versa.
Drawing upon these findings, our work offers multiple contributions. First, this research expands the existing feedback paradigm and theoretical category of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on team creativity. Second, our study enriches the theory of creativity and broadens the antecedents of team creativity by exploring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on team creativity. Third, this work provides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influences team crea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eam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effects of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Finally, by exploring the contingent role of team motivational climate, our study revealed the critical boundary condition for the effect of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on team creativity, which provide a more integrative and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whether and when team performs more or less creativity as results of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teacher dialectical feedback, team creativity, team information elaboration, mastery climate, performance climate
2022-09-08
*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22AZD026);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72074024)。
周愉凡, E-mail: zhouyufan@qdu.edu.cn
B849: G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