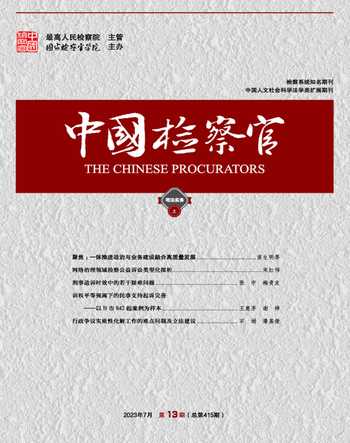論行政公益訴訟訴前程序證明標準
繆淑妮 陶永強
摘 要:實踐中,基于訴前調查規范化、訴前監督精準性及與訴訟程序有效銜接等多方面要求,有必要明確統一的訴前程序證明標準。具體而言,應當在綜合考量檢察權與行政權邊界、檢察機關調查能力現狀、待證事實差異和后續程序證明標準基礎上,明確其證明標準,具體如下:在整體上將訴前程序證明標準明確為優勢證據標準;以待證事實為基礎,將公益受損明確為高度蓋然性標準、行政機關監督管理職責及因果關系明確為排除合理懷疑標準、行政機關作為違法明確為高度蓋然性標準、行政機關不作為違法明確為優勢證據標準。
關鍵詞:訴前程序 證明標準 待證事實 訴前調查
與訴訟程序相比,行政公益訴訟訴前程序(以下簡稱“訴前程序”)具有獨立性,且為司法實踐主流樣態。但如何把握其證明標準,司法實踐中有不同認識,有必要進行專門探討。
一、明確訴前程序證明標準之必要性
(一)訴前調查規范化的要求
根據《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規則》(以下簡稱《辦案規則》)第71條,在訴前程序中,檢察機關需要圍繞“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實、行政機關的監督管理職責、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行為、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行為與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關聯性”開展訴前調查。在不同證明標準指引下,所要調查內容、方式等存在較大差異,對訴前程序證明標準進行明確,可以確保訴前調查的統一規范。
(二)訴前監督精準性的要求
在訴前程序中,需要突出監督的精準性,否則,便無法有效維護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此外,訴前程序實現精準監督,可以實現“通過訴前程序實現維護公益目的”最佳司法狀態。司法實踐中,訴前監督的精準性離不開訴前調查,而訴前調查則以證明標準為指引。由此,明確訴前程序證明標準,有助于提升監督精準性。
(三)與訴訟程序有效銜接的要求
訴前程序在司法實踐中占據主導地位,但這并不排斥訴訟程序。當訴前程序功能失靈時,有必要進入訴訟程序。此時,訴前調查收集或保全的有關證據,即成為后續提起訴訟的支撐和保障。如果在訴前程序中缺乏明確證明標準,僅依靠辦案人員經驗收集證據材料,很可能會因證據不全而導致程序銜接出現問題。基于此,明確訴前程序證明標準,并以此為指引進行證據收集,可以實現與訴訟程序有效銜接。
二、明確訴前程序證明標準的考量因素
(一)檢察權與行政權的邊界
在訴前程序中,檢察機關應當在法律規定的職責范圍內行使職權,嚴守檢察權與行政權的邊界。具體來說:
1.檢察權的謙抑性。檢察機關主要職責在于監督行政機關依法履職,因此,在行使權力的時候應當秉持謹慎和克制,不能逾越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界限,代行行政機關的有關職權。[1]
2.檢察權的程序性。作為法律監督權,檢察權本質是一種程序性權力,即其行為具有提示性、建議性效果。[2]檢察機關僅需通過法律監督啟動相應程序即可,至于后續調查、處理等,均由行政機關進行負責。
3.行政權的專業性。在社會治理方面,行政機關更具專業性,由行政機關制定方案,對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更有益處。
(二)檢察機關調查能力現狀
1.法律支撐不足。修訂后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21條對檢察機關的調查核實權進行了明確,并確定了相關單位的配合義務,但由于其屬于檢察機關內部法律且規定內容較為模糊,導致該條款剛性不足。
2.辦案人員短缺。受制于人員編制較少等原因,多數基層檢察院存在人員力量薄弱問題,“案多人少”矛盾突出。
3.技術支持滯后。當前,辦案人員調查取證的技術裝備相對滯后,多數只能通過直觀判斷對相關問題進行判定并固定證據,導致無法深入判斷。此外,對于檢測、鑒定、評估等,專業機構少、費用高等問題仍是實踐中的困擾。
(三)待證事實的差異
1.待證事實的重要程度。針對紛繁復雜的待證事實,如果一味要求查清,達到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顯然不現實。應當對待證事實的重要程度進行區分,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調查相對重要待證事實,以求達致較高證明標準。
2.待證事實的可證程度。所謂可證程度,是指待證事實的證明困難程度。受制于認識方式、認識能力和認識技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針對不同的待證事實,可以證明的程度存在一定差異,證明標準也有差異。
(四)后續程序證明標準
隨著調查逐漸深入,辦案人員對案件事實的認識也逐步提高,相應證明標準也應逐漸提升。具體到行政公益訴訟案件中,訴前程序證明標準應當低于訴訟程序證明標準。而且,訴前程序和訴訟程序之間還有行政執法程序。因此,對訴前程序證明標準的考量,應當在明確行政執法程序和訴訟程序證明標準的基礎上,確定證明標準。
三、構建訴前程序證明標準的應然路徑
理論上,證明標準主要有幾種類型:一是“排除合理懷疑”,要求對待證事實達到100%證明程度;二是“高度蓋然性標準”,一般要求達到80%以上證明程度;三是“優勢證據標準”,一般要求達到50%以上證明程度。根據證明標準分類,綜合考量以上因素,訴前程序中,應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對其證明標準進行把握。
(一)宏觀層面:作為訴訟程序的證明標準
在宏觀層面,應當將訴前程序視為一個單獨訴訟程序,認定其證明標準。
從訴前程序自身特點來看。檢察權具有謙抑性和程序性特點,這決定了訴前程序應當采取優勢證據標準。這是因為,如果把訴前程序證明標準明確為排除合理懷疑或高度蓋然性標準,則檢察機關會盡可能查明真相,而行政機關無需另行調查便可以對相關問題進行處理。如此,檢察機關顯然代行了行政機關職能。而采取優勢證據標準,證明有關情況出現可能性更大,督促行政機關調查并解決有關情況,顯然更加符合檢察權行使要求。
從訴前程序與后續程序進行對照的角度來看。行政執法程序的核心意旨在于促進社會治理,為確保精準性,行政機關應當對涉案事實進行充分調研,并應達致高度蓋然性標準或者排除合理懷疑標準。行政公益訴訟為行政訴訟的一種特殊表現形態,且更加突出對公共利益保護,因此,其證明標準應當高于或者等于行政訴訟的證明標準。司法實踐中,行政訴訟證明標準居于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和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中間。[3]而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為排除合理懷疑,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為優勢證據標準,因此,行政訴訟證明標準應當為高度蓋然性標準,相應地,行政公益訴訟證明標準則至少為高度蓋然性標準。在明確以上兩個程序證明標準的基礎上,應當將訴前程序證明標準界定為優勢證據標準。
綜上所述,在宏觀層面,訴前程序的證明標準應當明確為優勢證據標準。同時,還應當根據訴前程序具體情況對優勢證據標準進行動態掌握。具體來說:一方面,從待證事實重要程度來看。越是標的額大、社會影響大的案件,其證明標準應當更高。另一方面,從待證事實的可證程度來看。越是證明難度高的案件,其證明標準應當更低。
(二)微觀層面:基于待證事實產生的證明標準
1.公益受損的證明標準。一方面,對公共利益受損的證明有一定證明難度,過高的證明標準恐怕難以實現。[4]另一方面,作為啟動訴前程序的首要前提,公益受損狀態理應在一定程度上被證明,其證明標準不應過低。否則,僅以公益受損這一籠統表述啟動訴前程序,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缺乏底氣且監督意見有不被采納風險。綜合來看,針對公益受損現狀,可以采取優勢證據標準。也即,在檢察機關提供相應證據后,行政機關相信公益受損可能性大于沒有受損可能性,并基于此開展后續調查。
2.行政機關監督管理職責的證明標準。從訴前程序目的來看,其主旨在于督促行政機關依法履職,如果無法精準查找到相對應行政機關,則可能出現檢察建議發送對象錯誤情況,破壞公益訴訟制度根基。因此,無論是公開文件所確立的行政機關職責還是內部文件所確立的行政機關職責,證明標準應是一致,而且為排除合理懷疑這一標準。
3.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證明標準。在司法實踐中,行政機關違法履職可以分為作為和不作為兩種情況,其證明標準存在差異。
首先,行政機關以作為形式違法履職。筆者認為,可以將其證明標準設定為高度蓋然性標準。理由如下:一是在全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行政機關以作為形式違法履職情況少、影響大。針對此類情況,通過借調、組建專案組等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補充公益訴訟部門辦案力量,不宜將優勢證據標準作為指引。而且,設定較高的證明標準,盡可能收集證據材料,也有助于檢察機關對行政行為進行監督。二是作為違法表現為行政機關積極主動采取了一些措施和手段,產生了相對較多證據材料,檢察機關獲取證據可能性較高,設定較高證明標準有現實可能性。三是行政機關作為違法通常與腐敗、瀆職等違法犯罪行為雜糅,較為錯綜復雜。以此為出發點,檢察機關深挖可能收集的證據材料,通過移送監察委等方式,有利于強化法律監督剛性。
其次,行政機關以不作為形式違法履職。由于不作為違法無法產生很多證據材料,其可證程度不高,不應設定過高證明標準。同時,基于監督的權威性和精準性,過低證明標準亦不可行。筆者認為,應當將不作為違法履職證明標準界定為優勢證據標準。換言之,只要有證據證明行政機關不作為違法履職可能性更高,檢察機關便履行完證明責任。
4.因果關系的證明標準。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行為應當與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具有關聯性。對于該待證事實,筆者認為,應當將其證明標準明確為排除合理懷疑。理由如下:一是基于監督的精準性,只有明確因果關系,才可以對行政機關進行有效追責。二是基于監督的權威性,只有將因果關系進行明確,進而向相對應的行政機關發送檢察建議,才能做到有效監督,進而體現檢察監督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