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詩經》“起興”手法,讓詩歌詩味更濃
趙麗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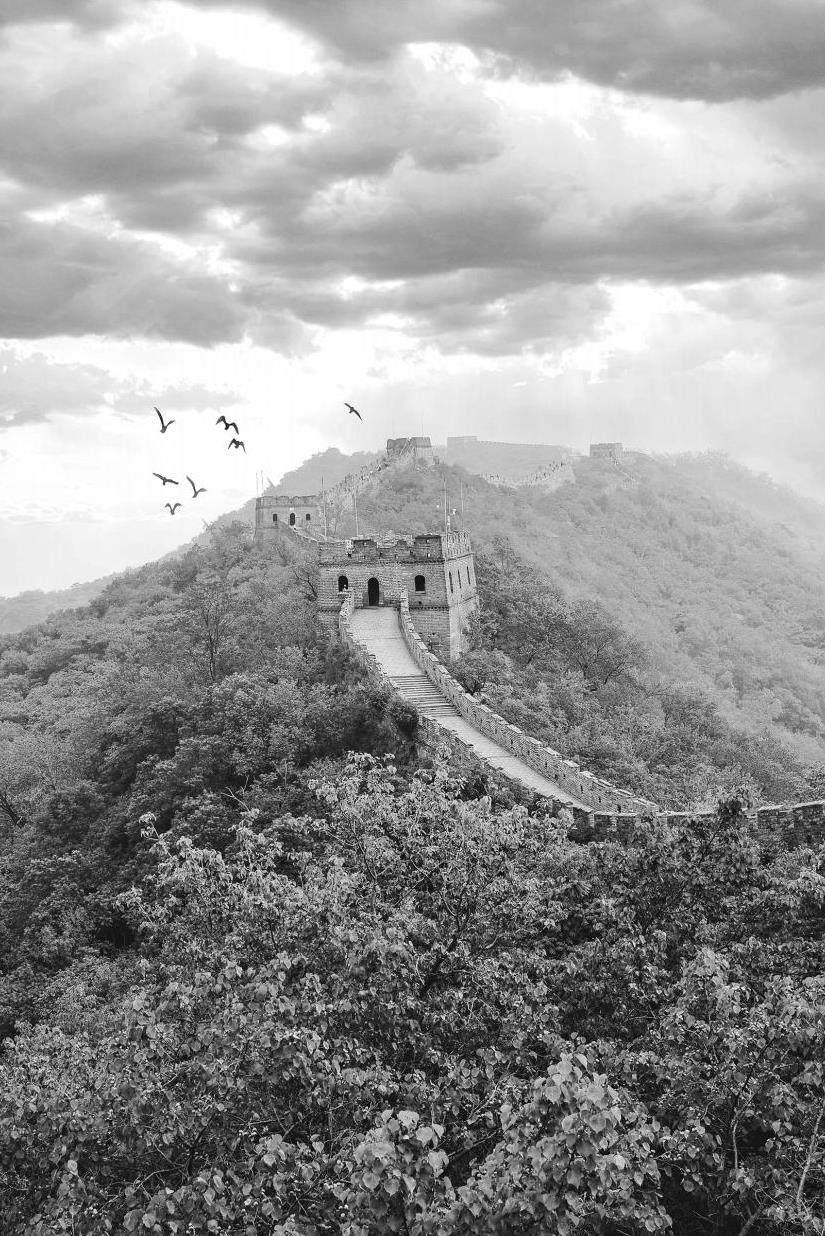
作為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無疑是中國文學史上最燦爛、最閃爍的篇章之一,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清末的學者梁啟超曾這樣評價:“現存先秦古籍,真贗雜糅,幾乎無一書無問題,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詩經》其首也。”雖然帶有歷史偏見,但《詩經》直寫生活、表達人們最樸素的愿望,確實如梁啟超所言值得一“信”。《詩經》中最重要的表現手法是賦、比、興。關于它們的準確含義,多年來爭論不休。總的來說,賦,就是直陳其事,直接描寫;比,就是比喻;興,就是起興,就是先言他物,引出要吟詠的對象,這是詩歌中最具特點的表現手法。
我們知道詩歌是詩人感于現實之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面,它需要外界事物引發;另一方面,需要詩人對詩歌內容的修正,這里要運用到高超的表達技巧。而“起興”無疑是很重要的,是寫詩的“起源”,因為眼前的優美景物或事物必然蘊含著詩人觸物所引發的情思和感慨。可以這樣認為,“興”是一種極為委婉含蓄的表現手法,它讓詩歌的詩味更濃,更能以事感人,以情動人。本文以《關雎》? 《蒹葭》《子衿》三首詩歌為例,探討起興對詩歌濃濃詩味的影響。
一、起興,營造了如詩如畫的美感
(一)《關雎》中構建了唯美的美景
《關雎》的起興句是“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雎鳩”是一種水鳥,就是今天我們說的魚鷹,傳說它們成雙成對、形影不離,是忠貞、淳樸愛情的象征。詩人用“雎鳩”引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表現男子追求心儀女子的愿景;“關關”是擬聲詞,形象地展現了水鳥互相鳴叫的場面。不妨聯想一下此時的畫面,一位小伙子偶然間在河洲上看見一對相親相愛的水鳥,聽到它們一唱一和的鳴叫,響徹天際,在空曠的小洲里回環,恬靜和諧,這是多么溫馨、浪漫的時刻啊,也把讀者帶到一片平曠遼遠的境地之中。后續的兩句——“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說的是小伙子心儀的對象采摘荇菜的過程,畫面中的姑娘乘著小舟,認真地挑選著水草。遠處是水鳥相愛的啼叫,近處是姑娘采摘荇菜的場景,把兩者有機融合,不就是一幅溫馨的圖畫嗎?
(二)《蒹葭》中營造了朦朧的意境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意思是“這里的蘆葦非常茂盛,一顆顆露珠凝結成了霜”,巧妙地營造了一個朦朧、浪漫的夢幻意境,仿佛讓人置身其中。后續的“蒹葭萋萋,白露未晞”和“蒹葭采采,白露未已”同樣營造了這樣的境界。天地間是如此朦朧,但“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意思是說思戀的人在別處),刻意凸顯了失意與惆悵的氛圍。這首詩歌運用起興手法,以景融情,茫茫的水汽、蒼茫的白茅草,都讓詩人陷入無限的情思與想象之中,情與景相互交融,最終產生“天人合一”的朦朧圖畫。
(三)《子衿》實寫現實的想念
《子衿》的起興沒有《關雎》的唯美,也沒有《蒹葭》的朦朧,因為《關雎》《蒹葭》明顯帶有中國古代水墨山水的意境,在空曠的空間中隱藏自己的情感。而《子衿》,實寫一位女子的心理,起興起得快速,從衣襟和佩玉繩子的顏色開始說起,暗示詩人內心的輾轉反側、心中的纏綿以及憂思不斷的牽掛,同時也有強烈的畫面感:一天,女子約見了一位衣襟淺藍、佩戴著用淺藍色繩子纏繞的玉佩的男子,但他最終卻離開了自己,留下了綿長的思念。
二、起興,協調了靈動抒情的韻律
詩是用來抒情的,通過靈動的節奏抒發自己的情感,當然,詩的節奏是由作品內容決定的,只有節奏和內容相互協調,才能有助于充分發揮詩歌的抒情效果。因此,《詩經》中的起興手法,確保在詩詞一開頭就確定了全詩的韻腳和音調,不但讓上下句聯系密切,還可使語言詠唱有序,行文顯得輕快、活潑。比如在《蒹葭》當中,起興句“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已經奠定了 “霜”的韻腳是“ɑng”,此節中的“方”“長”“央”的韻腳都是“ɑng”;同理,第二節的起興句是“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晞”的韻腳是“i”,接下來所有的最后一字“湄”“躋”“坻”的韻腳也都是“i”,我們在朗讀時,就會發現朗朗上口,很容易熟讀成誦,這都符合詩歌的特點,充滿著濃濃的詩味。還有,《詩經》運用雙聲疊韻的聯綿詞,增強音調的和諧美和描寫人物的生動性。如《關雎》中“窈窕”是疊韻,“參差”是雙聲,“輾轉”既是雙聲又是疊韻,讀起來無不讓人感覺到活潑逼真,聲情并茂。同樣的手法在《子衿》里,也可見一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子佩,悠悠我思”就是重章疊句的應用。更為重要的是,《詩經》的起興為詩歌注入了豐富而強烈的情感,再加上相同協調的韻律,把上下句中不同的事物很自然地結合在一起,讓整首詩渾然一體。比如在《關雎》的第二節“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中,我們看到一個男子得不到心上人的焦急和無奈的心理感受,可謂形聲兼顧,達到了追求形象意境之美與聲韻和諧之美的兩者有機統一的境界。又比方說,在《蒹葭》當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湄)(涘)”,深刻表現了反復追尋及追尋之艱難、渺遠的情感。就算千年之后的我們讀起來,也感覺到情感的真摯,不愧是“古代愛情詩的絕唱”。
三、起興,刻畫了個性鮮明的形象
起興就是用個性鮮明的形象來渲染氣氛,激發讀者想象,創造出纏綿悱惻的情調,又能引起下文的故事,起到了統攝全篇的作用。比方說《關雎》,詩的本意其實是寫“求淑女”,于是以在河洲上關關和鳴的雎鳩起興,由雎鳩鳥的雌雄匹配聯想到“君子”“淑女”的愛情,然后順著這個思路寫出“君子”對“淑女”的一片癡情。本詩的起興之妙在于情趣與自然景物渾然一體,達到了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在傳說中,雎鳩和鴻雁、鴛鴦一樣,感情專一,絕不亂配,詩人用雎鳩起興,生動形象地表明了它們純潔而又真誠的愛情。詩中還以荇菜既得而“采之”“芼之”,來表現求偶的過程是由挑選到認識再到理解,最后喜結良緣。耐人尋味的是,雎鳩鳥除了忠貞不貳之外,還有其他意蘊:雎鳩天性溫順,可比淑女之嫻靜;雎鳩乃“河洲”常見之鳥,可使人聯想起常來河邊采摘荇菜的女子;“關關”乃雎鳩雌雄唱和之音,可起“君子”思“逑”之情,這種含蓄委婉而又生動的形象描寫,讓全詩產生了意味深長、回味無窮的藝術魅力。
《蒹葭》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情感更加鮮明。它用“蒹葭”起興,深秋,露重霜濃,而水面的蘆葦蒼蒼,詩人不顧秋寒去湖邊守候自己的心上人,因為“伊人”在水的另一方。此時的男子糾結萬分:逆流而上去尋找吧,但道路崎嶇且漫長;順流而下去尋找吧,她仿佛又在水中央。在我們看來,這個“伊人”飄忽不定,可望而不可即,實際上是描繪了一位青年男子深情的執著,而且這名男子在不停地追求,從“白露為霜”到“白露未晞”再到“白露未已”,時光匆匆,唯一不變的是男子的執著深情,讓我們看到了一位對愛情忠貞不貳的青年才俊。
《子衿》不同于《關雎》和《蒹葭》,因為后兩者是男子追求女子,而《子衿》表達的是女子對男子的思念,在古代中國,能直接宣揚女子對愛情的追求,就已經是很了不起了。《子衿》 的第一節以“子衿”(衣領)起興,表明女子對男子刻骨銘心的愛戀,但男子失約,女子很不開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為什么你就不能給我一個交代呢?可憐的女孩子,在城樓上苦苦等了一天,相思之苦,恐怕只有自己知道,這短短的一天,仿佛是三個月,將這位女子的焦急、失望、抱怨、思念的情緒全部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形象非常鮮明,讓人感嘆:癡情如此,比《關雎》和《蒹葭》有過之而無不及。
起興之“妙”在于其思路和內容既有趣又深刻,其中存在許多自然名物知識和社會生活情理,引人聯想,啟人睿智,所以朱子也宣稱:“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詩歌的本質是表現人的感情和志向,以最簡練的語言達到最感染人的效果。所以,起興的手法更能讓人領悟到濃濃的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