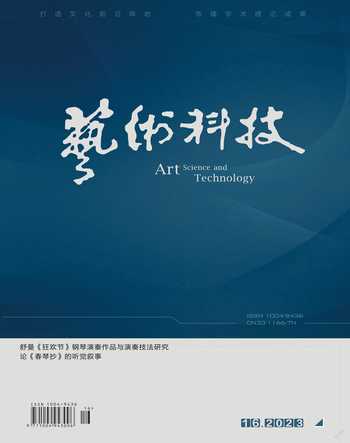新文學的“泥土”
摘要:1925年夏,未名社于北京成立,這是一個由魯迅發起并自始至終親身參與的現代文學社團。因為魯迅的存在,未名社吸引了眾多學界的研究目光,同時由于魯迅過于耀眼,所以很少有研究關注未名社青年成員文學活動的價值和貢獻。社團主要成員除魯迅外,還有韋素園、李霽野、韋叢蕪、臺靜農以及日后得知消息趕來加入的曹靖華。不難發現,社團成員中除魯迅外,均不是知名作家,他們沒有接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但以踏實苦學的精神耕耘自己的文藝園地,為新文學的發展譯介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理論和批評。在活躍的6年時間(1925—1931年)里,未名社文學活動的價值得到了當時諸多作家的認可。但是因為未名社文學史現場模糊、活躍時間較短等,過往研究主要停留在社團史和人事交往層面,文學活動的價值長時間被遮蔽,未得到發掘。未名社的社團歷史、文學翻譯和文學創作在中國的時代浪潮中都是不俗的“浪花”,關注這些“浪花”有利于深化對未名社的認識,把握20世紀初部分知識分子的心理走向。基于此,文章對未名社文學活動展開述評。
關鍵詞:未名社;魯迅;文學翻譯;文學創作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16-00-03
1 同人的相聚與散落
1922年春,中學沒有畢業的臺靜農從漢口來到北京大學旁聽,隨后與結束俄國留學不久的同鄉韋素園相遇,第二年同來的還有李霽野、韋叢蕪。四人都來自宿州葉集鎮,曾經在同一所小學讀書,幼時便感情甚篤,同在異鄉求學的艱難經歷讓他們之間從地緣關系轉化為親密的業緣關系。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幾名小鎮青年日后能夠在人才濟濟的中國文壇占據一席之地,與他們的“抱團取暖”密不可分。得益于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治校政策,當時的北大成為各地學子心中的文學殿堂,諸多文學史上留名的作家,如沈從文、瞿秋白、丁玲等人,都曾在北大旁聽。雖然這時北大為外地學子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但實際上小鎮青年們異鄉求學的日子還是充滿了酸澀和苦楚,來到北京后卻發現實在難有所為。但葉集鎮的這幾名青年是幸運的,他們在文學路上得到了魯迅的提攜和幫助。
1924年9月20日,在《魯迅日記》中記錄了這樣一件小事:“上午張目寒來并持示《往星中》譯本全部。”[1]張目寒是魯迅在北京世界語專科學校的學生,也是安徽葉集鎮人,李霽野將《往星中》的譯稿經由這名同鄉轉交給魯迅。正是《往星中》的出版困難,引發了未名社的成立。魯迅對稚嫩的文學青年充滿耐心和包容,收到李霽野的譯稿后很快就開始閱讀校對。在《魯迅日記》和李霽野的回憶錄中,都記載了第二天魯迅就開始了相關工作,并隨即著力尋找出版作品的機會。雖然有魯迅這樣的成名作家推薦,但《往星中》的出版過程還是坎坷不斷。在《憶韋素園君》一文中,魯迅回憶起這件事時說:“那時我正在編印兩種小叢書,一種是《烏合叢書》,專收創作,一種是《未名叢刊》,專收翻譯,都由北新書局出版。出版者和讀者的不喜歡翻譯書,那時和現在也并不兩樣,所以《未名叢刊》是特別冷落的。”魯迅多經輾轉,最后在他自己主編的《未名叢刊》中也沒有出版這本《往星中》,不禁讓他感慨翻譯和譯者的艱難。最后索性與北新書局的老板李小峰商量,將不受歡迎的《未名叢刊》從北新書局移出,交由李霽野等人編輯出版。
于是,李霽野、韋素園、臺靜農、韋叢蕪便在魯迅的建議下效仿日本丸善書店成立了未名社,因此未名社不單是一個文學社團,也是一個出版社,其創刊之初便承載著魯迅推動中國翻譯事業發展的愿望,而社中的這些青年則是魯迅愛護和寄予希望的文學嫩芽。當時未名社的這批青年生活十分拮據,除魯迅資助的100元外,據郭汾陽考證,剩下的資金均由他們同鄉的長者臺壽銘資助。“臺壽銘接到李霽野、臺靜農的求助信后,很快欣然寄去二百元,作為葉集青年韋素園、韋叢蕪、李霽野、臺靜農四人參加‘未名社籌集的印書費用。”[2]當時遠在河南參加革命的曹靖華在得知未名社成立后,積極寫信響應表達自己參加未名社的愿望,并附上社費50元。社址選在了北京大學附近的沙灘公寓,彼時這里也是韋素園簡陋破舊的住所。魯迅常常在北大講完課后便貓著腰鉆進去與這群青年聊天,把這里戲稱為“破寨”,韋素園也成了未名社最早的“守寨人”。
社團成立后,幾經沉浮。1928年2月,韋素園和李霽野合譯的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首次印行出版,因為書名中含有“革命”一詞,濟南第一師范的代售處被張宗昌搜查,連帶未名社北京的編輯部也被查封。經歷這場無妄之災的未名社反而迸發出更加強大的活力,臨時成員李何林、王青士加入后,未名社有了更多的精力經營售書,在北京新添了一個售書處,一時間未名社的事業達到了鼎盛。1929年,魯迅歸京探親時見到了未名社的蓬勃發展,社中青年也對魯迅十分熱情,種種景象都讓處境艱難的魯迅感到寬慰。但是好景不長,隨著臨時成員離去,韋素園患病,其他成員也因為要奔向自己的事業,無暇顧及社務,未名社漸漸走向了下坡路。1931年5月,韋叢蕪無力支撐未名社,致信魯迅表示將未名社交由開明書店代管,魯迅因此退社,第二年韋素園病逝。1933年春,未名社在京、滬兩地登報發布了社團解散的聲明。至此,未名社解散,社團同人散落,現代文學史上為數不多致力于譯介外國文學的一個社團不復存在。
2 心血所系的事業——外國文學譯介
在現代文學史上諸多留名的文學社團中,未名社獨特的價值在于其對外國文學的譯介。這些譯作涉及英美、北歐、蘇俄等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小說、戲劇、文藝理論、文學批評等多種文體。魯迅在《憶韋素園君》中寫道:“然而未名社的譯作,在文苑里卻至今沒有枯死的。是的,但素園卻并非天才,也非豪杰,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1]這里所說的“泥土精神”便是未名社譯介活動最真實的寫照。創作誰人都知道可尊,但是甘心掩去姓名,選擇翻譯,未嘗不是一種風骨。
在未名社的青年成員中,除臺靜農專注于文學創作,完全不涉及文學翻譯外,其他4名成員都是以譯介進步民族的文學為主要的文學事業。從翻譯所用的外語來看,未名社中的4名成員可以分成兩派,首先是用俄語直接翻譯蘇俄作品的韋素園和曹靖華,他們都曾在蘇聯留學,能夠直接閱讀俄語原文,憑借自己的俄語水平,譯介了大量俄國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俄語直接翻譯的好處就是能夠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給讀者的第一印象。韋素園所譯的《外套》《黃花集》《文學與革命》等作品,曹靖華所譯的《白茶》《蠢貨》《第四十一》等作品,都盡可能保留了蘇俄文化的內涵,尤其是文化負載詞的翻譯,最大限度地展現了作為“魯門弟子”的直譯傳統,也將作品中底層人民的苦難更全面地展示出來。
另外一派則是用英語翻譯的李霽野和韋叢蕪,兩人都是中學沒有畢業就到北京,轉入崇實中學就讀。在北京求學的過程中,自學英語從事翻譯,但是因為語言的限制不能直接翻譯,往往需要借助英譯本轉譯。在未名社的英譯本轉譯活動中,一個不得不提到的人就是英國的女翻譯家加尼特(Constance Garnett)。加尼特一生熱愛俄國文學,是第一個將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和契訶夫(Antonchekhov)的作品翻譯成英文的人,除此之外,她還翻譯了大量果戈理(Gogol)和屠格涅夫(Turgenev)的作品。正是她對俄國文學的大力譯介,讓當時的中國有了更多接觸蘇俄文學的機會。這時的中國剛從蒙昧中蘇醒,渴望吸收進步思想的營養,而蘇俄文學是最符合當時中國國情的“營養品”,因此,當時的大量作家和翻譯家都曾接觸過加尼特的譯作。韋叢蕪在他翻譯的《罪與罰》序言中說:“我是根據Constance Garnett的譯本重譯的,時常也用俄文原本對照。”[2]雖然英語轉譯使原作中的部分信息不能完整傳達,但是擴大了譯者的文化視野,李霽野和韋叢蕪對英美文學的涉獵充分證明了這一觀點。
從翻譯內容上看,未名社的翻譯大致有三類:浪漫主義作品、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和左翼文學理論。其中,浪漫主義作品和文學理論主要是韋叢蕪和李霽野的貢獻。在語言的影響下,兩名未名社的譯者對歐美的浪漫主義非常關注,如韋叢蕪翻譯的《格列佛游記》《英國文學:拜倫時代》,李霽野翻譯的《近代文藝批評斷片》等,都是英美浪漫主義的產物。對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的翻譯是未名社文學翻譯的主要工作,每個成員在時代中國的感召下,對批判現實主義作品中所展現出的黑暗現實深惡痛絕,大加撻伐。對左翼文學理論的紹介可以說是批判現實主義翻譯的延伸,在具體的文學作品之外,他們也留心文學理論,尤其是左翼文學理論的紹介,他們作出了突出的貢獻。1928年7月,未名社因組織出版左翼文學理論作品被北京方面查封,而起因就是韋素園和李霽野合譯的《文學與革命》。可以說,未名社在文學翻譯的路上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3 別樣驚喜——未名社的文學創作
學界過往對未名社的研究主要是與魯迅的關聯和未名社的文學創作,這是因為,雖然未名社的主要文學活動是譯介進步民族的文學作品,但其在文學創作上也多有建樹,并且成員自身也有獨特的文學創作風格。韋素園和李霽野長于散文,韋叢蕪擅長詩歌創作,臺靜農的鄉土小說算得上是近代鄉土小說中的佼佼者。
韋素園是葉集鎮青年中年齡最長者,也是帶領其他幾名小鎮青年走出大山的人,為人沉靜寡言,但如同長兄一樣關懷著幾個幼弟,之后的未名社在內憂外患時“抱團取暖”,韋素園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他也是所有成員中離世最早的,因為肺病,1927年之后便長期在西山療養院修養,所以他的作品往往是從病人的視角,包含個人的疾病體驗。在文學創作歷史上,疾病文學是一種邊緣文學,不過并不少見,因為疾病是一種常見的生活體驗,而作者能夠將自身獨特的體驗用文字撰寫出來,這種異于常人的世界畫卷讓讀者對生命的體驗更加深刻,韋素園的散文便具有這種力量。
李霽野的性格與韋素園相似,靜水流深,這也使他對散文創作更為傾心。1928年,李霽野開始了自己的散文創作生涯,相較于譯作選材的激烈生猛,李霽野散文呈現出另一種樣貌,關注生命,關注人間之愛,筆調顯得親切從容。
韋叢蕪是未名社詩歌成就最高的人,他的新詩《君山》《冰塊》等都具有極強的現代性和較高的藝術水平。1981年,漢學家馬悅然在編寫《中國文學指南1900—1949》時,馮至曾徑直推薦韋叢蕪和他的新詩《君山》,可見韋叢蕪的詩歌創作已經得到時人的認可。《君山》是一首長篇敘事詩,共計40節,600多行。詩歌講述了詩人在旅行途中遇到兩個姐妹,并對她們產生了復雜微妙的感情。韋叢蕪在詩歌中將東西方文化和表現手法結合,深刻細膩地展現了獨特的情感體驗,是現代敘事詩中不可多得的一部作品。
臺靜農主要的文學活動是小說創作。1926年,彼時的臺靜農尚在中學求學,隨著魯迅的南下,狂飆社作家群與未名社作家群發生沖突,社內一時間沒有了稿件來源,臺靜農才不得不開始自己的小說創作生涯。剛開始臺靜農以愛情小說試水,但是在魯迅的影響下,臺靜農的小說轉為描寫家鄉農村封建落后的場面。出乎意料,開始文學創作的臺靜農成果斐然,其創作的鄉土小說成為未名社的一面金字招牌。隨后《未名新集》出版了他的小說集《地之子》,他也成為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鄉土小說家中的一員。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的《導言》中對臺靜農有很高的評價:“在爭寫著戀愛的悲歡,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能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于這作者的了。”[3]
4 結語
未名社在學界受到的關注與其文化貢獻極不相稱,在現代文學史上是一個并不顯眼的存在,社團不善于宣傳造勢,一心盯住文學,不曾多留下只言片語。已有的研究中少有論著以未名社為專門的研究對象,大多數只是在論及魯迅或現代文學社團時順帶提及。但是隨著對未名社研究的深入,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到這個甘心“沉默”的社團。它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誕生,又為五四新文學引進了新的外國文學范式,提供了進步民族的文學理論,默默成為新文學發展的土壤。社團的文學活動為新文學創造了珍貴的發展環境,沒有辜負魯迅對他們的期望。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步履維艱,從早期西學東漸到創造社、新月社等文學社團,無不是中國知識分子探索出路的印記,但是在這些醒目的存在之外,普通文學青年的努力亦是探索出路的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 魯迅.魯迅日記: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441.
[2] 郭汾陽.臺壽銘與“未名社”[J].魯迅研究月刊,1990(2):64-65.
[3] 魯迅.魯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66.
[4]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M].韋叢蕪,譯.南京:正中書局,1947:7.
[5] 趙家璧,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M].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80:16.
作者簡介:胡旭(1998—),男,安徽池州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