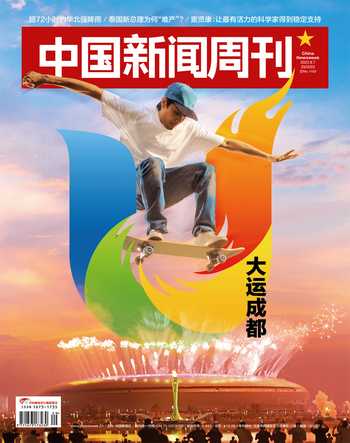結構性改革政策同樣有立竿見影之效
劉世錦
自2010年經濟增長進入高速到中速的轉型期以來,當前是中國經濟最為復雜和迷茫的階段。穩增長的老辦法不行了,新辦法是什么?
過去十年,高速增長期的主要驅動力量基建、房地產、出口,經濟下行時抓一下還管用,但這一次房地產長時間負增長、基建投資難持續,出口也是下行態勢。從國內的基本背景看,仍處在高速到中速或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期,原有動力觸底,有的出現“超調”;由來已久的結構性矛盾水落石出;新老動能銜接出現問題;政策應對也有改進之處。
從需求端來講,重要耐用消費品、房地產、基建等相繼出現歷史需求峰值,進入減速期。生存型消費趨于穩定,發展型消費帶動消費結構升級,需求結構已經出現重要變動。關注生存型消費不夠,重心應轉到發展型消費,這一點要引起足夠重視。而發展型消費和政府基本公眾服務均等化直接相關。這方面最突出的問題是近三億進城農民工的保障性住房、醫療、教育、社保等不到位。四億中等收入人群與九億中低收入人群存在著巨大結構性需求缺口。
從供給側來講,受需求減速的影響,傳統產業進入下行通道,需要一批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的新先導產業帶動產業更替和升級。但現在房地產下滑過快、過深,引發全局性的沖擊。企業家預期不穩、信心不足,制約創新活動和新先導產業的成長。
資產負債端的問題最近討論較多。在需求和供給雙重沖擊下,政府、企業和個人資產負債表都經歷著從數量擴張型向效率導向型的轉換,這個轉換非常不容易,經常是被動的和危機倒逼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只是陷入困境或危機出現后的階段性現象,問題是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如何應對。
房地產等行業原有的高負債、高周轉、高風險模式難以為繼。不少領域仍在提杠桿,只是“借新還舊”,大量資產缺少現金流,出現某種意義上的龐氏結構,到了某個時點將無法維持運轉。所以,本質上還是經濟增長由高速到中速后資產負債模式的轉型問題。
三年疫情,宏觀政策已經盡力。貨幣政策繼續放寬的空間已經很小,財政政策僅有的一點中央發債空間,如果導向不對,也可能是加劇而非緩解經濟轉型困難。如果把穩增長注意力繼續置于宏觀政策上,副作用將會加大,更重要的是將會再次錯失結構性改革的時機。
需要澄清的是,具有擴張效應的結構性改革同樣可有立竿見影之效。新一輪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一是以進城農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的需求側結構性改革;二是以穩定房地產等既有支柱產業、激發企業家精神助推新先導產業發展為重點的供給端結構性改革;三是以擴大有效需求、轉換資產負債模式、化解防控風險為重點的資產負債端的改革。
現階段中國有兩個大的增長引擎。從橫向看,提高對低收入階層特別是農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發需求潛力。有一個說法,農民進城帶動消費增長30%,如果基本公共服務到位,又可以增長30%。近9億中低收入階層如果能夠達到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對現有產業將會形成一個很大的拉動。從縱向看,通過穩定預期和信心、改善營商和發展環境,激勵企業家精神,推動創新、新先導產業發展和經濟社會轉型升級。因此,建議實施一些重要政策措施。
一是實施進城農村人口基本保障住房建設工程或購置計劃;實施為期三年的以近三億進城農民工為重點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攻堅計劃,其也可看成是脫貧攻堅戰的升級版。
二是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鄉結合部,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與國有土地同權同價;允許農民宅基地向集體組織之外轉讓、抵押、擔保等交易行為,這方面的口子可以開得大一些。試點地區的經驗表明,利遠大于弊。以往有人擔心,農民把房子賣了以后,會不會引發社會問題?建議所獲收入優先為相關人員完善社保,包括保障性住房,形成比原有土地保障更可靠、更有效率的現代化保障體系。這樣就可以土地利用效率提高、農民收入增長、社保能力增強,一舉數得。
三是加快發展新先導產業,包括新技術催生的新產業或“未來產業”,成熟產業和傳統產業中的高技術和附加價值產業,數字技術產業化、雙碳綠色轉型帶動的新產業等。
四是允許和鼓勵平臺企業、大型科技骨干企業大膽投資、積極創新,參與國家重點項目建設,實行常態化、負面清單為主的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