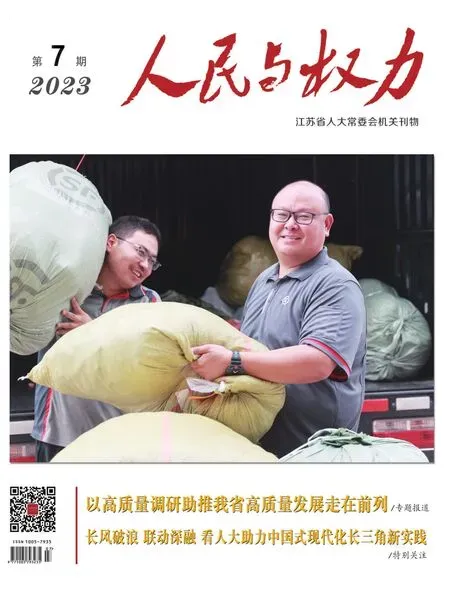“只因曾讀數(shù)行書”
☉王彬彬

讀中國古代的野史、筆記、小說,偶爾能遇上好詩,有時是一首詩中的一兩句十分精彩,有時則整首詩都很棒。這些散見于專門的詩歌集以外的詩,往往為文學(xué)史家所忽略。
清人吳敬梓《儒林外史》第九回,寫到所謂的“高士”楊執(zhí)中在一張紙卷上寫了一首“七言絕句”,但其實,這是一首元人呂仲實所作七律的后半。吳敬梓把這半首無人詩送給楊執(zhí)中,自然意在諷刺楊執(zhí)中,但也因為出現(xiàn)在這樣有影響的小說中,反倒使這首詩能夠比較廣地為人所知。
呂仲實的這首七律,最早記錄在元人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里。《輟耕錄》卷十二“文章政事”條說的是呂仲實的故事。陶宗儀說,呂仲實“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污”。呂仲實未科舉告捷、做官發(fā)達前,家境非常貧寒。一天,早晨起來便斷炊,半粒米也沒有,以薄粥充早飯都不成。呂仲實便拿起布袍找人換米,不管怎樣,先把早飯吃了再說。妻子則“有吝色”,就是舍不得那件布袍。布袍換掉了,天冷了穿什么呢?呂仲實于是“戲作一詩”,曰:“典卻春衫辦早廚,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里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shù)行書。嚴霜烈日皆經(jīng)過,次第春風(fēng)到草廬。”這詩平易如話,老嫗通解。最出色的,當然是頸聯(lián)“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shù)行書”了。呂仲實說自己之所以如此窮窘,是因為不肯做“些子事”。那么,為什么不做呢?呂仲實的解釋是只因為讀過些書,只因為是一個讀書人,越不過道德倫理的底線。
《儒林外史》第九回,婁府兩公子聽說那窮鄉(xiāng)僻壤的地方有一位叫楊執(zhí)中的人,替別人管理鹽店,卻百事不問,每日里只顧自己讀書,店里終于虧空了七百多兩銀子,便認定這是一位隱居于窮鄉(xiāng)僻壤的“高士”“讀書君子”。婁府兩公子便想結(jié)識這位超凡之人。但幾次到楊執(zhí)中居住的新市鎮(zhèn)登門拜訪,都撲空。最后一次,在歸來的船上,遇上一條賣菱的船,便向船上的孩子打聽楊執(zhí)中,孩子不但熟知楊執(zhí)中,還拿出一張紙卷交給婁府兩公子。兩公子打開一看,是一幅素紙,上面寫著一首七言絕句,也就是呂仲實《典卻春衫》詩的后面四句。最后還寫著:“楓林拙叟楊允草。”而兩公子看罷不勝嘆息,說道:“這先生襟懷沖淡,其實可敬!只是我兩人怎么這么難會?”兩位貴公子為終于不能見到楊執(zhí)中而遺憾不已。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儒林外史》能“以公心諷世”“燭幽索隱,物無遁形”,這在第九回對婁府兩公子拜訪楊執(zhí)中的敘述中表現(xiàn)得很充分。在那首表示“襟懷沖淡”的七絕出現(xiàn)以前,讀者已經(jīng)知道楊執(zhí)中實際上是一個既迂腐又惡俗之人,待到這首剽竊的詩出現(xiàn),楊執(zhí)中就在迂腐、惡俗之上,還有奸詐虛偽詭詐的一面。婁府兩公子不能識破真相,也顯示了他們不過是繡花枕頭而已。
近人鄧之誠的《骨董瑣記》卷二有“呂仲實詩”條,記錄了呂仲實的兩首詩,一首是前面說過的《典卻》,另一首《寄內(nèi)》,也是七律:“自從馬上苦思卿,一個窮家兩手擎。少米無柴休懊惱,大男小女好看成。恩深夫婦情何極,道合君臣義更明。早晚太平遂歸計,連杯共飲話離情。”這是身居逆旅的呂仲實寫給家中老妻的詩,仍然是用語淺易清新、真情自然流露。
回到那首“典卻春衫”,呂仲實對老妻說“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shù)行書”。這應(yīng)該有個前提,有個言外的起因,不然就有些突兀。我想,那就是老妻曾埋怨夫君不肯做“些子事”,不然也不至于一貧如洗,呂仲實便解釋說自己之所以不敢做“些子事”,因為是一個讀書人。并非呂仲實要努力克制自己才沒有做“些子事”,而是那讀過的數(shù)行書內(nèi)化為強大的精神屏障,擋住了呂仲實走向墮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