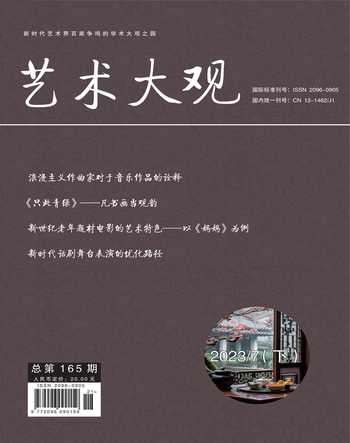大理白族小調《新麻雀調》的詞曲演唱
趙賽前
摘 要:民歌是人類民族民間生活的重要實踐記錄和思想提煉。民歌在世界各國、各地區、各民族幾乎都擁有自己代表性的民族民歌佳作。大理白族民歌有其獨特的藝術魅力,是白族表達自我的一個重要途徑。白族民歌在創作和演唱上,有其自己獨特的審美習慣和表達方式。其中,大理白族小調《新麻雀調》是大理白族民歌中極具代表性、傳唱較廣、影響至深的瑰寶作品,它是白族民歌元素特點的高度提煉和綜表。探究大理白族小調《新麻雀調》的音樂形態,有助于我們了解和認識白族民歌突出的獨特音樂形象。音樂創作離不開人類的生活,更離不開人類賴以交流、溝通的語言。白族民歌亦是如此,白族民歌創作與白族生活、白族語言有著不可分割的“子母”關系,決定了白族民歌詞曲創作的“重詞”慣象。和其他民族民歌一樣,白族民歌有著相似的音樂情愫,但同時也有著不同的音樂表達方式。筆者通過對大理白族小調《新麻雀調》的音樂形態探究,加深人們對白族民歌小調音樂習性和個性特點的認識。
關鍵詞:白族;小調;語調化;生活;語言
中圖分類號:J60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3)21-000-03
白族主要聚居于我國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少部分還分布于湖南、貴州、四川各省及云南怒江、保山、楚雄等云南各地州。白族民歌作品主要以白族山歌和白族小調為主,白族小調是白族音樂個性呈現的重要形式,其音樂影響主要分布在大理白族聚居區。本文探究的大理白族小調《新麻雀調》,在大理白族聚居區流傳久遠、影響深廣。《新麻雀調》最早是由白族大本曲“十八調”中的《老麻雀調》創編演變而成的。大本曲是云南大理“白族特有的演唱長篇故事的一種曲藝形式”。[1]大理白族“大本曲”的唱腔素有“三腔九板十八調”的總稱。大本曲中的“十八調”只是作為演唱者在演唱時穿插在大本曲之間的輔助性白族小調,這便是《老麻雀調》在大多白族傳統大本曲曲目演唱時的實際效能。《老麻雀調》雖然作為白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自娛自樂的演唱歌曲形式存在,但在大本曲演唱中大多是輔助性唱腔。而《新麻雀調》以《老麻雀調》為主體和延伸進行創編、演變,不僅供白族人民在日常生活田間地頭、家庭聚會、廣場等主要活動場所進行自娛自樂演唱,且逐漸發展為以舞臺表演為主要呈現內容的獨立民歌表演曲目。隨著現代音樂的多元化發展需求,《新麻雀調》也在大理各類大、中、小學校的專業或非專業的音樂表演中生根發芽,成為學校歌舞表演、聲樂演唱、學生音樂會的重要聲樂選曲。
筆者最早接觸大理白族小調《新麻雀調》是在初中就讀云南省大理市挖色中學的一次校文藝晚會上,當時被該校的音樂教師李紅萍演唱此歌時極富感染力和表現力的音調所吸引、打動。李紅萍老師演唱時那純樸、生動且極具白族韻味的演唱和表達,至今回想起來仍記憶猶新、別具一格。這也是筆者高中進入藝術特色音樂班,將大理白族小調《新麻雀調》作為聲樂學習的常備練習曲目和演唱曲目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讓筆者實實在在地領略了白族小調《新麻雀調》的歌曲魅力和藝術價值。下面筆者就以多年學習和演唱大理白族小調《新麻雀調》的實踐對此曲的音樂形態展開探究。
一、生活化
白族小調作為白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常客”,承接了白族人民在辛苦勞作之余的情感需求,形成了白族日常民間創作的人文瑰地。如《栽秧歌》,每逢插秧季節,為了激發勞動熱情,白族人民便在此時開展栽秧音樂勞動競賽的民俗活動。[2]以詼諧逗樂、諷刺懶漢的歌唱內容“教育”于人。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白族小調還有很多,比如《放羊調》《祭祀調》《上墳調》等,這些大理白族小調都是白族人民在日常生活勞作中表達自我、總結日常創作而成的白族小調。本文探究的《新麻雀調》就是大理白族小調中典型的代表作之一。
生活化語言鮮明,形象簡明生動。麻雀作為我們日常生活中極其常見的鳥類,此曲唱詞創作設計以“麻雀”為載體,將麻雀和人在生活中的“有意”“無意”接觸與互動進行取材并展開創作。歌曲第一段以動物“麻雀”的身體構造突出介紹麻雀的直觀外在形象,以此靜態形象引出歌曲第二段中白族女性勞動時人物形象與麻雀捕食之間的有趣“互動”。歌曲第三段作為終止段落將“麻雀”的外在靜態形象進行動態形象的轉變、升華,麻雀的聲音形象同時也從無聲靜態直接推到有聲動態,將麻雀的動作和叫聲展現得可謂“惟妙惟肖,引人聯想”。曲終以麻雀的叫聲作為歌曲結束的終止引用,亦十分巧妙有趣,將麻雀嘰嘰喳喳的喜動形象展現無余。
大理白族常用語言為白語和大理地方方言(漢語),此曲歌詞使用了大理地方方言。大理白族民歌小調《老麻雀調》三個樂段的歌詞均是生活化話語的直接運用。如第一段歌詞直觀介紹麻雀的外在形象:“一個麻雀,一張嘴,一個頭,兩只眼,兩只翅膀,兩只腳,一條尾”。第二段歌詞依舊沿用日常生活話語,描述了麻雀在妹妹舂米時偷食的生動畫面:“麻雀飛在碓窩里,一個妹妹來舂米,三碗谷子舂完了,才出半碗米。”第三段歌詞將口語化歌詞貫穿到底,把麻雀飛在鼓樓上的肢體動態和聲音動態活靈活現:“麻雀再飛到鼓樓上,頭一翹尾一甩,腳一扒,眼一眨,這個居兒,那個哚兒,居哩咯兒勒麻居哚兒,嘚兒。”除歌詞的主唱詞外,歌詞中加入了極具大理地方方言特色的方言慣用襯詞,襯詞在樂曲句子的句頭、句中、句尾都有大量出現,主要集中在句中和句尾。襯詞發音主要遵循大理地區的地方方言,保持歌詞內容的生活化氣息。例如,“那,那哈,來支,是,咿喲,哎呀”,這些襯詞的運用將生活口語直接搬到了歌唱作品中,可謂“藝術源于生活,忠于生活”。最后一段后半部分幾乎都是以襯詞填滿,襯詞在此部分更像“反客為主”的主唱詞。其中“麻雀”的自然啼叫,是自然生活的真實再現。
二、語言化
白族民歌中“重詞輕曲”的現象較為突出。[3]這種由來已久的“重詞輕曲”現象,決定了白族民歌創作和演唱時的白族語言傾向特點。有關聲樂作品中詞曲創作先后、輕重的利弊問題一直是歌曲創作的常見論題。在白族歌曲的創作上,筆者認為白族歌曲詞曲創作的先后、輕重極大地關聯著白族音樂作品風格、特色的架構與形成。其中,大理白族小調《新麻雀調》的歌詞創作便是白族歌曲“重詞”典型代表。
白族民歌創作基于曲調與語言的契合。白族歌曲在演唱選曲上一般選用白族固有的“山花體”歌詞結構的民歌旋律,主要是為了配合白族民歌長期慣用的“山花體”歌詞,方便歌唱者依曲編配符合語言押韻的即興創編需要,主要出現在白族重大的民俗對歌活動環節。例如,大理白族地區每年農歷三月十五至二十一日的“三月街”,每年農歷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初一的“石寶山對歌會”,每年夏歷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的“繞山林”等對歌會。在對歌會上,前來對歌的白族人民便會使用開唱者選用的符合“山花體”歌詞結構的固定白族民歌旋律,進行相應的“山花體”歌詞結構即興歌詞創編,以此來展開情感交流、技藝切磋、競技爭冠。對歌會大多是以競賽為主,在對歌過程中哪一方歌詞即興創編沒有押韻也就自動認輸,一直被白族人民敬推的“歌王”“歌后”稱號也就無緣競稱了。除押韻外,對歌環節中需要歌者對大理地區常用語白族語言和大理地方方言的遣詞造句進行深入研究,因為大理白族民歌的旋律多依據白語或地方方言語調進行創作。[4]綜合白族“對歌”的表達方式,決定了歌者的歌詞創編既要符合白族語言或大理地區漢語方言的語調進行即興創編又要擅長“山花體”歌詞結構進行押韻,且在此基礎上還要體現對歌者用詞內容表達的優劣,綜合以上對歌條件也間接形成了白族歌曲中“重詞”的普遍現象。通過了解白族民歌的形成元素和發展歷程,筆者結合實踐熟讀熟唱大理白族小調《新麻雀調》的譜例,從中發現詞曲相互依托、相互關聯,可謂曲調與語言的巧妙契合,這與大理白族的民歌形象達成高度一致。早期白族歌曲的創作“胚胎”形成了白族特有的音樂主體風格,要延續和發展白族民歌音韻勢必要求在白族歌曲創作和演唱上要合理地保留和借鑒白族民歌創作的語言化。白族民歌創作的語言化引申發展形成了音樂的白族化,相反地,白族化又基于語言化。大理白族小調《新麻雀調》以《老麻雀調》為基礎進行創編改寫而成,故筆者推斷《新麻雀調》的創作先后、輕重是“先詞后曲”“重詞”。因此,大理白族小調《新麻雀調》的演唱必須基于“語言化”進行白音白感的揣摩和塑造,將語言作為此歌演唱表達的基礎核心需求。
白族民歌演唱遵循曲調與語言的融合。本文上段論述的白族民歌創作基于曲調與語言的契合體現了創作者依托“詞”為核心,以致白族民歌創作詞曲的高度契合,故而演變、形成了白族民歌演唱詞曲的語言化,即演唱遵循曲調與語言的融合。歌者演唱一首聲樂作品時,首先需要解讀歌譜、作者意圖、音樂背景等核心要素,其中尊重歌曲詞曲創作目的和意圖尤為重要。基于白族民歌歌詞創作的“山花體”固有歌詞結構,曲調旋律創作依據白語或地方方言語調創作的習慣,演唱白族民歌的歌者需服從歌曲語言的地域語言需要,遵循白族語言或大理地方方言的發音、咬字、語調等特點。通過對詞曲語言關系和連接的準確理解和運用,從而獲得白族民歌在演唱時曲調與語言的融合。大理白族小調《新麻雀調》的詞曲與語言關系是明朗的,歌詞的創作直接運用了大理地方方言的日常生活口語,曲調大多是根據歌詞在大理地方方言中的聲調進行,使得《新麻雀調》具有大理白族音韻,同時又將白族生活實景進行有趣的還原和升華。
演唱服從“說”與“唱”的結合。大理白族民歌創作的“語言化”氣質,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白族民歌創作者精通并運用白族語言或大理地方方言,也決定了歌者歌唱表達的“重”語言性、語調化、咬字特點等個性需求。作為一名專業的歌者,如果不能將不同作品加以區分演唱、表達,而是一味地追求“技巧為上,千篇一律”的聲音表現,則失去了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地域歌唱表達的特殊意義。綜上所述,根據大理白族民歌小調《老麻雀調》所使用的大理地方方言為歌詞,歌者需做足唱前地方語言學習準備,特別是非大理地區的歌者演唱此類少數民族特色歌曲,應將語言作為重要的歌唱門檻進行突破練習。《新麻雀調》由于將大理地方方言的生活口語進行直接運用,使歌曲具備了說唱結合的突出特點和特性。演唱大理白族小調《新麻雀調》時建議先聽讀,再者說,勤練習,善分辨,找到規律,掌握語感,形成語韻。曲調上,先唱后帶,即先唱準、唱熟旋律,再循序帶入歌詞,歌詞進入后應以不失語感、語韻為歌唱練習基礎,最終以達到“說”“唱”結合的白族歌唱聲感聲態為目標。為求歌曲演唱時的韻味純正、濃厚,歌者也可“唱后再說”“說后再唱”,達到此曲說唱結合的歌感需求。
基于白族“白音白韻”的歌感表現,使得白族民歌自然地與其他民族民歌區別開來,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各民族、各地區音樂交流的語言差異和個性不一。大理白族小調《新麻雀調》“白音白韻”的歌感表現,實際上是白族語言在歌唱上的運用和表現。《新麻雀調》在大理白族地區得以廣泛流傳、經久不衰的核心命脈主要來源于語言的基礎力量和延伸發展。如果演唱時不再突出表現語言的固有特征、個性表達等,則失去了“白音白韻”的歌感,同時也失去了歌曲演唱的情感認同和表達必要。這一點,很多少數民族音樂有著相似的感觸,“同”與“不同”的語言、文化、生活習性等造就了自己民族的別它性。需要肯定的是,少數民族固有的語言特點和歌詞創作慣用結構方式等差異,是眾多少數民族音樂區別于它的實質原因。
三、結束語
民歌,在人類各民族、各地區的音樂發展歷程中,通過不斷的創作作品的形式將所處時代的社會現狀進行了描述、總結和提煉。我們將藝術作品視作“時代的縮影”“民族的名片”,它保存了人們對未知過往的社會畫面,喚起了人們對某個民族、某個時間的時代記憶,藝術作品的魅力和價值也因此得以體現。白族民歌亦是如此,大理白族民歌小調《新麻雀調》就是白族人民過往生活實照的縮影。它既是白族人民在生活中的獨立創作,也是白族人民在社會生活中用集體智慧創作而出的白族民歌結晶和典型佳作。本文通過論述大理白族民歌小調《新麻雀調》與生活和語言之間的內在關聯、相互作用,拋出了白族民歌小調的一些共性特征和個性特點。同時,我們也可以通過大理白族民歌小調《新麻雀調》窺探到白族的社會實狀,認識白族音樂與白族生活、語言的內在連接,使人們更好地理解白族歌唱作品。
參考文獻:
[1]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編,楊政業主編.大本曲簡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2]李建英.試論白族民歌及演唱法[C]//大家文學雜志社.民族文化與文化創意產業研究論叢(第三輯).云南出版集團公司,2011:373-388.
[3]楊曉勤.論白族民歌中的“重詞輕曲”現象[J].民族文學研究,2021,39(01):80-88.
[4]李佳芯.大理白族民歌《麻雀調》的音樂風格及演唱探析[D].四川音樂學院,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