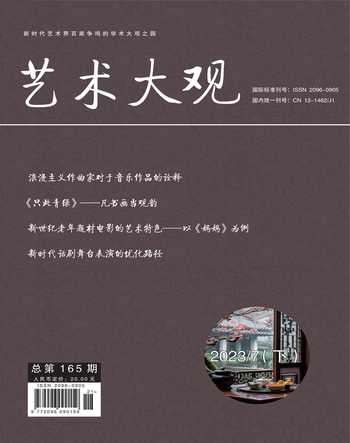新世紀老年題材電影的藝術特色
丁梓懿
摘 要: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國老齡化進程的加快,老年群體的比例不斷上升,老年群體的生活困境和內心情感狀況也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本文主要針對進入21世紀后涌現出的老年題材電影的藝術特色進行對比分析,并以電影《媽媽》為例進行闡述,進而總結出老年題材電影的藝術特色。通過梳理新世紀老年題材電影的發展和藝術特色,為未來的老年題材的電影創作提供新的方向。
關鍵詞:老年題材電影;老齡化
中圖分類號:J9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3)21-00-03
一、新世紀老年題材電影的發展
進入21世紀后,在面對全球老齡化的現實語境下,老年題材電影的創作進程也大大加快。中國在1999年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隨著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老年人的生活困境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重視,也使得許多創作者將創作視角轉向老年人,因此在進入21世紀后老年題材電影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實現了大幅度的提高。老年題材電影在商業價值和藝術價值之間不斷尋求平衡,強化其藝術特色和人文關懷。
進入21世紀后,老年題材不僅僅只是一個符號象征,而是通過對老年群體的深度挖掘,去思考關于死亡與人生價值等深刻的問題。21世紀以來陳國星的《聊聊》、吳兵的《苦茶香》、 馬儷文的《我們倆》、哈斯朝魯的《剃頭匠》、 王全安的《團圓》、張揚的《飛越老人院》、 張濤的《喜喪》、張躍平的《大寒》、張唯的《空巢》、高子彬的《殺出個黃昏》、楊荔鈉的《媽媽》,都是不同代際的導演圍繞不同時期下老人的生存環境和困境而創作的作品。盡管在創作主題上不盡相同,但是老年題材電影有著共同的藝術特色,同時都通過老年題材電影表達了對于老人這一社會群體的人文關懷,為人們打開了一個審視不同時期老年世界的窗口與途徑。
二、新世紀老年題材的藝術特色
(一)現實主義藝術風格
“一切文藝都關乎‘人,無論是劇情片或是紀錄片在本質上都是通過一定的媒介手段來說明動作環境、敘述事件、貫通結構,更主要的是塑造相對獨立完整的人物形象體系和個性形態,以真實可感的具象去喚起受眾的審美感應和情感體驗。”[1]現實主義風格,顧名思義便是貼近現實生活,反對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旨在反映真實生活,而老年題材電影就是貼近老年人的真實生活,去反映他們的生存現狀。
老年題材電影的現實主義風格可以從多個方面體現出來,首先就是人物形象的設定,《我們倆》中孤獨的老人金雅琴、《飛越老人院》中渴望獲得兒子原諒的老葛、《媽媽》中為了女兒堅強生活的蔣玉芝,這些人物形象都十分貼近真實生活,仿佛就是生活在觀眾身邊的人。其次,故事發生的場景,老年題材電影的情節往往都發生在家中。老年人由于年齡的原因,導致行為能力都退化,因此家就是老年題材電影最常選擇的故事發生場景。而家中發生的故事本身就貼合觀眾的生活,更容易讓觀眾產生熟悉感,從而引發共鳴。在電影《媽媽》中,第一重主題是母愛,85歲高齡的母親為了患病的女兒,主動從被照顧者轉變為照顧者。影片的第二重主題便是死亡這一永恒話題,尤其是老年人這一特殊群體,他們離死亡很近,甚至每天都在和死神賽跑。影片中父親的死亡對于馮濟真的影響、蔣玉芝與馮濟真面對即將有可能到來的死亡。影片的第三重主題便是引發社會對阿爾茲海默癥老人的關注,根據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國內超過60歲的老人總數已經達到2.5億之多,其中患有阿爾茲海默癥的老人更是有1500萬人以上,并且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因此《媽媽》這部影片也是貼合社會熱點話題,讓更多人關注到這一特殊老年群體。
(二)老少配的人物組合
老少配這一人物組合總是出現在老年題材電影中,電影《我們倆》中獨居在北京四合院的孤獨奶奶與因上學碰巧租了老人房子的年輕學生之間的老少配組合;電影《孫子從美國來》中老楊頭和洋孫子布魯克斯之間的老少配組合;電影《過年好》中老李和李羊朵以及李羊朵和朱莉之間的老少配組合;電影《飛越老人院》中老葛和孫子之間的老少配組合;電影《殺出個黃昏》中田立秋和被雙親拋棄的屈紫瑩之間的老少配組合。這些老年題材電影中的老少配組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有著血緣關系的家人之間的老少配組合,另一種則是沒有血緣關系最終卻勝似家人的老少配組合。之所以老年題材電影中經常出現這種人物組合也是由于老年題材電影的主題所導致,老年題材的電影主題往往圍繞著代際矛盾展開,而代際矛盾離不開年輕人,因此老少配的人物組合是老年題材電影中最常見的人物搭配。
電影《媽媽》中其實存在兩種老少配組合,一種是母親蔣玉芝和女兒馮濟真之間有血緣關系的老少配組合,另一種是女兒馮濟真和問題少女周夏之間沒有血緣關系的老少配組合。電影《媽媽》中在人物設定上具有創新性,編劇不再將老少配組合設定為年老的父母和中年子女之間的矛盾,而是將兩位主人公的年齡都放在老年群體中,再加上馮濟真無兒無女、一生未婚的人物設定,讓養老問題不再只局限于母親身上,而是女兒和母親兩個人同時面臨著養老問題。據調查顯示,如今社會上不婚不育的女性比例正逐年上漲,因此這種人物設定也暗示了未來不婚不育群體將會面臨的困境。已經85歲高齡的蔣玉芝面對65歲的女兒馮濟真被確診為阿爾茲海默癥后,毫不猶豫地再次為女兒撐起了一片天空,展現了母親的無私與偉大,深化了母愛這一主題。第二種老少配組合,一方面讓馮濟真這個人物實現了自我救贖,另一方面周夏與她的女兒就如同蔣玉芝和馮濟真一般,是母愛的一種延續。馮濟真一直無婚無子,自我封閉的原因在影片中并沒有直接交代給觀眾,而是通過馮濟真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從她的話語中才能得知她將父親的死都歸咎到自己的身上,因此一輩子沒有出嫁,活在愧疚中。當馮濟真面對周夏扒竊的栽贓和入室搶劫時,她都選擇了保全這個年輕的女孩,這也就是為什么周夏在快餐店時對馮濟真說:“也許是我成全了你呢”。馮濟真幫助周夏的原因,除了不想讓周夏未來和她一樣陷入無法悔改的境地,更像是對于自我的一種救贖,她希望周夏能夠改過自新,從某種層面上講是代替自己彌補錯誤,所以周夏和馮濟真的相遇就是一場雙向的救贖。三年后,改過自新的周夏帶著自己的女兒再次來到馮濟真家時,她就像一直存在在這個家庭中的一員,幫她們大掃除,為這個家帶去了生機,同時周夏和她的女兒也象征著一種愛的延續。
(三)淡化敘事沖突
電影敘事節奏是指單位時間內矛盾沖突的密度所營造的或快或慢的敘事風格。它體現著導演的創作意圖,影響著觀眾的情感與情緒。[2]淡化敘事沖突會造成敘事節奏緩慢:鏡頭語言較為委婉,節奏平緩。老年題材電影由于老年人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其電影敘事節奏是緩慢的,而緩慢的電影節奏使得影片的矛盾沖突會相應地減弱,敘事的重點不再是激烈的矛盾沖突,而是轉向對細節的刻畫。在老年題材電影中,情感的爆發往往是通過一件件小事的累積,而不是多么強烈的矛盾沖突。在許鞍華的電影《桃姐》和《天水圍的日與夜》中都體現出了淡化敘事沖突的藝術風格,這種藝術風格使得矛盾沖突得到了消解,而這種對生活細節的大量描繪和安排也拉近了電影和觀眾之間的距離,讓觀眾更容易在后續產生情感共鳴。電影《我們倆》中更是將淡化敘事沖突做到了一種極致,在看完全片后甚至講不出影片里哪件事最重要,因為每一件都是生活中瑣碎的小事。但這并沒有減弱影片的情感表達,反而將所有情感都融入日常生活的細節中,讓最后的情感顯得更加厚重、深沉。
淡化敘事沖突體現電影語言的多個方面,具體包括鏡頭語言、音樂、人物行動等。在電影《媽媽》中一開場就是媽媽蔣玉芝在女兒馮濟真的陪伴下進行體檢的一組鏡頭,在這組鏡頭中,平均鏡頭時長是5s,按照好萊塢的鏡頭語言節奏來看,幾乎是好萊塢平均鏡頭時長的兩倍,開頭這種較緩慢的影像節奏,也為整個影片奠定了一個總基調。并且在短短12個鏡頭內,運用了多個搖鏡頭和移鏡頭,不僅起到了放慢鏡頭節奏的作用,也增強了影片真實感。整個影片除了周夏帶著自己的女兒來看望馮濟真這一段戲中采用了節奏感較強的背景音樂,全片都是舒緩、抒情的背景音樂,音樂的節奏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也與敘事節奏相吻合,也從側面體現出了影片緩慢的敘事風格。整個影片最大的矛盾沖突發生在馮濟真被確診阿爾茲海默癥后,病情從輕到重不斷發展,病情從記憶模糊、幻覺、迷失、妄想、暴躁,逐步發展到暴力、失語、失認,整個過程是循序漸進的,因此影片也沒有強烈的敘事沖突,而是通過不斷的細節鋪墊,達到最后情感的迸發。這種淡化敘事沖突的創作方式可以讓老年人的生活情感等細致地通過鏡頭呈現出來,加強情感的鋪墊,有利于情感的最終抒發。
(四)意識流片段參與敘事
電影中意識流片段是在一個寫實的時空里構建一個超現實主義的主觀心理世界。[3]不同于傳統的意識流電影,意識流片段參與敘事是指通過一些意識流片段去表達人物的潛意識和主觀情緒,而這些意識流往往通過人的幻覺、夢境、想象等途徑來實現。這些意識流片段是服務于人物的現實時空,借用意識流片段這一形式來幫助人物實現現實中所不能實現的愿望以及滿足人物情緒的抒發,可以說是人物幻想與現實博弈的一種表現。在電影《媽媽》中,馮濟真埋藏在心里多年的心結就是通過阿爾茲海默癥發病后的自身幻想展現出來的,可以說馮濟真和父親的感情線就是通過意識流片段表現出來的。馮濟真在全片中出現了三次幻覺,第一次是看到年邁的父親和年輕時一樣在家中和學生討論考古工作,第二次是看到年邁的父親站在家里的院子里抽煙,而第三次幻覺更像是回憶的重現,她看到了小時候一家三口在家里溫馨地慶祝生日的樣子。通過馮濟真的三次幻覺,讓觀眾發現了她埋藏在內心的對父親的愛與思念,也為了后面父親的死之所以成為她一生心結做出了鋪墊。
精神分析學中對夢境的研究是符號化的,夢境中出現的元素都具有其背后的隱喻或預示。[4]夢境常常出現在老年題材的電影當中參與敘事,幫助老年人去完成無法實現或者潛意識里內心的鏡像投射,常常和回憶、現實、夢想等元素聯系起來。夢境參與敘事這一形式早在幾千年前的戲劇中便有體現,如《西廂記》《竇娥冤》《南柯記》。夢境出現在電影中參與敘事起到的作用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由于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和受壓抑,通過夢境展現對現實生活與人生的象征與隱喻,第二類是將夢境作為一個實現某件事、達成某個目的的工具[5]。在電影《媽媽》中,馮濟真最終在夢境中解開了多年以來的心結,這個夢境不再是她一個人的幻覺,而是母親和她一起入夢完成的。在夢境中馮濟真終于挽住了父親的胳膊,年邁的父親和母親陪伴在她的左右,她們用著她們之間獨特的表達愛的暗號肆意宣泄著壓抑多年的思念與愛。馮濟真最終通過夢境這一形式實現了與父親團聚的這一愿望,也終于原諒了自己曾經的錯誤。這個夢境彌補了馮濟真現實中的遺憾,是她愿望寄托的最好表達。
三、老年題材電影的新方向
老年題材電影具有鮮明的藝術特色,但是這些藝術特色也使得老年電影的受眾范圍較小。大多數觀眾更加偏愛快節奏、敘事沖突激烈的電影,但是老年題材電影由于老年群體自身的特點,不能完全為了迎合觀眾而去改變自身的藝術特色,否則老年題材電影也失去了自身的獨特性。那么如何在保留老年題材電影自身的藝術特色的情況下,吸引更多的觀眾成為現在老年題材電影最需要解決的問題。首先,可以采用群像式敘事表達,目前的老年題材電影,大多數都是圍繞某一個家庭、某一位老人展開,這樣雖然可以充分地挖掘某一個人物身上的故事,但是電影的趣味性就會受到影響。如果將單個主人公變成多個,而每個人都具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家庭類型,那么就可能產生多種不同類型的矛盾沖突,也就大大增加了情節的多種可能性。其次,讓老年題材電影和類型片進行結合,張揚的《飛越老人院》就是老年題材與公路片的一次大膽結合,并且這部片子也取得了不錯的反響,為老年題材電影的創作提供了新思路。除了公路片,喜劇片這一類型也是老年題材電影適合結合的方向。現在很多電影都呈現出泛喜劇化特征,無論是純喜劇片還是披著喜劇的外殼的悲劇,都很受觀眾喜愛。老年人常常被人們稱作老小孩,因此在他們身上可以挖掘的笑點本身就很多,因此也就更加適合喜劇片這一類型,再加上巧妙的情節設置,可以通過喜劇將老年人的困境展現出來,這種笑中帶淚的設置,更能打動觀眾,達到情感共鳴。未來老年題材的電影將隨著中國老年化進程的加快,受到越來越多創作者和觀眾的青睞,老年題材電影也會在不斷的創新中煥發出新的生機。
四、結束語
老年題材電影具有自身獨特的藝術特色,如現實主義藝術風格、老少配的人物組合、弱化敘事沖突,以及意識流參與敘事。這些藝術特色使得老年題材電影具有自己的影像風格,但是同時也讓老年題材電影的受眾變得有限。未來老年題材的電影可以通過群像式敘事表達和與類型片結合這兩種方式,來增強電影的觀賞性和趣味性,在最大限度保持自身藝術特色的前提下,為老年題材電影注入新的生機。
參考文獻:
[1]朱旭輝,宋子揚.新時期老年題材電影的類型構建、空間話語與鏡像隱喻[J].電影文學,2021(21):35-39.
[2]邵雯艷.論紀錄片人物的形象建構[J].社會科學家,2013(03):126-129.
[3]蔣東升.矛盾沖突編織中的電影敘事節奏[J].電影文學,2019(06):3-7+119.
[4]段鵬,孫浩.幻想與現實:論新世紀以來意識流在電影中的作用及展現方法[J].當代電影,2019(03):48-50.
[5]熊越.夢境在當代中國電影中的敘事策略[J].視聽,2021(04):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