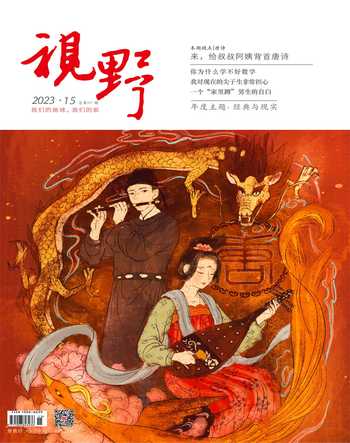生活的答案,在唐詩里
幽幽之默

詩必窮而后工
阿城曾說,每個時代的人都有絕境。他做了一個相對的補充:絕境是一個比喻,可能是任何你碰到的問題,你有這個能量、智慧和經驗穿越嗎?沒有,那就可能是絕境。這句話似乎過于絕對,但遇到的問題至少是一種困境。過去三年,很多人的生活都泛出一番寒意,生活似乎變得無法完全掌控。
我們哀嘆、我們焦慮、我們不甘,但內心深處也知道,困境是生活的常態:年輕時候總會感喟窮困,懷才不遇;中年常常遭遇變故或者病痛;老了總要面對親人朋友一個接一個地離去。而身處困境,人們常常不平則鳴,有一個成語叫“絕處逢生”,那新生的事物可能就是詩。
古代詩人都是如何用詩面對人生困境的?多病困擾之時,韋應物想念老友,他這樣寫:“去年花里逢君別,今日花開已一年。”元稹思念亡妻,留下千古佳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李白被赦免后乘舟東下江陵,寫下“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名句,但其中透露的喜悅背后,是詩人經過流放、拋妻別子的痛楚。
《全唐詩》的四萬八千多首詩,大部分都是羈旅行役的苦悶、求而不得的痛苦、對親人的悼念以及刻骨的相思,單純描寫快樂的詩句很少。正因此,古人總結道:憂憤出詩人、詩必窮而后工。
人生的詩意時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現實苦難的正視以及對它的超越之上。命運的沉浮,以及悲歡離合、生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這些人生的遭際,會讓詩人有感而發。千年前某人內心的一次漣漪,落在紙上成為詩句,被記錄被誦讀被流傳,引發之后無數代人的精神共振,余音裊裊,直到今天。
生活的詩意:雖然嘆息,總是輕盈
在古代,像“我要做一個詩人”這種提法,是不存在的。戰國的屈原、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蘇軾等等,大部分被我們稱為“詩人”的那些古人,他一生的主要身份都不是詩人,而是心懷抱負的士子、居廟堂之高的政客、夢想兼濟天下的文人。他們認為生命中有更重要的事,而這件事不是寫詩。
有時,他們并不活在詩意的“藝術真空”里,甚至要直面“有財有勢即相識,無財無勢同路人”的現實。在唐代詩人孟郊的小世界里,流露出一種現實的冷峻。孟郊在底層生活過,當他沒權沒勢時,常有人把他當作“路人甲”。韓愈因此對孟郊一直抱有同情:“人皆余酒肉,子獨不得飽。”
孟郊幼時喪父,中年喪妻,晚年喪子,屢試不第,貧困如影隨形,一生悲苦。但他并不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困境,能眼光向外,關注人間的疾苦。看到百姓生活艱辛的殘酷現實,他寫下悲天憫人的詩句:“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目睹貪腐的官吏對農民的繁重剝削,他痛心疾首地吟誦:“如何織紈素,自著藍縷衣。”
古代農民經常遭受繁重剝削,孟郊用詩記錄下了他們生活的艱辛。
他一生都在漂泊,“十日理一發,每梳飛旅塵;三旬九過飲,每食唯舊貧”。當他晚年當上縣尉,終于可以把母親接來同住時,飽嘗世態炎涼的他愈覺親情之可貴,于是用真摯的情感,給后世留下了“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的經典慈母形象,“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被歷代傳頌,直到今天還被揮灑在各種書法卷軸上。
孟郊不避諱內心的失意,用真切的生命體驗去寫詩。人生的各種際遇匯聚成了詩,詩是生活的副產品。
相比起孟郊,劉禹錫很早就踏上了仕途,他年少成名,二十歲中進士,三十歲就位極人臣。但他的后半生卻遭遇讒言、排擠和攻訐,一路被貶連州、夔州、和州等地,長達二十年。
面對苦難,不同于孟郊,劉禹錫一生樂觀曠達,堅毅剛強,更是用詩歌實現了對苦難的精神超越。盡管有數次被貶謫的遭遇,當遇到后起之秀白居易,他的詩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流露出欣喜與樂觀;因寫玄都觀桃花得罪權貴而被貶,但當再次奉調回京任職時,他還敢寫玄都觀桃花,一句“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盡顯韌性與傲骨。
他告訴我們,要豁然地看待世事的無常,“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但他又并非一味沉浸在前塵往事中,而是勸誡人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不必糾結于往事,就算遇到了痛苦與愁悶,生活還是要不斷向前。
而比起劉禹錫,王維又更進一步,把面對苦難的精神超越,上升到了禪的超脫與智慧。經歷了仕途風波后,他看透了官場沉浮,愈發感覺到人世的虛幻,因此對佛家的超脫有了更親切的體會,遂在輞川營造了一座別墅,隱居山林。
他愛描寫山林的“空”與“虛”,在他的詩里,世界總能顯現出原初的面目,幽靜且空靈玄妙。“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有時,甚至初升的月亮會驚動山鳥,它們在山澗里的鳴叫聲,安慰那被俗世侵擾的內心。
在禪的境界里,他找到了樸素自然的處事智慧,“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于是擺脫了世俗中的各種糾葛,體會到生命的自在與詩意。他過的是半官半隱的生活,好比一個挑夫,一個擔子里裝的是喧囂,另一個裝的是隱逸。
正是從他的詩中,我們學會了如何與一個喧囂的外在世界打交道。王維隱居山林的行為,以及隨緣自適的心境,提供了生活的另一種答案,深深打動了內卷的現代都市人。
生活的答案,在古詩里
詩人們生活的副產品,被不斷傳頌后成為經典,直到今天仍是激勵后世的精神財富。快一百歲的葉嘉瑩先生歷經戰亂,轉蓬萬里,半生漂泊,她說她的往事總是“隨命運撥弄和拋置”。
她的人生,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故事。1948年,二十四歲的葉嘉瑩南下結婚,不久跟隨丈夫去了臺灣。抵臺第二年,丈夫便入獄,葉嘉瑩也一度被捕和接受審訊。她帶著吃奶的女兒,睡過親戚家的走廊,寫下“剩撫懷中女,深宵忍淚吞”來表達艱辛。
四年后,丈夫出獄,失去了工作,她靠在中學教書的收入養活全家。一次下課后,她在等公車時,由古文里的“云母車”想到李商隱的詩:“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經歷了患難,她和詩人有了心靈上的共鳴,體會到那種孤獨、寂寞和悲哀。回到家,她又是那個擦地板,架著竹籠在炭火上烘烤尿片的女子。
1976年,五十二歲的葉嘉瑩收到大女兒和女婿車禍去世的消息。葬禮后,她回到家里,接連數十天閉門不出。她在《哭女詩十首》里,寫“痛哭吾兒躬自悼,一生老瘁竟何為”,“遲暮天公仍罰我,不令歡笑但余哀”。她回到學校工作,見到同事,最多眼圈一紅,就低頭走過去了。是古詩詞,把她從人生苦難中拯救了出來。
“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禪不借隱為名”,她一次次告誡學生,要以悲觀的心情過樂觀的生活,以無生之覺悟,為有生之事業。她從那些偉大的詩歌、偉大的心靈中汲取力量。葉嘉瑩先生說,古詩詞中歌詠的生命、感情、理想、志意,千古而下,只要是有感覺的人,就能與詩人感同身受。她因體會到古典詩詞里那些美好高潔的心靈而感動,而詩詞的寫作、研讀,也成為支持她走出低谷的力量。
就那種“面對困境也依然浪漫”的氣質而言,可以說,詩從未在我們心里消逝過,它的精神一直都在。只要生活在繼續,那么就會有無數個與詩歌“同頻”的時刻。兩年前日本援華防疫物資上的一句唐詩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為許多人帶來了寬慰。而詩歌總是常讀常新,在不同的人生階段與時代背景下,詩都能給人不同的感覺。
最近,抖音聯合南開大學文學院、中華書局推出了短視頻版《唐詩三百首》,葉嘉瑩先生也通過短視頻的方式,與社會公眾一起讀詩、品詩,體會唐詩的微妙與幽深,溫故而知新。
作為中國古代詩歌的集大成者,唐詩塑造了中國人的語言和審美,也構建了我們的精神世界。唐詩所傳遞給我們的是:有些人生困境千年未變,早在一千多年前,詩人們就為后世留下了參考答案,只等待與我們的人生契合,重新賦予我們力量。
當人生處于某種糾結時,我們會想起“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李白《把酒問月》),它提示我們,放下糾結,事情的格局終會有所改變;當精神疲憊時,我們會想起“東山高臥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李白《梁園吟》),這是對“躺平話語”最溫柔的強心劑;而當再一次被“事業”打敗時,我們或許應該記住:“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杜牧《題烏江亭》)
今天的人生起承轉合,與一千多年前的唐詩仍能絲絲入扣。古人感發的生命體驗,穿越深遠的時間阻隔和濃重的歷史風煙,仍舊能與今人心心相印。今人亦能透過唐詩讀到古人詩意的魅力,熏陶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
詩歌從未遠離生活,生活的答案就在詩里。唐朝的詩人有答案,先生們有答案,你自己從唐詩中,也能找到答案。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