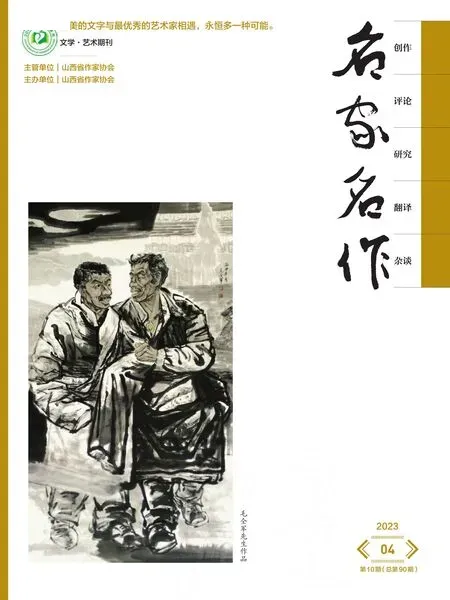認知語言學視角下的新修辭學及其運作
楊維鈺
一、引言
以肯尼斯·伯克為代表的新修辭學一直在當代美國修辭學中占主導地位。美國對伯克的研究始于20世紀20年代,圖默(1924)最早開始對伯克的文學作品進行研究,而后海門和霍克馬斯分別于1948年和1952年發表了早期研究伯克的著名論文(鄧志勇,2011:17)。由于伯克的思想博大精深,在西方引發眾多學者的狂熱研究。美國甚至于1984年成立研究會,建立伯克研究網站,開辦伯克研究雜志。國外對伯克的研討系統全面,主要圍繞伯克的元修辭學思想、伯克與其他哲學流派的相關性和伯克修辭理論中的“同一”及“五位一體”三方面展開。近年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人將焦點轉向了伯克理論在文學批評等領域的應用。
我國最早對伯克進行撰文介紹的是顧曰國,而后胡曙中和溫科學在其出版的專著中論述過伯克理論(鄧志勇,2011:21)。近年雖有很多學者對伯克思想展現了興趣,但全面且有深度的剖析不多,大多局限于“同一”和“五位一體”,忽視了伯克修辭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其實伯克理論吸收了眾多學科成果,若不堅持跨學科原則,很難透徹地把握該體系(鄧志勇,2011:23)。基于此,本文重點研究伯克新修辭理論中的跨學科性,從認知語言學視角出發,探析新修辭學的核心概念及運作原理,以彌補國內研究的短板。
二、新修辭學與認知語言學的內涵闡述
(一)新修辭學的發展歷程及構架
新修辭學指20世紀30年代在歐洲大陸及美國產生并在60年代盛行的修辭學思潮。韋弗等新修辭學家緊密聯系社會,從多領域汲取營養,使其成為一門有效使用話語的綜合性語言理論(胡曙中,1999:1)。若要給其下定義,可說它是對可利用的明智處理社會問題的話語手段的尋求,可以促進和諧幸福(鄧志勇,2016:41)。
公元前7世紀,古希臘人就學會運用演講以勸說,但作為學問的修辭學的奠基之作是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而后,西塞羅等傳承和發揚羅馬希臘時期的修辭思想,使其在體系形態上達到頂峰。到了19世紀,西方修辭學主戰場由英國轉向美國,修辭學淪為寫作教學。20世紀30年代,理查茲對其衰落感到不滿,將修辭學視為哲學學科,提出研究意義的語境理論,但他雖意識到意義受語境制約,卻未真正觸及語言本身的修辭性(鄧志勇,2015:16)。之后伯克開創新修辭學,提出具有解構意義的認識論方法,將修辭學融入社會學中,為美國修辭學邁上興旺之道做出了卓越貢獻(鄧志勇,2001:93)。伯克新修辭學有三大組成部分:動機語法理論,它闡釋了語言戲劇要素間的邏輯關系;動機修辭學理論,它闡釋了修辭者的戲劇性話語運作的修辭策略;詞語理論,它不僅論述了語言本身的特征,還從宏觀層次概括了戲劇性修辭話語的運作(鄧志勇,2016:41)。它們彼此交融,從不同角度對修辭行為進行了考量。
(二)認知語言學的定義及基本觀點
術語“認知語言學”首先出現于1971年,指真正對大腦中的語言進行的研究(Lamb,1998:381)。但如今所說的認知語言學常指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迅猛發展并于21世紀漸成主流的新興語言學流派。認知語言學歷史較短,尚未形成完整的系統,也未形成嚴密的定義,但據王寅(2006:11)所說,可將它視為堅持體驗哲學觀,以概念結構和意義研究為中心,著力尋求語言事實背后認知方式的跨領域學科。和新修辭學一樣,認知語言學不是一種單一語言理論,而是一種研究范式,由多種理論匯集而成,通過對語言結構的分析來推測人類思維中概念內容的特點、解釋語言現象背后的認知理據(王寅,2006)。它主張從人類一般認知能力研究語言,哲學基礎是體驗哲學,它的構建基于“心智體驗”“認知的無意識性”及“思維的隱喻性”三大哲學觀點(王寅,2002:84)。
三、新修辭學中的認知語言學思想
雖然新修辭學和認知語言學在研究目的、內容及路徑上都存在差異,但新修辭學中很多重要概念及運作原理明顯與認知語言學思想,尤其是體驗哲學觀掛鉤。
(一)新修辭學的哲學基礎之人性論
新修辭學駁斥傳統語言學“語言是工具”的觀點,認為語言是建構社會現實的必需物,但語言畢竟是人的語言,人的動物性及因語言中的否定而產生的價值觀特征決定了人的行為。伯克(1935:184-185)認為,“人身上好像有一種持續按照其特征形象用語言來塑造自己的趨勢”,因此人的體驗孕育了人的修辭行為。每個人都在世界這個等級社會里尋找位置,有等級就有隔閡,要求人們必須使用符號溝通去消除隔閡。伯克(1950:40-43)這樣定義修辭:“修辭……是用作為符號手段的語言在那些本性上能對符號作出反應的動物身上誘發合作。”“誘發合作”在這里不僅暗示了社會成員間隔閡的存在,還反映了人們達成共識的潛在可能性。在《永恒與變化》(1935)中,伯克就指出,人具有普遍心理特征,正是這些永恒特征決定了人與人進行言語交際的可能。基于人的本質特征,包括體驗性特征,新修辭學斷言:“哪里有勸說,哪里就有修辭;哪里有意義,哪里就有勸說。”(Burke, 1950:172)
從前文的定義中可看出,認知語言學本身就以體驗哲學觀為基礎,認為人類對世界的體驗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認知系統才是語言的主要成因(王寅,2006:581)。認知語言學家堅信語言是體驗和認知的結果。我們的認知推理均建構在我們與客觀世界的交互中,因此新修辭學和認知語言學在“人之體驗”思想上有很大交集。
(二)新修辭學中的“動機”與戲劇五要素
新修辭學認為由象征手段誘發或進行的活動都涉及動機,因此都是象征行動。當人們用象征行動對環境作反應時,便不可避免地顯露“動機”,表露自己對現實世界的闡釋框架(鄧志勇,2011:29)。語言滲透主觀意志,我們對語言的每一次使用都暗指態度,而態度體現行動,哪怕最簡單的事實陳述也隱含修辭動機。
由于語言是我們對場景的策略式反應,面對同一事物時,源自不同動機及體驗,每個人也有不同表達。伯克認為要想完整描述事物,必須涉及五個基本戲劇要素:場景、行動、行動者、目的和工具。它們既彼此獨立,又在事件中統一(鄧志勇,2011:73)。另外,這五要素在不同問題中還可相互轉化,表現在對同一事件,不同人對其體認不同,凸顯的戲劇要素不一樣及要素間的關系可以轉化,如一個動作者的行動可變成另一動作者的場景。通過分析修辭者對五要素的不同搭配,我們就能窺探他的“動機”及體驗,即他如何用語言闡釋當前修辭情景。從這點看,新修辭學的戲劇五要素及“動機”理論也與認知語言學中“不同個體由于各自不同的身體經驗和認知水平,對一件事物的評價也不盡相同”的體驗觀及其重要組成部分——認知語法——關于注意凸顯的理論(同一情景由于不同的假設或期待、不同的立場或態度,會在大腦的認知語境中形成不同的意象,產生不同的表達式)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新修辭學中的“同一”修辭策略
有了動機,人們又如何具體實施以達成消融效果?新修辭學中關于修辭運作的核心原理“同一”也包含了豐富的體驗認知思想。修辭者在實施“同一”時總以聽眾的體感為參照,使讀者設身處地地感受修辭者的經歷,最后與說客認知相同,便自然取得“同一”。
在伯克的修辭體系里有三種同一策略:同情同一、對立同一及無意識同一。“同情同一”指在思想情感等方面相同或相似。“對立同一”指修辭者與聽眾即使在某方面是對手,也會因有相同敵人而同一。“無意識同一”指修辭者使用包括聽眾在內的詞語,如“我們”,使聽眾無意識認同修辭者。同一機制里的勸說原理與認知語言學中“人們在學習新觀點時,往往與已形成的教育經驗及認知作對比”的觀點相似,事實證明同一策略的確可以在認知語言學中找到修辭成功的理據。如以“無意識同一”掩蓋的認知規律為例,回想服裝店的宣傳海報,“讓人美麗的東西值得購買”是人們潛意識里認可的一般價值觀,加上海報中身著新款服飾而顯得妖嬈動人的模特圖片,顧客很難不產生“這件衣服值得入手”的沖動,這種情況下,顧客便不知不覺跟著廣告商的思緒,認為自己換了新衣服就如圖中所示,無疑這正是一種地道的體驗性同一。
(四)新修辭學中的“職業心理”“訓練出的無能”及“術語屏”
人通過語言接受教育、參與交往,形成自己“訓練出的無能”“職業心理”和獨特的“術語屏”,這是新修辭學認識論中的主要內容。“訓練出的無能”指由于人的教育訓練等而形成的能力使人能做某事,但不能做其他事,如擅長繪畫的人在音樂方面可能五音不全。由于教育背景等不同,人的“職業心理”也不同:木匠看木箱是看它的工藝,拾荒者則看它是否值錢。同理,由于成長經歷不同,各人掌握的詞匯也不同,形成了不同“術語屏”,決定了個人認識世界的視角,它就像一個過濾器,在允許某些事物進入視野時,其他事物就會被篩選遮蔽掉。
由上不難看出,它們歸根結底都與人們在客觀世界中各異的體驗有關,人們習慣按照自身經驗闡釋事件。人在語言中思考,就必然導致擁有不同術語屏的人對世界的理解不盡相同。這正與認知語言學中的圖式理論相似,認知學表明人們認識事物時總是根據已有圖式以某種視角認知它。如著名的圖形與背景實驗證明了人們傾向看到自己熟悉、感興趣的東西:有人將視線聚焦在圖片的黑色部分,會看到人的側臉輪廓;有人則首先把視線聚焦在白色區域,看到一只花瓶。總之,人的認知受制于人腦中的圖式,圖式是在對事物間關系認知的基礎上構成的結構,來源于人體在外部世界中的活動,具有體驗性,從認知語言學視角佐證了“職業心理”“訓練出的無能”及“術語屏”的運作原理。
(五)新修辭學中的“不協調而獲視角”
伯克修辭學認識論的方法論是“不協調而獲視角”,即破除思維定式。該認識論方法也體現了它與認知語言學的交叉,可從體驗觀中找到支持。盡管人們依據不同體驗會獲得“訓練出的無能”“職業心理”和獨有“術語屏”,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人們無法打破以往思維圖式。新修辭學強調誘發合作,人們必不能固執己見,要換位思考,看到他人的處事依據。格式塔心理學表明,當認知者換用新視角看問題時,他會主動為觀察的事物提供新的整體圖式,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看圖實驗中不同視角均可被人們理解:最先看到側臉輪廓的人將關注點從黑影轉向白色時能獲得對該圖的新理解,即看到花瓶,最先看到花瓶的人在強制轉換視角時則能看見人物輪廓。
四、結語
伯克的新修辭學豐富了西方修辭學的內涵,提出了很多具有開創性的見解。從前文得知新修辭學與認知語言學有很多交匯,筆者認為這與它們所處的時代背景分不開。新修辭學與認知語言學具有相同后現代背景。后現代主義指20世紀上半葉以來哲學上反對主體性和主客體對立的哲學思潮(馮契,徐孝通,2000:316),用哲學家利奧塔的話說,它指“對元敘事的不信任”(姚大志,2000:1-2),即關于“人類解放”的故事。這與新修辭學的任務即促進社會和諧相呼應。而認知語言學作為認知科學與語言學的交叉學科,秉承“意義基于體驗”的體驗觀,認為人們在使用語言時總會將主觀態度帶入其中,也與新修辭學的基本觀點不謀而合,可看作對現代主義解構的武器。相比國外對伯克學說的研究熱情,我國新修辭學研究還不成熟,如要完整把握其精髓,跨學科研究原則不容忽視,希望以后有更多學者投身伯克新修辭學研究中,從中吸收理論精華,為國內修辭學的蓬勃發展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