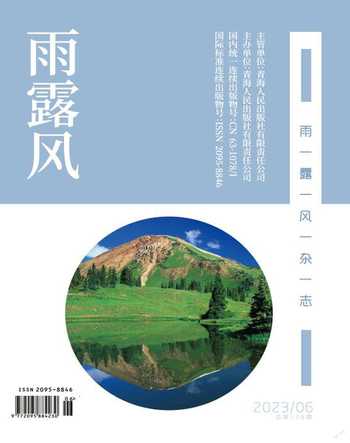現代性視域下的《儒林外史》悲劇意蘊探究
本文嘗試將《儒林外史》的悲劇意蘊放在現代性的視域下進行探究。吳敬梓通過描述泰伯祠的興與廢,宣告了舊文化與價值體系的死亡,借儒林的眾生相揭露了明清時期士人的存在困境及價值危機。而復古的失敗嘗試則讓《儒林外史》的悲劇性表現出一種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痛苦、失落與迷茫,有著特殊的思想文化史價值。
一、泰伯祠的興與廢——失敗的復古嘗試
《儒林外史》的審美特征可以看作丑劇與悲劇的“復調”,丑劇是鑼鼓喧天的雜耍,悲劇則像一段凄清哀婉的小提琴旋律,含蓄而克制。第三十回杜少卿的出場,在我看來不僅可視作寫實性逐漸加強的節點,也是悲劇的審美特質逐漸壓倒丑劇的標志。杜少卿與遲衡山、季葦蕭等“賢人君子”從相聚到風流云散,作為一條敘事線索,從三十三回綿延至五十五回,雖時不時有情節的枝杈旁逸斜出,但是隱而不斷,在《儒林外史》獨特的文本結構特征下,格外引人注目。而祭泰伯祠更是這一條線索的主干。正是因為祭泰伯祠,全書士人都開始向南京集中。《儒林外史》特重寫人,隨著人物的聚集,之前散亂的一條條線索也都聚攏在泰伯祠內,造成信息量的迅速堆積,進而達到了全書情節的高潮。隨著泰伯祭的結束,圍繞著杜少卿與泰伯祠的南京名士也如落葉般飄零,小說的情節線索也再次變得蕪雜,南京士人聚散這條線索逐漸淹沒。臥閑草堂本評道:“從開卷歷歷落落寫諸名士,寫到虞博士是其結穴處,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結穴處。”
所謂“結穴”,是指在祭泰伯祠這條情節線索中,吳敬梓寄寓了全書最為深刻的思索,這從對相關情節特殊的處理方式便能看出。遲衡山首提祭泰伯祠是在三十三回,泰伯祭則要到第三十七回,吳敬梓足足用了四回的篇幅為泰伯祭蓄勢。在這四回中,從遲衡山首倡到籌措銀兩物資到商議主祭,每一步都有交代,呈現出步步為營之勢。而主祭虞育德更是小說中少有的近乎用史傳筆法將先前行狀一一交代清楚的人物。虞育德是“書中第一人”,與泰伯祭共同象征著以古禮古樂匡正世風的理想追求,體現出一種強烈的復古傾向,虞育德是“真儒”,泰伯祭的禮樂更是整個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正統文化體系的源頭。顯然,吳敬梓想借泰伯祭在作品中進行一場復古的嘗試。三十七回的泰伯祭是全書的高潮,以其獨特的寫法與語言風格而格外引人注目。大段的重復以及對祭禮過程每一個細節近乎瑣碎的交代讓整段情節都“古氣磅礴”,這顯然是吳敬梓有意追求的結果,繁瑣冗長的敘事與《儒林外史》輕盈跳蕩的整體敘述風格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從籌備到祭禮,一派史家的典章手筆,吳敬梓著意突出一種鄭重,似乎想以此來給后世作一個典范。
更值得玩味的是,吳敬梓以同樣的鄭重經營著泰伯祠的“毀”。泰伯祭激起的漣漪在三十七回以后的回目中蕩開:先是遺憾未能躬逢其盛,后是感慨賢人君子零落略盡,到第五十五回剩下一句:“這些古事,提起來令人傷感,我們不如回去罷!”離三十七回愈遠而感慨愈深,從具體可感的人事遺憾到不可言說的大傷感,泰伯祠被遺忘的過程,也是泰伯祠承載的“習學禮樂,以助政教”的復古理想瓦解的過程。這樣的結局讓泰伯祭的鄭重筆調變為一種荒誕。寬蓋與鄰居瞻顧泰伯祠舊跡的一段,臥評曰:“凄清婉轉,無限悲吊,無限悲感。非此篇之結束,乃全部大書之結束。”這里的結束也可以理解為復古理想的結束,也是吳敬梓內在的從自我建構到自我摧毀的這一噬尾蛇般的思想過程的結束。
祭泰伯祠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文化復古情懷,這產生于對當下文化環境的反思與批判。在古代中國,革新的沖動往往被包裹在“向后看”的循古傾向里。故而泰伯祭越過了朱熹與孔丘,直接找到了泰伯這位南京的“古今第一賢人”;也越過了四書五經,直接回到了古禮古樂,回到了正統文化最古早的精神源頭。泰伯祠與泰伯祭的結局,不是被反對,而是被遺忘——一個比被反對更尷尬與悲哀的處境,只剩下一些瞻仰遺跡的姿態與感慨。吳敬梓親手建起泰伯祠又親手推倒了它,即使逆流而上追尋到文化純潔的源頭依然于世無益,世風依然在崩壞墮落,以禮樂為源頭,整個正統文化的泱泱巨流被否定了,這些生在古中國的黃昏的士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價值危機與自我懷疑,他們所處的精神文化空間正不可避免地變成一潭死水,毒與鬼在其中淤積,直到百年后的一場痛苦文化轉軌中的新生。
二、懸置與流動——士人的存在困境
在中國的歷史文化環境中, “士”的概念相當復雜,難以給出一個既清晰又有充足的概括力的定義,只能說特定歷史時期的士人群體往往會體現出一些較為鮮明的特點。而在作為小說時間背景的明朝及吳敬梓所生活的清朝,隨著科舉制度的最終完善及庶族地主階級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統治地位的牢固,相較于前代,明清士人有兩個突出的群體特征:懸置與流動。這兩個特征深刻影響了明清士人的心理結構。
《儒林外史》對明清士人的懸置和流動特征有全面而細致的呈現。懸置,可以理解為一種特殊的生存狀態,即不掌握生產資料也不直接參加勞動,為謀生計不得不依附于他人。《儒林外史》中士人的謀生手段主要有四種:處館、賣字作文、編選時文和游食。這四條謀生之路無不仰仗于他人的施舍,也就使士人時刻處于焦慮不安的狀態,今日被給予的,明日隨時可收走。明清士人處于社會的不穩定的中間層,讀過書、受教育的經歷使他們自覺高于底層民眾,對于官宦豪紳、富商巨賈,則極盡諂媚之事。在第四十七回,作者以辛辣的筆調諷刺了五河縣的民風,這種大段的議論語言相當少見,敘述者直接跳出來作評論,滿腔激憤鄙夷溢于言表。吳敬梓描寫了五河縣的兩類士人,一類是余、虞兩家的舉人、進士、貢生、監生、秀才,他們趨附于“中了幾個進士,選了兩個翰林”的彭鄉紳。另一類是余特、余持,對舊道德的崩壞和士人的墮落痛心疾首,實際上卻無能為力。懸置的狀態讓明清士人相較于前代更加直露地趨炎附勢,因為這是士人唯一的謀生之道,漸漸地引發對財利權勢的崇拜,也給自持清高、循禮守舊以期風世的士人帶來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他們無力改變現狀,無力挽回這道德崩壞的末世。這固然是因為他們無財無權,只有胸中點墨與翻爛的四書,更深刻的原因是沒有外來的思想資源讓他們跳出現有的知識結構重新審視社會問題與士人的精神問題。小說中兩位余先生認為道德淪喪的根源是沒有一個像虞先生那樣的“真儒”,而虞先生大展其“德化”的泰伯祠也頹毀了。這種精神上的懸置狀態給這類士人帶來的是道德焦慮而非生計焦慮。這種焦慮是極強烈且不穩定的,要么如莊紹生、虞育德那般自絕于世,要么極有可能在道德壓力的催迫下更瘋狂地投入科考之路。
流動性也是明清士人區別于前代的重要特征。流動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向上流動,即通過科考體制,成為官僚集團的一員,進而掌握權力,擺脫懸置狀態,《儒林外史》中最為經典的例子便是范進。一種是向下流動,以杜少卿最為典型。天長杜府“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在天長縣時,杜少卿曾浪擲千金幫助過臧荼、張俊民、鮑廷璽等人,移家南京后則日漸拮據,到后來需要當掉衣服才能湊出四兩銀子。小說中多次提到杜少卿賣田籌錢資助他人的豪舉,也正是在田宅賣盡后,杜少卿又回到懸置的狀態。這是杜少卿主動的選擇,“鄉試也不應,科歲也不考”,放棄科舉仕途,甚至直接放棄生產資料,將田賣盡后“隨手亂用”。這固然是杜少卿超凡脫俗一面的表現,借用周月亮的評語便是“敢于絕望”,敢于面對懸置的處境,寧愿像范進中舉前兩天開不了鍋,也不愿走上科舉仕途,同時也意味著將始終處于懸置的狀態,時不時要面對揭不開鍋的絕望。多數情況下,儒林中人陷于科舉的泥淖可能并不是想“榮身”,只是為了免于對懸置與絕望的恐懼。如果說杜少卿的向下流動是自我的選擇,那么蘧府從蘧祐、蘧景玉、蘧駪夫到蘧駪夫的兒子,這四代人無可挽回的向社會下層流動的軌跡則體現出一種殘酷。蘧祐初任縣令后又“升任南昌”,是朝廷命官;蘧景玉一開始去山東門道、“門伯”范進處作“少年慕客”,后又因蘧祐“署內無人辦事”而隨侍左右;蘧駪夫名士和舉業都做不成,逐漸沒落為庸流之輩;其子在魯小姐的逼迫下自小講讀四書,看來是要重新走上科舉仕途。這種殘酷體現在明清士人在所處的社會環境中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如果不走科舉之路向上攀爬,就不可避免地向下流動,只要三代人就重回懸置狀態。
懸置和流動的生存狀態造成了明清士人普遍而強烈的焦慮。而科舉制度作為士人向上流動、擺脫懸置狀態的唯一途徑,便在無形中支配了處于焦慮狀態下的士人的精神世界。這種支配是多方面的,士人的人生觀、價值觀乃至于審美趣味無不與之掛鉤,以至于魯編修說:“八股文章若作的好,隨你作什么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作出什么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更重要的是,士人入鮑魚之肆而不覺其臭,甚至醉心于科舉仕途的鉆營,這從馬純上對編選時文的蓬勃熱情就能看出。不僅沒有反思,甚至還樂此不疲,這是一種近乎頹廢的癲狂與沉醉——不問意義,在細處甚至是無意義的事物上以狂熱的態度耗盡心血。正因為如此,《儒林外史》將對明朝以來士人的生存狀態的反思聚焦于科舉制度。第一回便借王冕之口評價了明朝以來的科舉制度:“這個法卻定得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這樣的反思在小說中再也沒有出現,可見“文行出處”確實被忘了個干凈。
《儒林外史》對科舉制度的評價并不著眼于社會文化層面,而是強調其對士人生存狀態尤其是精神世界的影響。《儒林外史》在第一回便開宗明義,“一代文人有厄”,厄,有義項為車轅前端架在馬頸上的橫木,這一詞用得實在是生動。科舉制度是士人向上流動的唯一途徑,不由此路,不僅基本的生存條件得不到滿足,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也歸于空無。這種極具現代特征的荒誕感近乎絕望:只有套上這橫木才能在精神與物質兩個維度下繼續存在下去,士人存在的意義、生存的憑借都系乎這橫木。然而這橫木也在不斷地窄化,腐蝕著人存在的內涵與豐富性,最終使之成為行尸走肉:或是道德淪喪,為生存的私欲而無所不用其極,如匡超人、牛圃郎等;或是精神萎頓,在八股仕途的泥沼里沉沒,如周進、魯編修、馬純上等。吳敬梓也嘗試著書寫另一種存在的方式,來為可能從這架在頸上的橫木中掙脫出來的士人提出存在的價值的歸依與憑借,如王冕“連夜逃往會稽山中”、莊紹光“我道不行”“懇求恩賜還山”、虞育德“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縣……每年養著我夫妻兩個不得餓死,就罷了”。然而,我們又禁不住像魯迅那樣問一聲:“還山”之后怎樣呢?吳敬梓沒有回答,也無力回答,他的理想隨著泰伯祠的傾頹如落日般緩緩沉沒,只有儒林中眾生相的喧嘩與嘈雜掩蓋著這致命的、空蕩蕩的沉默。這是《儒林外史》悲劇性的根源,也使整部小說在諷刺的嬉笑輕快之下流露出自作挽歌一般的沉痛悲涼的審美特征。
三、復古中求新生——自發的現代性
吳敬梓通過《儒林外史》梳理了士人的精神困境,試圖用泰伯祭的復古嘗試來改變現狀,這就蘊藏著新變的動力,對“中世紀”的反動是現代性最堅實的基礎。以吳敬梓為代表的敏感而獨立的士人站在時代的最前沿,他們發現前方無路可走,而現狀又是如此的不堪與墮落,滿是荒誕的困境。而他們的知識結構與文化背景無法給另立價值體系的努力以支持,于是他們只能把求索的目光越過現代投向古代,投向被重重疊疊的書寫變得漫潰不清的“三代之盛”,是在復古中求新生。
如果打破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之間的藩籬,將《儒林外史》置于整個中國文學從古典轉向現代的歷程中,會發現《儒林外史》處在一個關鍵的節點上,那是落日墜下山莽的那一瞬間。這是一個特殊的時間點,在這一時間點上的知識分子有著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思想矛盾與精神掙扎。這些思想矛盾是中國自發的現代性的最有思想史價值的一部分。西方的現代思想體系尚未到來,現實的困境與精神危機又迫使知識分子進行思想的探索與價值的開拓,這些探索與開拓是中國自發的現代性,有著深刻的中國特質,比如復古形式下的革新等等。同時以吳敬梓為代表的士人又對其所生長的文化環境有著深刻的眷戀,這與五四運動以后欲置舊中國于死地的知識分子截然不同。這一代知識分子在走投無路的困境中,在對文化傳統既憤恨又眷戀的矛盾中,孤獨地行走于萬馬齊喑的黑暗里。
作者簡介:徐天馳(2002—),男,漢族,江蘇江陰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為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