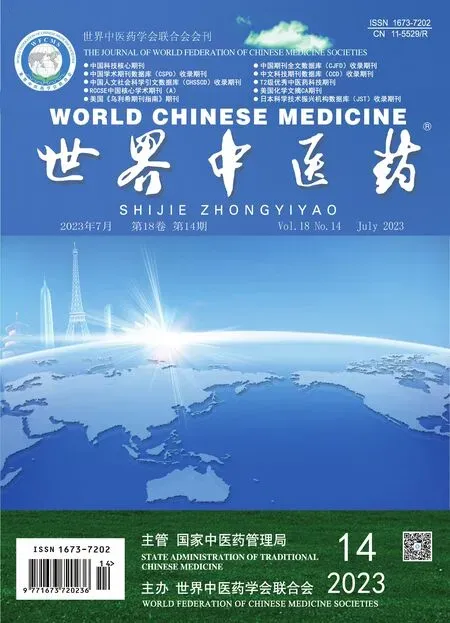針灸防治炎癥性腸病的研究進展
楊新月 唐青青 孫濛濛 何 敏 薩 仁 李 鐵 王之虹
(1 長春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學院,長春,130117; 2 長春中醫藥大學東北亞中醫藥研究院,長春,130117; 3 三亞市中醫院,三亞,572000)
炎癥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種慢性非特異性腸道炎癥性疾病,包括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羅恩病(Crohn's Disease,CD)[1-2]。它的發病率不斷上升,已經成為一種全球性疾病,在西方國家,其患病率超過0.3%[3],近年來我國患者也在不斷增加,IBD已成為全球范圍內的公共衛生挑戰。目前認為IBD是由環境因素、遺傳因素、免疫因素和微生物等因素共同引起的[4-6]。通常是使用糖皮質激素、氨基水楊酸制劑、免疫抑制劑、生物制劑、手術等方式對其進行治療,然而藥物治療會產生一定的不良反應,手術又有致殘的風險[7]。IBD患者會出現腸梗阻、腸穿孔、腸瘺等并發癥,甚至增加患癌癥的風險,因此,也被稱為“綠色癌癥”。由于IBD的疾病特點,患者需要反復住院,藥物、手術、住院等也需要較高的醫療費用,對家庭和社會造成了較大的經濟負擔[8]。針灸對IBD的防治具有的積極作用得到關注,現對針灸防治IBD的研究進展從病因與診斷到臨床應用與機制研究展開綜述。
1 IBD的病因
目前,IBD的具體發病機制尚不明確,但可以確定與遺傳因素、環境因素、免疫因素和腸道微生物有關。
1.1 遺傳因素 基因突變或被誘發的基因改變被認為是IBD發生發展的一個先發性因素,研究顯示,IBD具有種族和地區差異,具有一定的家族遺傳性[9]。20世紀30年代首次報道了IBD的家庭聚集性,UC患者親屬的患病率為5.7%~15.5%,IBD患者親屬的患病率為6.6%~15.8%[10]。2001年,研究發現了第1個CD相關的疾病基因[11-12]。隨后的研究中又發現了163個IBD疾病相關的基因位點[13]。在這些基因位點中,有110個是IBD亞型的相關位點,其中,30個基因位點與CD相關,23個基因位點與UC相關。這163個基因位點也解釋了13.6%的CD和7.5%的UC的疾病變異[14]。在IBD的全基因組關聯性研究中,確定了99個非重疊的遺傳風險位點,其中包括28個在CD和UC中的共有位點[15]。
1.2 環境因素 不同的地理位置、生活環境具有不同的IBD易感特點。北美和北歐報告的CD和UC的發病率和患病率最高,南美洲、東南亞、非洲(南非除外)和澳大利亞報告的發病率最低[16]。IBD的發生與地區工業化程度,醫療衛生水平均具有相關性。許多低發病率地區包括發展中國家。有統計顯示,低發病率地區的居民移居到發達地區,其發病率明顯上升[17]。除了地理環境、經濟發展等因素,生活習慣、飲食規律等也是影響疾病發展的重要因素。有研究發現,吸煙和肥胖都與CD正相關[18]。以高水平的飽和脂肪酸、紅肉和各種加工肉類食品為主的西方飲食習慣常常導致維生素D的缺乏,也被認為是IBD發病率上升的主要原因[19]。環境污染和食品添加劑的使用也被認為是誘發IBD發生的主要環境因素[20]。而較高水平的維生素D和維生素B9可以降低IBD的風險[21]。
1.3 免疫因素 IBD是一種發病機制不明的腸道免疫性疾病,現有證據表明,對環境改變的異常免疫反應是遺傳易感個體患病的原因。適應性免疫反應通常被認為在IBD發病機制中起主要作用。然而,免疫學和遺傳學的最新研究進展表明,先天免疫反應在IBD的發生發展進程中同樣重要。上皮屏障功能的改變會導致UC的腸道炎癥,而異常的先天免疫反應,如抗菌肽的產生,先天微生物感應和自噬,與UC的發病有關[22]。自噬作為一種維持腸道內穩態的重要過程,自噬功能障礙在IBD的發生發展中起重要作用,IBD患者體內往往會出現細胞自噬功能低下[23]。除了輔助性T細胞類型Th1和Th2免疫反應之外,其他T細胞亞群,即Th17和調節性T細胞,也可能在IBD發揮作用。NLRP3炎癥小體是一種蛋白復合物,在先天性免疫系統中也發揮重要作用。而且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NLRP3炎癥小體在IBD的發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24]。
1.4 菌群失調 腸道微生物群的穩定是腸道穩態和宿主維持正常功能的必要條件,也是局部和全身免疫系統和非免疫系統發育和分化的必要組成部分[25]。最新的研究通過新一代測序技術,已經確定腸道菌群的數量和功能失調均與IBD的發生發展有關[26]。在IBD的研究中發現膽汁酸、短鏈脂肪酸和色氨酸等代謝物的變化,與IBD的發病機制有關[27]。整合人類微生物項目的部分研究,對132名受試者進行為期1年的追蹤,研究證實了IBD中厭氧菌特征性增加,梭狀芽胞桿菌等分子轉錄被破壞,短鏈脂肪的代謝發生改變,宿主血清中的抗體水平也出現變化[28]。有學者對腸道微生物群在IBD發病機制中的作用進行研究,通過對CD、UC、IBD的患者糞便樣本進行代謝組學和宏基因組分析,并對8 000多個代謝物進行篩選,確定了IBD的差異代謝物,包括鞘脂類和膽汁酸的富集,三酰基甘油和四吡咯的減少[29-30]。
2 IBD的診斷
IBD的診斷目前尚無統一的金標準,主要是在排除感染性和其他非感染性結腸炎的基礎上,結合臨床癥狀、實驗室檢查、影像學檢查、內鏡檢查和組織病理學表現綜合分析。
UC病程多在4~6周以上,主要臨床表現包括持續或反復發作的腹瀉、黏液膿血便,伴有腹痛、里急后重,還包括皮膚、黏膜、關節、眼、肝膽等不同的全身癥狀,其中黏液膿血便是UC最常見的癥狀。結腸鏡檢查并活檢是UC診斷的主要依據,在結腸鏡下UC的病變多從直腸開始,并呈連續性、彌漫性分布。根據疾病活動性的嚴重程度,UC病情分為活動期和緩解期,而活動期按照嚴重程度分為輕、中、重度[31-34]。
CD臨床表現呈多樣化,主要包括腹瀉、腹痛、便血等消化道表現和體質量減輕、發熱、食欲不振、疲勞、貧血等全身表現,還包括腸外表現及并發癥,其中腹瀉、腹痛、體質量減輕是其常見癥狀。CD診斷的常規首選檢查是結腸鏡檢查和活檢,鏡檢應達末端回腸。鏡下一般表現為節段性、非對稱性的各種黏膜炎癥,其中非連續性病變、縱行潰瘍和卵石樣外觀是具有特征性的表現[31-34]。
3 針灸防治IBD的臨床研究
3.1 針灸療法 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針灸學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針灸作為防治IBD的有效方法也不斷得到證實,在醫療實踐中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可。有研究連續2周觀察針灸和西藥對慢性潰瘍性結腸炎患者的療效,針灸組的治療效果更為顯著,且針灸組患者的不良反應率更低[35]。針灸可以改善克羅恩病患者腹痛、腹瀉等主要臨床癥狀,還可以調節患者血漿色氨酸代謝水平,使患者因疾病產生的負性情緒好轉[36]。針灸治療可以明顯改善活動期和緩解期克羅恩病患者克羅恩病活動指數(Crohn's Disease Activity Index,CDAI)評分以及腹痛、腹瀉、神疲乏力、形寒肢冷等中醫癥狀。腸黏膜上皮組織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轉化生長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1過度表達,使TNF-α/核因子κB/Snail1和TGF-β1/Smad3/Snail1這2條途徑引起腸上皮間質轉化[37],而溫針灸結合針刺治療可以對過度表達起到抑制作用。隔藥灸為主的方法能降低患者外周血中Th17細胞水平,達到顯著的治療效果,改善臨床癥狀從而提高生命質量[38]。針灸不僅可以改善臨床患者的不適癥狀,也改善了血液和代謝物等的相關指標,對疾病的治療和愈后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3.2 針藥結合 針灸除了作為一種單獨療法,也常常和中藥聯合應用,用于IBD的防治。張博等[39]對100例慢性潰瘍性結腸炎患者進行治療和觀察,觀察組在對照組常規西醫治療的基礎上給予針灸聯合自擬扶正平潰湯治療,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的臨床癥狀體征得到顯著改善,腸道黏膜炎癥得到緩解。李艷[40]應用中藥聯合針刺治療慢性潰瘍性結腸炎患者療效顯著,急性發作期中藥治則以涼血燥濕止痢,針法以瀉為止;緩解期宜溫補脾腎,補氣利濕,針法以補為主。王兆春和李耀龍[41]治療潰瘍性結腸炎患者是在常規西醫柳氮磺胺吡啶的基礎上加用自擬中藥湯劑和針灸治療,臨床效果明顯。有研究運用芪術三黃湯聯合針刺對IBD進行治療,治療后腸鏡Baron評分和結腸組織病理評分均得到改善,癥狀得到緩解[42]。清熱利濕益腸湯聯合針灸能調節UC患者血清中TNF-α和白細胞介素-8水平,改善相關癥狀[43]。有研究通過針刺鬼眼穴聯合膈下逐瘀湯治療活動期UC,針藥結合的治療方式有效改善患者癥狀,調節血清炎癥介質和腦腸肽神經遞質水平,提高生命質量[44]。臨床IBD的治療中,在常規藥物的基礎上加入針灸的治療,起到了一定的協同增效作用。
3.3 其他療法 埋線、隔藥灸、穴位注射等方式也被用于IBD的臨床治療中,具有一定的療效。孫志華[45]運用穴位注射配合埋線治療慢性潰瘍性結腸炎,采用穴位注射,解除臨床癥狀,起到近期治愈的作用;采用穴位埋線,鞏固前期治療效果,起到遠期治愈的目的。施茵等[46]通過隔藥灸聯合針刺治療CD患者,可以降低腸黏膜異常增高的TNF-α、腫瘤壞死因子受體(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TNFR)1、TNFR2,從而抑制腸上皮細胞的異常凋亡,對腸上皮屏障損傷起到保護作用,減輕了腸道炎癥反應。王歡等[47]對UC大鼠雙側“天樞”“足三里”“膈俞”“脾俞”“腎俞”“大腸俞”埋線治療,治療后結腸病變明顯減輕,黏膜損傷指數評分顯著降低,改變了結腸組織內相關蛋白的表達。李林等[48]對UC大鼠進行穴位埋線聯合艾灸的治療,研究發現可以調節結腸黏膜組織Notch1、Hes1表達水平,上調Math1表達的水平,調節過度活化的Notch信號通路,有效調節上皮分泌細胞系和吸收細胞系間分化的平衡。楊瀟等[49]通過八髎穴導氣針法聯合溫針灸治療脾腎陽虛型潰瘍性結腸炎,可以有效調節血清IL-6、IL-8、TNF-α水平,改善疾病活躍指數(Disease Activity Index,DAI)評分。
4 針灸防治IBD的機制研究
4.1 調節基因表達及表觀遺傳 表觀遺傳修飾調控相關基因表達在免疫反應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與IBD的結腸黏膜免疫和防御反應有著密切的關系,并影響了易感基因、機體內環境及其他環境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50]。目前,研究揭示了表觀遺傳學參與了IBD的發生發展過程,為從表觀遺傳學探究針灸對IBD防治機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有研究發現針灸治療CD后結腸黏膜組織炎癥反應減輕,與健康者比較,CD結腸黏膜基因出現差異表達,上調2 250個,下調1 199個;針灸治療后,CD結腸黏膜也出現差異表達,上調536個,下調1 390個。轉錄因子STAT磷酸化、ATP酶活性、B細胞介導的免疫、自然殺傷細胞相關免疫等,是針灸可調控的CD中差異表達基因與疾病密切相關的生物功能,而Toll-like受體信號通路、自噬調節系統、自然殺傷細胞介導的細胞毒作用為相關的幾個主要通路[51]。
4.2 調節免疫及相關炎癥介質 目前,普遍認為腸黏膜異常的免疫反應與IBD的發生有著密切的關系。IBD患者自身的腸上皮屏障薄弱,由于自身及外在原因,其自身腸上皮的先天免疫機制被打亂,對抗原的識別和處理受到干擾,非典型抗原呈遞細胞成為有效的T細胞激活劑,會清除過度反應或自身反應性T細胞群,導致調節性和效應性T細胞的平衡被擾亂[52]。IL-1β促進中性粒細胞浸潤,是一種炎癥介質;IL-17可促進T細胞的激活,釋放炎癥介質而放大炎癥反應,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發揮著重要作用[53]。研究發現與正常對照組比較,UC大鼠模型組的IL-10水平低,IL-17水平高,與模型組比較,針藥結合組、美沙拉嗪組的IL-10水平高,IL-17水平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1);針藥結合組和美沙拉嗪組的IL-10、IL-17水平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54]。艾灸與針刺可能通過抑制干擾素-γ、IL-17A表達,改善結腸黏膜免疫狀態,進而發揮治療CD的作用[55]。有研究通過艾灸神闕穴治療UC小鼠,發現艾灸神闕穴能夠顯著改善UC癥狀,并調節UC小鼠血清炎癥介質IL-6和TNF-的水平[56]。CD會使腸黏膜的TNF-α、TNFR1、TNFR2異常增高,導致腸上皮細胞出現異常凋亡,而隔藥灸結合針刺能夠對此起到抑制作用從而減輕上皮屏障損傷和降低腸道炎癥反應[46]。
4.3 調節腸道菌群 腸道菌群是由相當于人體細胞數量10倍的微生物構成的微生態系統,在人體腸道內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腸道菌群在參與營養物質與維生素代謝的同時,還分泌著多種酶類[57]。在生理狀態下,組成腸道微生態系統的菌群數量和比例是相對恒定的,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而針灸就是通過對腸道菌群中有益菌含量以及菌群多樣性的調節使在IBD發生發展中被打破的腸道微生態恢復平衡和穩定。魏大能[58]電針和艾灸UC模型小鼠的關元、足三里,發現電針和艾灸干預UC模型小鼠后,其腸道菌群中群落組成和群落豐富度有所改變,增加了有益菌乳桿菌等的數量,降低了有害菌鏈球菌等的數量。何其達[59]在艾灸調節消化性潰瘍大鼠腸道菌群失衡的作用機制研究中,發現艾灸足三里和梁門能夠提高腸道中的有益菌數量,艾灸可以通過影響菌群的種類和數量以達到修復腸黏膜、治療消化性潰瘍的作用。艾灸UC大鼠雙側天樞改善了病變結腸黏膜而使腸道內菌群水平恢復趨近正常[60]。艾灸能夠較好地調節梭菌、帕拉普氏菌屬、毛螺旋菌科等菌群,以調節CD模型大鼠腸道菌群豐富度與多樣性[61]。同時,針灸對可能是CD治療關鍵菌的擬桿菌、腸桿菌以及乳酸桿菌等起作用,從而實現對失調腸道菌群的良好調節作用[62]。
4.4 調節機體代謝物水平 IBD由于機體異常的免疫反應及腸道炎癥變化,其機體的自身代謝和代謝物會發生變化。針灸作為一種中醫治療方法,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可以起到調節氣血,協調陰陽的作用,進而調節機體異常的代謝變化。肖山峰[63]對CD大鼠結腸組織代謝物運用代謝組學技術進行分析,發現針刺和艾灸對氨基酸代謝、能量代謝、糖代謝和膽汁酸代謝發生紊亂的CD大鼠能起到調節作用,艾灸對氨基酸的調控更加明顯,針刺對能量代謝的調控更加明顯。耿煜[64]篩選出甘油二酯、肉堿、氟尿嘧啶、丁酰膽堿酯酶等7個分子標記物,發現艾灸可以通過影響UC小鼠的脂肪酸、氨基酸代謝等能量代謝通路改善其血液代謝物紊亂。楊陽等[65]研究發現UC大鼠電針治療后,顯著降低的大腦皮層谷氨酸、總膽固醇和極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和顯著增加的丙氨酸、低密度脂蛋白均有回歸正常的趨勢。劉紅華[61]對CD大鼠結腸代謝物進行篩選,主要代謝物通路為牛磺酸、次牛磺酸代謝、丙氨酸、天門冬氨酸和谷氨酸代謝,精氨酸、脯氨酸代謝,甘氨酸、絲氨酸和蘇氨酸代謝,初級膽汁酸合成,纈氨酸、亮氨酸和異亮氨酸合成等。艾灸干預使代謝紊亂狀態的CD模型大鼠在一定程度恢復正常,甜菜堿、膽堿、肌酸、肌醇、牛磺酸、亮氨酸、異亮氨酸、賴氨酸等代謝物顯著回調[62]。
5 小結
隨著人們對IBD的關注度逐漸增高,作為一種安全、有效、無不良反應的治療方法,針灸也越來越多被運用于臨床IBD的防治中,并且其改善IBD患者癥狀的作用是得到證實的。中醫學將IBD歸屬“休息痢”“久痢”“泄瀉”“痢疾”“腸澼”等范疇。針灸通過調節氣血,平衡陰陽而起到防病治病的作用。目前的化學藥物治療存在一定的不良反應,患者長期用藥難以耐受,不得已停藥又容易導致病情反復,而針灸作為一種有效的治療方式,可以在IBD的各個時期發揮作用。但目前臨床的研究樣本數量少,以個案報道為主,研究多以療效為主要關注點,較少涉及其作用機制的深入研究。目前,針灸防治IBD的作用機制主要以調節基因表達及表觀遺傳、調節機體免疫及相關炎癥介質、調節腸道菌群數量和比例的相對穩定、調節機體代謝物水平等幾個方面。隨著基因組學、蛋白組學等技術的不斷發展,針灸防治IBD的機制也將得到不斷的深入研究,這也將為IBD的臨床多元化全方位的治療方案提供更多的參考和依據。
利益沖突聲明: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