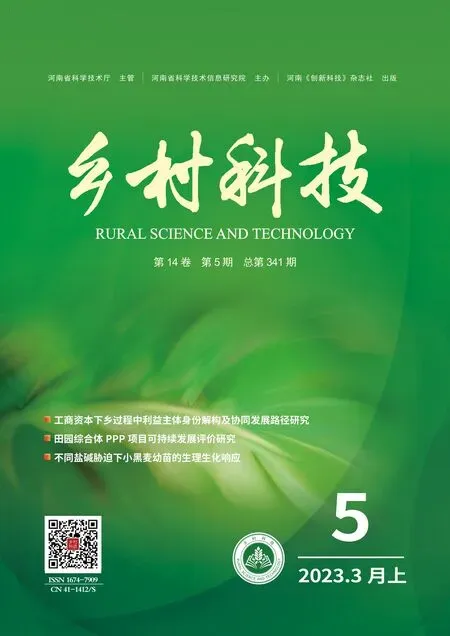元陽縣哈尼族傳統村落景觀特征分析
單選倫 包 蓉
西南林業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云南 昆明 650224
0 引言
2013 年6 月,紅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觀獲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而位于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陽縣的元陽梯田作為紅河哈尼梯田的核心區,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和生態價值。因此,筆者選取元陽縣哈尼族傳統村落作為研究對象,對該地區哈尼族傳統村落的形成背景和聚落景觀要素進行分析研究,梳理出哈尼族傳統村落的景觀特征,以提高人們對哈尼族傳統村落景觀的認知,為紅河哈尼梯田的傳承和保護及未來的發展提供借鑒。
1 元陽縣傳統村落概況
元陽縣隸屬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哀牢山脈南段、紅河南岸,地理位置為東經102°27′~103°13′、北緯22°49′~23°19′,東西跨度74 km,南北縱距55 km,總面積2 212.32 km2[1]。元陽縣東與金平縣相接,南與綠春縣相連,西與紅河縣相鄰,北與建水縣、個舊市、蒙自市隔紅河相望。截至2019 年6 月,元陽縣境內共有7 個傳統村落列入我國傳統村落名錄,分別為阿者科村、箐口村、埡口村、大魚塘村、太陽老寨村、全福莊中寨村和大順寨村。在這7 個傳統村落中,太陽老寨村和大順寨村分別為瑤族傳統村落和傣族傳統村落,其余5個皆為哈尼族傳統村落。
2 元陽縣哈尼族傳統村落景觀產生的自然資源背景
2.1 地形地貌
元陽縣屬于低緯度高海拔地區,地處橫斷山系哀牢山脈南段。由于元陽縣海拔較高,境內高差較大,河流底蝕強烈,因而該地區形成了深切割中山地貌。此種地貌主要集中在縣內哀牢山南北坡的中山地區,占元陽縣總面積的84%。受到新構造運動影響,元陽縣境內發生大幅度的間歇性抬升和夷平作用,故形成了山高谷深、層巒疊嶂、溝壑縱橫的總體地貌特征。同時,由于受到南部藤條江和北部紅河的切割與侵蝕,元陽縣境內形成了中部高、兩側低,呈“V”字形發育的地形;境內以觀音山—白巖子山一線為紅河和藤條江的分水嶺,將元陽縣分為了南北兩部分;總體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海拔最高處為白巖子山(2 940 m),海拔最低處為小河口(144 m),相對高差達2 796 m[1]。元陽縣境內除去少量分布于山間河谷地帶的小沖積、堆積壩子之外,其余都是山區,因此該地區以山地農業生產為主。據2016 年統計數據,元陽縣耕地面積達到24 741.66 hm2,其中哈尼族耕作的水梯田面積占45.4%[1]。
2.2 氣候
元陽縣地處云南省南部,位于北回歸線以南,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由于境內南北氣流的影響及海拔差別很大,故當地形成了夏季高溫多雨、冬季溫暖少雨、干濕季分明、夏無酷暑、冬無嚴寒、多雨區和少雨區分明且水平分布復雜、山地立體氣候顯著的總體氣候特征。元陽縣年平均氣溫24.4 ℃,年平均降水量1 397.6 mm,年平均相對濕度85%,全年日照時間1 770.2 h[1]。元陽縣立體氣候顯著:在海拔1 000 m 以上的山區,溫度下降使暖濕氣流凝結于此,形成云霧繚繞的自然景觀;而在海拔1 000 m 以下的地區,溫度較高且水資源豐富,利于農作物的生長。元陽縣境內觀音山所形成的天然屏障,使來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暖濕氣流受到阻擋,加上元陽縣境內海拔差別很大,共同造成當地“一山分四季,隔里不同天”的氣候特點。依據不同海拔,元陽縣氣候可分為高山、上半山、下半山、河谷4 種微氣候類型。
2.3 水資源
以境內的觀音山作為分水嶺,元陽縣內水系分為南部藤條江和北部紅河水系,共有大小河流29 條。其中,藤條江水系落差大,水力資源豐富;紅河位置低,落差小,支流眾多,水力資源利用價值小,但水力資源豐富。元陽縣境內河流總長約700 km,流域面積2 216.9 km2,常年流量為42.7 m3/s,水能資源蘊藏量為36.81萬kW,其中可開發量為21.38萬kW,占水能資源的58.1%[1]。
2.4 植物資源
元陽縣境內山高谷深、地形復雜、氣候多變,植被類型多樣。截至2020 年,元陽縣森林覆蓋率達54%,不同植被類型在縣內相互交錯,具有明顯的鑲嵌性,但以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和針闊混交林為主。根據氣候和海拔不同,可將元陽縣的植被類型分為3 大類:低熱河谷稀疏灌草叢植被,分布在海拔800 m 以下的河谷地帶,由于長期的開發利用,原始狀態的植被已經遭到破壞,現存多為次生林;中山暖濕性常綠闊葉林及針葉林帶,分布在海拔800~1 600 m 的地區,現有闊葉林保持原生狀態的較少,多為次生林;亞熱帶常綠闊葉苔蘚林,分布在海拔1 600 m 以上的地區,基本保持了原生狀態,是維護元陽縣生態環境的重要植被帶。
3 元陽縣哈尼族傳統村落宏觀景觀特征分析
哈尼族人遷徙、定居到紅河南岸和哀牢山區之后,其生產方式由狩獵、采集向精耕細作轉化,其生活也由游牧變為了定居。因此,無論是其村落的選址還是規模,都圍繞著梯田稻作農業展開。
3.1 選址方面
根據對元陽縣5 個哈尼族傳統村落的調查,筆者發現哈尼族村落的選址均是以三面環繞高山、前方一覽無余、在地理空間上相對封閉而隱秘的地方作為落腳點。將村落修建于這樣的地方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來自外界的侵擾,使族人獲得安全感。同時,這樣的選址容易蓄水,從而滿足村民的生產生活用水需求[2]。
3.2 規模方面
元陽縣哈尼族傳統村落的規模各有不同,大至一兩百戶,小至三十四戶。針對元陽縣5 個哈尼族傳統村落,筆者查閱了相關文獻,開展了現場調查,并沒有發現關于村落規模的具體村規民約,但發現在這些村落發展過程中,當沒有多余空地建房時,村民會共同商量由某幾戶村民搬離原村落,并依據傳統的選址原則去選擇新的村落營建地點。在實地訪談中,筆者發現哈尼族傳統村落的規模與以下兩個因素有關。一是村落適宜建房的土地面積,二是村落所擁有的梯田面積。由于村落適宜建房的土地面積相對固定,因此當村中人口數量隨時間不斷增加,而村落中的土地不能滿足建房需求時,就會促使新村落的出現。哈尼族人將梯田建在村落的下方,因而梯田的面積也是相對固定的;隨著人口的增加,梯田的產出不能滿足人們的生活需求時,人們就會向外搬遷,尋找適合耕作的土地并在當地定居,從而產生新的村落[3]。
4 元陽縣哈尼族傳統村落微觀景觀特征分析
4.1 建筑方面
元陽縣哈尼族傳統村落中的民居以“蘑菇房”為典型樣式,其中阿者科村的“蘑菇房”建筑群保留得最為完整。“蘑菇房”因其房頂形似蘑菇而得名,屬于邛籠式建筑。“蘑菇房”大部分為3層獨棟建筑,采用竹木材料的梁、柱作為支撐,與土坯墻、石墻共同承重。
從平面布局來看,可以將哈尼族“蘑菇房”分為以下3 種類型。一是“獨立型”,其平面近方形,尺度較小,在入口處設有門廊,將門廊一側隔出房間,供人居住。二是“曲尺型”,即“L 型”,由正房加單側耳房組成。“曲尺型”蘑菇房因平面組合方式的不同而形成了兩種格局,一種是“糯美型”,正房與耳房在平面上是兩個獨立的矩形;另一種是“糯比型”,正房與耳房在平面上組成一個整體,呈曲尺狀。三是“合院型”。“合院型”有兩種格局:一種是“三合院”形式,正房兩側各設一間耳房形成半圍合形式,利用地形差異將正房和耳房分臺而建,可由正房二樓進入耳房的曬臺,曬臺面積較大;另一種是“四合院”形式,由正房、兩側耳房和入戶門廊組成四面圍合空間,中間留有天井[4]。
因為元陽縣處于亞熱帶山區,具有雨熱同期的氣候特點,濕度較大,所以“蘑菇房”的一樓多用于關養牲畜、存放柴草,少數村民會將廚房設置在一樓,第一層的層高較為低矮(1.5~2.0 m);二樓用于居住,有臥室和廚房、糧倉、火塘等;一樓與二樓之間以石階或木梯連接。大部分“蘑菇房”的石階建于屋外,而木梯由于耐水性差,通常建于屋內。第三層由閣樓和曬臺兩部分組成,閣樓部分及茅草覆蓋的屋頂約占總面積的2/3,用來存放曬干的糧食,剩下的1/3 是曬臺,用來晾曬糧食、衣物,也是哈尼族人活動的場所。曬臺一般朝東,便于陽光照射。茅草屋頂通往曬臺的一側會設有一扇門,方便人進出曬臺[5]。
4.2 道路方面
元陽縣5 個哈尼族傳統村落位于海拔1 200~1 900 m 的山區,阿者科村海拔1 880 m,箐口村海拔1 600 m,埡口村海拔1 360 m,大魚塘村海拔1 920 m,全福莊中寨村海拔1 840 m[6]。5個傳統村落中的房屋沿等高線修建,其內部主要道路也沿等高線修建,而連接主要道路和寨神林的彈石路則垂直于等高線形成輔路,連接每家每戶的小路與輔路相平行,這3 種道路共同形成了哈尼族傳統村落的主要街巷。由于筆者研究的5 個哈尼族傳統村落入選了中國傳統村落名錄,同時處于紅河哈尼梯田的核心區,因而當地獲得的相關支持較多,村落中大部分道路都經過了硬質化處理,但因所采用的修筑材料不同,所以形成了不同形態的道路。
4.3 給排水方面
哈尼族人在村落選址之初,便將水源位置的選定放在首位。水是哈尼族傳統村落“森林-村落-梯田-河流”四素同構生態循環系統中最為重要的一環。每個哈尼族傳統村落的水源均來自村落上方的水源林,部分水源林緊挨村落,部分水源林距村落較遠。在元陽縣5 個哈尼族傳統村落中,大魚塘村、全福莊中寨村和埡口村的水源林都緊挨村落,阿者科村和箐口村的水源林則處在距離村落一定距離的廣闊森林中。
溝渠是哈尼族傳統村落給排水系統的重要組成,分為大渠和小溝兩種類型。大渠寬度為30~60 cm,由自然土石壘砌而成。一部分大渠將水源林的水引入村落和梯田中,為哈尼族人提供生產生活用水,同時另一部分大渠將人畜生產生活廢水排入梯田。哈尼族人充分利用山地地形特點,將大部分大渠建在垂直于等高線或與等高線成較大角度的地方,利用高差增加水流速度,保證能在雨季快速泄洪。小溝也是給排水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圍繞著民居建筑墻腳修筑,將生活污水和雨水排入大渠。小溝通常比房屋的地基低15 cm,以避免土坯房遭雨水侵蝕。小溝還有一個特殊功能,即“沖肥”。哈尼族人會將自家飼養的禽畜產生的糞便堆在“肥塘”里,需要時用水將肥沖入小溝內,再經由大渠最終流入梯田,滋養田中農作物。哈尼族人通過溝渠得到生產生活用水,同時通過溝渠將使用后的污水引入梯田用來灌溉,充分展現出其對水資源的循環利用。
4.4 植被方面
筆者在實地調研中發現,海拔較高的山地,林木規模大于海拔較低的地區;等高線較密集的陡坡處,林木規模大于坡度較為平坦的地方。這是由于哈尼族傳統村落普遍選址于林木茂盛的山坡下方,又將村落下方的山坡開辟為梯田,同時對于村中坡度較陡、不適宜建房的地方又保留或種植樹木。
哈尼族傳統村落周邊的森林分為寨神林、水源林、生計林和其他林木。哈尼族人認為,寨神林可保佑村落人丁興旺、五谷豐登。哈尼族人與寨神林是一種相互保護、和諧共存的關系。水源林是最重要的功能林之一,水源林中的水不僅滿足了哈尼族人的日常生活用水,還能用于梯田灌溉。哈尼族傳統村落周邊都有水源林的存在,保護水源林也是村民的共識,水源林中的樹木不允許砍伐。生計林是包括薪炭林、用材林等哈尼族人用來獲取生活必備物資的樹林。其中,薪炭林是哈尼族人獲取木柴的地方。村民根據村落的森林資源情況,共同商議制定薪炭林的使用標準,如薪炭林的范圍、砍伐時間、可砍伐樹木的大小等。而用材林則主要是用于修建房屋、窩棚或制作農業生產工具,用材林的砍伐時間一般為冬季農閑期。其他林木包括風景林、村內林木等,其作用是阻擋大風、分割村落與梯田,同時為村民提供放養家禽的空間等,能為村落提供良好的居住環境或更多的生活資源。
4.5 景觀節點方面
4.5.1 塊面狀景觀節點方面
從元陽縣5 個哈尼族傳統村落平面上看,寨神林、寨心廣場和磨秋場在村落中占據一定面積,構成了哈尼族傳統村落景觀的3 個景觀主節點,承載了居民休閑、社交等功能,對于哈尼族傳統村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其中,全福莊中寨村的寨神林占地面積約80 m2,寨心廣場占地面積約1 076 m2,磨秋場占地面積約600 m2;大魚塘村的寨神林占地面積約1 700 m2,寨心廣場占地面積約897 m2,磨秋場占地面積約800 m2;箐口村的寨神林占地面積約2 000 m2,寨心廣場占地面積約865 m2,磨秋場占地約880 m2;阿者科村的寨神林占地面積約4 000 m2,寨心廣場占地面積約284 m2,磨秋場占地面積約350 m2;埡口村的寨神林占地面積約1 800 m2,寨心廣場占地面積約204 m2,磨秋場占地面積約270 m2。
在元陽縣哈尼族傳統村落中,寨神林一般位于村落海拔最高處,而磨秋場位于村落海拔最低處,二者共同控制著村落的縱向發展。寨神林是哈尼族人祭祀和祈福的場所;磨秋場是哈尼族傳統村落的重要文化景觀元素,是哈尼族人農忙時晾曬糧食,農閑與節日時跳舞、唱歌等娛樂活動的場所,一般位于村落內的一塊開闊平地上,四周由植物圍合[5]。寨心廣場是哈尼族傳統村落的中心,面積大小不一,由村民的房屋和公共建筑圍合而成,是哈尼族舉辦長街宴的場所。
4.5.2 點狀景觀節點方面
寨門和水井占地面積不大,卻是哈尼族傳統村落重要的景觀節點,也是哈尼族人精神和物質生活的重要保障,承載了祭祀、社交和生活保障等功能。
元陽縣哈尼族傳統村落的寨門通常有樹寨門和建筑寨門兩種形式。其中,樹寨門最為常見,寨門由兩棵樹、一條稻草繩組成;建筑寨門則是由竹子制作而成,由兩根粗竹子和一塊寬約1 m 的竹排組合而成,上面會寫著村落的名字。在村落建造初期,哈尼族人在選取寨神林的同時,會選擇能夠提供生產生活用水的水源林。村民用水渠將水引到村莊中,然后將其分為兩支,一支進入村中的水井供人們飲用,另一支流入更低海拔的梯田。村落中的水井是蓄水池,長約4.0 m,寬約1.5 m,深約1.0 m,且有兩三個出水口,方便人們取水。水井上方用石板搭建頂蓋,防止雜物落入水井,保障村民飲用水安全。村落中的水井會根據人口數量修建,多建于道路交叉口,方便村民取水。例如,全福莊中寨村約有1 400 人,村落內共有7 口水井;阿者科村約有470 人,村內共有6 口水井;箐口村約有900 人,村內共有6口水井[7]。
5 結語
元陽縣哈尼族傳統村落形成了由森林-村落-梯田-河流組成的四素同構的格局,且其村落選址完整地體現出了哈尼族人的生態人居智慧。從哈尼族傳統村落的景觀要素特征分析來看,“蘑菇房”適應了當地的地理氣候和生活條件;對植被的功能分類和給排水系統的修建,又充分展現出哈尼族人長期居住在哀牢山中面對自然所形成的生存智慧;寨神林、磨秋場、寨心廣場、寨門和水井等要素都體現著哈尼族的民族文化,除了使用價值之外,還體現哈尼族對自然的崇拜,以及哈尼族人對于美好生活的期盼。哈尼族傳統村落景觀作為紅河哈尼梯田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開展研究,不僅有利于傳統村落的保護和開發,也有利于提升人們對紅河哈尼梯田的認知,為紅河哈尼梯田的保護與傳承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