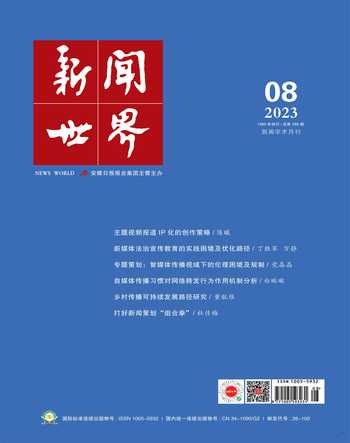人工智能應(yīng)用于新聞生產(chǎn)流程帶來的倫理失范問題及對(duì)策
張宏瑜 楊孔雨
【摘? ?要】相較于傳統(tǒng)的新聞生產(chǎn)流程,人工智能為新聞策劃、新聞生產(chǎn)和新聞分發(fā)等新聞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帶來創(chuàng)新,同時(shí)也存在著侵犯隱私、偏離新聞價(jià)值,缺乏人文關(guān)懷、危害新聞?wù)鎸?shí),塑造權(quán)力中心等倫理失范問題。通過出臺(tái)政策和頒布相關(guān)的法律條例,明確技術(shù)的使用底線,同時(shí)對(duì)技術(shù)進(jìn)行革新,改善技術(shù)侵權(quán)問題;新聞機(jī)構(gòu)和平臺(tái)要承擔(dān)社會(huì)責(zé)任,新聞工作者要發(fā)揮主觀能動(dòng)性,共同改善人工智能應(yīng)用于新聞生產(chǎn)流程帶來的倫理失范問題。
【關(guān)鍵詞】人工智能;新聞倫理;倫理失范;生產(chǎn)流程
【基金項(xiàng)目】本文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學(xué)2023年“促進(jìn)高校分類發(fā)展-公管傳媒學(xué)院專業(yè)學(xué)位點(diǎn)與研究生教育改革”(項(xiàng)目編號(hào):5112311021)項(xiàng)目成果。
大數(shù)據(jù)挖掘、機(jī)器人寫作和算法推薦等人工智能技術(shù)廣泛應(yīng)用在新聞媒體的新聞生產(chǎn)流程中,比如中國最早從事互聯(lián)網(wǎng)輿情監(jiān)測(cè)和研究的人民網(wǎng)輿情數(shù)據(jù)中心能夠監(jiān)測(cè)社交平臺(tái)中的海量數(shù)據(jù),反映輿論態(tài)勢(shì),為新聞工作者提供新聞熱點(diǎn)和線索;新華社“快筆小新”寫稿機(jī)器人30秒內(nèi)生成一篇有關(guān)財(cái)經(jīng)、體育題材的新聞報(bào)道;今日頭條利用算法推薦為用戶提供個(gè)性化新聞分發(fā)服務(wù)。我們?cè)趯?duì)人工智能技術(shù)優(yōu)勢(shì)抱有樂觀期待的同時(shí),也不能忽視技術(shù)在新聞生產(chǎn)各個(gè)環(huán)節(jié)帶來的新聞倫理失范問題。對(duì)比傳統(tǒng)新聞生產(chǎn)流程,使用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新聞生產(chǎn)流程有何變化?出現(xiàn)了哪些新聞倫理失范現(xiàn)象以及出現(xiàn)的原因?如何解決以上問題?這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一、人工智能應(yīng)用于新聞生產(chǎn)流程帶來的變化
新聞生產(chǎn)是新近發(fā)生的事實(shí)經(jīng)過選擇、加工最終形成完整新聞作品的過程。以往的新聞生產(chǎn)流程沒有技術(shù)的介入,主要經(jīng)過“編前會(huì)、新聞報(bào)道策劃、實(shí)地采訪與寫作、編輯校對(duì)、定稿印刷和發(fā)行”這幾個(gè)步驟,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出現(xiàn),使得新聞生產(chǎn)流程越來越智能化。
(一)新聞策劃和新聞采集:更豐富、更便捷的新聞來源
傳統(tǒng)的新聞采集主要是通過自身新聞源(也就是固定“爆料人”)的積累、固定的報(bào)社或者記者熱線、新聞選題策劃、記者自身的新聞敏感發(fā)現(xiàn)具有“新聞價(jià)值”的新聞事實(shí)、相關(guān)報(bào)道的深度挖掘幾種方式,主要建立在人與人的溝通和人與事物的聯(lián)系上。[1]而使用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新聞生產(chǎn)流程在新聞選題策劃方面,可以利用大數(shù)據(jù)分析受眾喜好,推測(cè)出受眾感興趣的議題,預(yù)測(cè)事件的熱度,利用受眾前饋生產(chǎn)出受眾所需的新聞內(nèi)容。例如,作為國內(nèi)首個(gè)媒體人工智能平臺(tái)的“媒體大腦”,在2018年全國兩會(huì)期間從5億網(wǎng)頁數(shù)據(jù)中梳理出了相關(guān)輿情熱詞,為新華社生成視頻新聞《2018兩會(huì)MGC輿情熱點(diǎn)》提供新聞選題。
(二)新聞生產(chǎn)與事實(shí)核查:更快捷的新聞生產(chǎn)速度
將“內(nèi)容為王”作為衡量新聞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的傳統(tǒng)媒體,稿件往往需要經(jīng)過寫作者的前期采訪、寫作以及編輯對(duì)包括新聞選題、事實(shí)的核查以及稿件排版等內(nèi)容的“二次加工”,雖然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稿件的質(zhì)量,但是新聞的時(shí)效性往往打了折扣。機(jī)器人新聞寫作憑借其超強(qiáng)的算力,在不易出錯(cuò)的前提下能夠迅速處理海量數(shù)據(jù),生產(chǎn)出新聞稿件。完成事實(shí)核查后的新聞稿件也可以第一時(shí)間發(fā)布到社交媒體上,受到用戶的廣泛關(guān)注。
(三)新聞分發(fā):更高的目標(biāo)群體抵達(dá)率
傳統(tǒng)媒體發(fā)行一般有代理式分發(fā)和直銷式分發(fā)兩種形式,代理式分發(fā)指讀者通過從發(fā)報(bào)員手里購買或者訂報(bào)站訂閱獲取新聞產(chǎn)品;直銷式分發(fā)是讀者直接通過訂閱熱線從總社進(jìn)行按月或者按年訂閱,郵局分發(fā)員會(huì)在固定時(shí)間派送到指定地址。[2]不管是從新聞的時(shí)效性還是從新聞作品的閱讀率、受眾群體的抵達(dá)率來說,傳統(tǒng)媒體的新聞分發(fā)相比依托用戶閱讀興趣進(jìn)行算法推薦的個(gè)性化新聞分發(fā)不具有較強(qiáng)的競爭力,無法實(shí)現(xiàn)新聞內(nèi)容精準(zhǔn)投放。
二、人工智能應(yīng)用于新聞生產(chǎn)流程帶來的倫理失范問題
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接入使得新聞生產(chǎn)流程與以往有了較大的區(qū)別,具體而言,表現(xiàn)為依靠數(shù)據(jù)抓取進(jìn)行新聞策劃和信息采集、借助算法程序快速生成新聞報(bào)道以及進(jìn)行個(gè)性化的新聞分發(fā)。隨著技術(shù)在新聞生產(chǎn)流程中的應(yīng)用不斷深入,我們?cè)诿鎸?duì)新聞生產(chǎn)的不同環(huán)節(jié)時(shí),都能夠發(fā)現(xiàn)一些由其帶來的倫理失范問題。
(一)新聞策劃與信息采集:侵犯用戶隱私,偏離新聞價(jià)值
能夠?qū)崟r(shí)追蹤社交平臺(tái)上海量數(shù)據(jù)的輿情監(jiān)測(cè)系統(tǒng)和能夠獲取用戶地理位置、移動(dòng)路線的傳感器等有助于新聞策劃和信息采集的人工智能技術(shù),由于大數(shù)據(jù)抓取和篩選的是用戶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留下的瀏覽痕跡和歷史記錄,雖然能夠獲取用戶的閱讀喜好和興趣焦點(diǎn),迅速掌握新聞線索,但是不可避免地會(huì)面臨源數(shù)據(jù)泄露,公民數(shù)據(jù)被迫陷入到非法收集、過度分析的危險(xiǎn)之中,[3]侵犯用戶的個(gè)人隱私。
同時(shí),如果長期使用大數(shù)據(jù)抓取和篩選來獲得新聞線索,也不可避免地會(huì)出現(xiàn)新聞價(jià)值的偏離。大數(shù)據(jù)抓取和篩選最終的結(jié)果是能夠找到受眾的興趣點(diǎn),而那些能夠吸引受眾注意力、進(jìn)行娛樂消遣的暴力、色情、獵奇等題材的信息占據(jù)較大的比例,這無疑會(huì)損害媒體所承擔(dān)的社會(huì)責(zé)任和媒體的公信力,嚴(yán)重偏離新聞價(jià)值的娛樂化信息,也會(huì)導(dǎo)致受眾優(yōu)先關(guān)注個(gè)人感興趣的話題,而漸漸漠視社會(huì)公共利益和重要的社會(huì)議題。
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新聞和記者所寫新聞在新聞質(zhì)量上呈現(xiàn)出新聞的信息量擴(kuò)容、知識(shí)量萎縮的發(fā)展趨勢(shì)。基于海量數(shù)據(jù)的新聞報(bào)道沒有記者在寫作時(shí)對(duì)新聞事件的舉一反三,所產(chǎn)出的新聞很大程度上就是對(duì)數(shù)據(jù)的梳理。我們需要的新聞不是讀起來味同嚼蠟的數(shù)據(jù)堆砌,而是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象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思考。
(二)新聞生產(chǎn)與事實(shí)核查:缺乏人文關(guān)懷,危害新聞?wù)鎸?shí)
人工智能在新聞生產(chǎn)過程中表現(xiàn)出強(qiáng)大的生產(chǎn)能力,依賴數(shù)據(jù)庫的數(shù)據(jù)作為新聞稿件的“原材料”,基于工程師植入其中的算法作為新聞稿件的“模板”,[4]這種拼貼式的寫作方法使得人工智能能夠快速生成一篇新聞稿件,并由此出現(xiàn)了算法新聞、機(jī)器人新聞和傳感器新聞等全新的新聞樣式。
1.無法感同身受,缺少人文關(guān)懷
不可否認(rèn),機(jī)器人新聞等新聞樣式在生成速度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yōu)勢(shì),例如,今日頭條的新聞機(jī)器人“張小明”(xiaomingbot)在2021年里約奧運(yùn)會(huì)上日產(chǎn)30篇以上有關(guān)羽毛球、乒乓球、網(wǎng)球的消息簡訊和賽事報(bào)道。由于新興新聞多是以數(shù)據(jù)為基礎(chǔ)生成的新聞報(bào)道,其程式化的寫作特點(diǎn)使它局限于財(cái)經(jīng)報(bào)道、地震報(bào)道和體育報(bào)道上。機(jī)器人寫作語言的標(biāo)準(zhǔn)化、程式化無法模擬和表達(dá)人類的情感,也無法感同身受,這就使得人工智能技術(shù)無法像媒介從業(yè)者那樣自覺地從新聞倫理的角度規(guī)約自己的行為。因此在地震等災(zāi)難新聞的報(bào)道中,很容易造成為了收集到足夠的數(shù)據(jù)而打擾受災(zāi)群眾,缺少相應(yīng)的人文關(guān)懷。
2.潛在的算法偏見,危害新聞?wù)鎸?shí)
如今互聯(lián)網(wǎng)的準(zhǔn)入門檻較低,Web2.0背景下用戶生成內(nèi)容成為主流,但沒有接受過專業(yè)訓(xùn)練的用戶使其所提供內(nèi)容的真實(shí)性大打折扣,這無疑會(huì)增加虛假信息進(jìn)入寫稿機(jī)器人信息采集內(nèi)容的可能性,降低了新聞報(bào)道的真實(shí)性。
寫稿機(jī)器人的底層運(yùn)作邏輯是設(shè)計(jì)者已經(jīng)設(shè)計(jì)好的算法程序,由于設(shè)計(jì)者對(duì)算法程序以及算法程序未來的生成內(nèi)容有著不可避免的主觀傾向性,算法本身在對(duì)數(shù)據(jù)挖掘、整理和分析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人類能力無法探明的“黑箱”,正如《紐約時(shí)報(bào)》曾在橄欖球比賽報(bào)道中直言不諱:“盡管有大數(shù)據(jù)作為支撐,但和NFL教練相比,我們的機(jī)器人生成的報(bào)告更傾向于樂觀。”[5]由于寫稿機(jī)器人無法對(duì)新聞現(xiàn)場進(jìn)行感知,只局限于了解事實(shí)真相的表面,不能夠挖掘深層新聞事實(shí),也就容易造成新聞?wù)鎸?shí)性的降低。
在新聞事實(shí)核查方面,相較于傳統(tǒng)媒體新聞經(jīng)過新聞從業(yè)者的層層把關(guān),人工智能時(shí)代的新聞把關(guān)已經(jīng)由新聞從業(yè)者向智能算法過渡。而智能算法面臨的問題就是算法本身也無法保證源始數(shù)據(jù)的真實(shí)性,本質(zhì)上這也是對(duì)新聞?wù)鎸?shí)性的一種偏離。
(三)新聞分發(fā):造成信息繭房,塑造權(quán)力中心
以受眾興趣為導(dǎo)向的新聞分發(fā)模式將數(shù)據(jù)、算法、人機(jī)有機(jī)結(jié)合起來,建立用戶和資源的個(gè)性化關(guān)聯(lián)機(jī)制,為用戶提供精準(zhǔn)的新聞投放與分發(fā)。[6]個(gè)性化的新聞推送在不斷迎合用戶個(gè)人信息需求的同時(shí),使得擁有同樣興趣的個(gè)人聚集成各個(gè)分散的小群體,造成網(wǎng)絡(luò)的“巴爾干化”。并且,精準(zhǔn)推送帶來的分眾化趨勢(shì)以及受眾只注意自己期望獲得的東西和使自己愉悅的領(lǐng)域,也造成了美國學(xué)者桑斯坦所言的“信息繭房”,受眾不再具有主動(dòng)選擇信息的權(quán)利,用戶對(duì)公共事務(wù)的關(guān)注度逐漸降低,代表著其生活中公共性的不斷減少。長此以往,受眾的信息接觸面愈發(fā)窄化,社會(huì)認(rèn)知、責(zé)任意識(shí)將不斷弱化,其所擁有的對(duì)社會(huì)公共事件的監(jiān)督權(quán)力將成為無稽之談。
個(gè)性化新聞推送主要以算法程序?yàn)橹危瑢?duì)新聞信息進(jìn)行個(gè)性化的匹配。但是,由于算法程序的不透明性和缺乏管制,媒體平臺(tái)成為個(gè)性化新聞推送中“隱藏的權(quán)力中心”,信息推送與分發(fā)的權(quán)利從公共媒體機(jī)構(gòu)轉(zhuǎn)移到使用算法推薦進(jìn)行信息分發(fā)的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公司,用戶和社會(huì)無法知道新聞是從何而來的,也無法判斷這背后是否有人為的操縱。而這樣的情況,會(huì)使得類似Facebook2016年的“偏見門”事件不斷上演。
三、人工智能應(yīng)用于新聞生產(chǎn)流程帶來倫理失范問題的對(duì)策
面對(duì)人工智能在新聞生產(chǎn)流程中帶來的倫理失范問題,我們可以從法與情兩個(gè)維度來分析應(yīng)對(duì)舉措,完善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明確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使用主體責(zé)任。我們?cè)谙硎芗夹g(shù)帶來便利的同時(shí),也要發(fā)揮作為使用者的主觀能動(dòng)性,讓技術(shù)更好地為我們所用。
(一)政策指引,法律規(guī)制,明確技術(shù)使用底線
政策的出臺(tái)影響行業(yè)發(fā)展的方向,法律條例成為行業(yè)發(fā)展不可逾越的底線。在面對(duì)倫理失范問題時(shí),我們可以雙管齊下。
首先,可以邀請(qǐng)國內(nèi)的知名學(xué)者和業(yè)界代表,共同商討全行業(yè)統(tǒng)一的管理機(jī)制,并完善細(xì)節(jié),形成適合于我國國情的行業(yè)標(biāo)準(zhǔn),并對(duì)該標(biāo)準(zhǔn)的實(shí)施情況進(jìn)行監(jiān)督。該標(biāo)準(zhǔn)應(yīng)該包括數(shù)據(jù)抓取、提取和使用的邊界,人工智能在新聞生產(chǎn)各個(gè)環(huán)節(jié)的社會(huì)監(jiān)督形式等,力圖實(shí)現(xiàn)其在新聞生產(chǎn)流程中的透明化和公開化。
其次,可以借鑒歐盟對(duì)涉及個(gè)人信息獲取、存儲(chǔ)、處理、轉(zhuǎn)移、監(jiān)督等各個(gè)方面進(jìn)行詳細(xì)規(guī)定的《一般性數(shù)據(jù)保護(hù)法案》,以及美國在2019年《算法問責(zé)法案》基礎(chǔ)上更新的2022年《算法問責(zé)法案》(草案),吸收有益經(jīng)驗(yàn),對(duì)人工智能進(jìn)行立法規(guī)范。近日,國家網(wǎng)信辦等7部門頒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wù)管理暫行辦法》,其中提出了促進(jìn)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shù)發(fā)展的具體措施,明確了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wù)總體要求,規(guī)定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wù)規(guī)范等,為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應(yīng)用和發(fā)展提供了指南。
(二)新聞機(jī)構(gòu)和平臺(tái)各負(fù)其責(zé),明確責(zé)任主體
目前應(yīng)用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多集中于中央及各地方新聞機(jī)構(gòu)和以今日頭條為代表的平臺(tái)。針對(duì)上述出現(xiàn)的“隱藏的權(quán)力中心”和危害新聞?wù)鎸?shí)的問題,新聞機(jī)構(gòu)和平臺(tái)應(yīng)該擔(dān)負(fù)起應(yīng)有的社會(huì)責(zé)任。
首先,媒體及平臺(tái)應(yīng)該體現(xiàn)其該有的公共價(jià)值,發(fā)揮政府規(guī)制和企業(yè)自治的雙重作用,貼合政府對(duì)媒體及平臺(tái)在宏觀層面的政策安排,接受外部監(jiān)督系統(tǒng)的審查機(jī)制,避免出現(xiàn)“隱藏的權(quán)力中心”。
其次,面對(duì)媒體及平臺(tái)使用人工智能技術(shù)產(chǎn)出智能新聞的生產(chǎn)機(jī)制應(yīng)該明確責(zé)任主體,實(shí)現(xiàn)人機(jī)責(zé)任捆綁。媒介及平臺(tái)可以制定智能新聞的問責(zé)機(jī)制,明確新聞把關(guān)責(zé)任,為每一板塊的智能新聞分配相應(yīng)的責(zé)任人,負(fù)責(zé)新聞稿件真實(shí)性的審查,避免算法把關(guān)對(duì)原始數(shù)據(jù)真實(shí)性不確定的情況出現(xiàn)。同時(shí)媒體及平臺(tái)應(yīng)當(dāng)在日常運(yùn)營中設(shè)置相應(yīng)的內(nèi)容發(fā)布規(guī)則,規(guī)范自媒體賬號(hào)的內(nèi)容發(fā)布,制定懲處措施,如果發(fā)布不實(shí)新聞,一經(jīng)查處,即刻查封賬號(hào)。
(三)人機(jī)結(jié)合,發(fā)揮新聞工作者的主觀能動(dòng)性
在財(cái)經(jīng)類、體育類等消息寫作領(lǐng)域,我們應(yīng)當(dāng)充分發(fā)揮人工智能技術(shù)既有的優(yōu)勢(shì)和作用,快速產(chǎn)出新聞報(bào)道。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新聞工作者的工作壓力,使他們擁有更多的時(shí)間進(jìn)行深度思考并且產(chǎn)出具有深度、引發(fā)社會(huì)思考的新聞報(bào)道。但是,我們不能忽視出現(xiàn)的新聞價(jià)值偏離和缺少人文價(jià)值報(bào)道等帶來的問題。
首先,為了解決新聞價(jià)值偏離的問題,我們應(yīng)當(dāng)推動(dòng)新聞機(jī)構(gòu)和人工智能技術(shù)研發(fā)公司實(shí)現(xiàn)對(duì)技術(shù)愿景的溝通,及時(shí)了解技術(shù)的生產(chǎn)和實(shí)際操作過程,進(jìn)一步明確新聞機(jī)構(gòu)對(duì)技術(shù)的期待以及預(yù)期取得的成效,不斷完善技術(shù)產(chǎn)品,避免信息采集時(shí)完全跟著受眾的興趣走,提高技術(shù)對(duì)信息的識(shí)別能力。
其次,我們應(yīng)當(dāng)發(fā)揮新聞工作者的主觀能動(dòng)性,在智能新聞中加入人文價(jià)值因素,實(shí)現(xiàn)技術(shù)和人的有機(jī)結(jié)合。先是主動(dòng)利用智能算法進(jìn)行數(shù)據(jù)分析、敏銳捕捉到熱點(diǎn)和重大事件并形成初稿,之后記者在深入調(diào)查的基礎(chǔ)上逐步完善新聞稿件,最后將新聞報(bào)道通過智能推薦的方式送達(dá)用戶。新聞工作者對(duì)新聞事實(shí)的深度分析和調(diào)查能力能夠增加新聞稿件的人文關(guān)懷因素,從而提升對(duì)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運(yùn)用與把控,實(shí)現(xiàn)“人機(jī)共生”,促進(jìn)新聞業(yè)高效、智能發(fā)展。[7]
(四)技術(shù)革新,改善侵權(quán)問題
人工智能技術(shù)在新聞策劃和信息采集以及新聞分發(fā)環(huán)節(jié)中的使用,能夠幫助用戶快速獲取信息,但這也造就了一批信息時(shí)代的“懶人”。他們?cè)跒樾畔⒌谋憬輷Q取歡呼雀躍的同時(shí),卻不知道已經(jīng)陷入了隱私侵犯困境和“信息繭房”之中。
首先,要明確人工智能技術(shù)在搜取信息時(shí)的界限和范圍,不斷完善或優(yōu)化算法,平衡技術(shù)應(yīng)用和內(nèi)容選擇之間的關(guān)系,構(gòu)建更科學(xué)合理的算法模型。這樣的算法模型不僅能夠識(shí)別用戶的個(gè)人興趣,同時(shí)也能基于時(shí)下的熱點(diǎn)和社會(huì)發(fā)展的客觀現(xiàn)狀實(shí)時(shí)推送分發(fā),避免“信息繭房”的出現(xiàn)。在程序設(shè)計(jì)中,給用戶閱讀“用戶須知”留出一定的時(shí)間,不讓“默認(rèn)勾選”成為侵犯用戶隱私的“霸王條款”。
除此之外,技術(shù)的使用也能夠改善虛假新聞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技術(shù)對(duì)機(jī)器人生產(chǎn)的新聞進(jìn)行數(shù)據(jù)來源、內(nèi)容生成方式的標(biāo)注,實(shí)現(xiàn)新聞?wù)鎸?shí)性的回溯。在技術(shù)未完全成熟前,“把關(guān)人”這一角色依舊應(yīng)由新聞從業(yè)者來擔(dān)當(dāng),承擔(dān)數(shù)據(jù)管理和程序驗(yàn)證的工作職責(zé),以保證源數(shù)據(jù)真實(shí)可用。我們也可以利用區(qū)塊鏈技術(shù),保存寫稿機(jī)器人的稿件生成記錄,當(dāng)出現(xiàn)虛假新聞時(shí)能夠進(jìn)行媒體信源的認(rèn)證。
四、結(jié)語
可以預(yù)見的是,未來隨著人工智能的發(fā)展,新聞業(yè)與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結(jié)合將會(huì)越來越緊密,個(gè)性化新聞聚合與推送已成為不可避免的發(fā)展趨勢(shì),如何趨利避害,更好地運(yùn)用技術(shù)以重塑新聞業(yè)價(jià)值,是值得繼續(xù)思考和討論的問題。正如萊文森所言,對(duì)待任何一個(gè)新型技術(shù)手段,必須要謹(jǐn)慎觀察,不可盲目地否定。
注釋:
[1][2]吳佳洪.人工智能技術(shù)背景下新聞生產(chǎn)流程創(chuàng)新研究[D].暨南大學(xué),2019.
[3]李超,李雅林.人工智能技術(shù)引發(fā)的新聞傳播倫理失范問題[J].城市黨報(bào)研究,2019(12):31-33.
[4]李暉,劉茂錦.人工智能在新聞傳播中的倫理失范與對(duì)策選擇.轉(zhuǎn)引自新媒體與社會(huì)[M].北京:社科文獻(xiàn)出版社,2020.
[5][7]靖鳴,婁翠.人工智能技術(shù)在新聞傳播中倫理失范的思考[J].出版廣角,2018(01):9-13.
[6]苗壯,方格格.人工智能如何“人性化”:新聞倫理失范分析與對(duì)策[J].傳媒,2021(23):94-96.
(作者單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學(xué)公共管理與傳媒學(xué)院)
責(zé)編:姚少寶